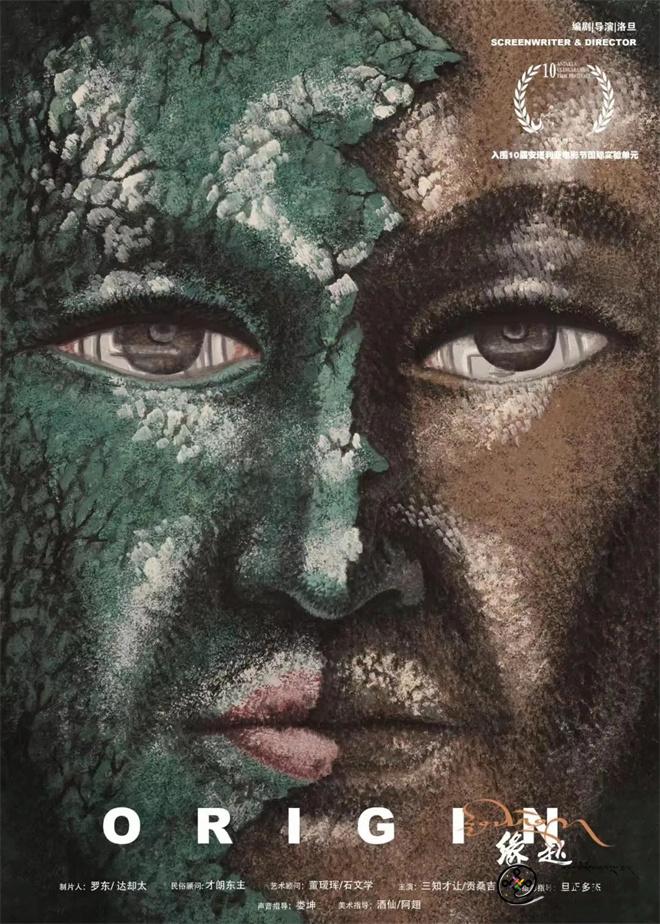时间: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
地点:北京东隅酒店
受访:万玛才旦(导演)
采访:王小鲁(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博士)
责任编辑:张煜
版权:《当代电影》杂志社
来源:《当代电影》2019年第11期
文化使命与个体性表达
 王小鲁(以下简称王):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您最新的《气球》我没有看过,不过我刚看过原著小说。但您从在北京电影学院创作的短片《草原》到后来的作品我都看过,那时候藏语电影还没有形成话题,还没有“藏地新浪潮”这个概念。
王小鲁(以下简称王):我们认识很多年了,您最新的《气球》我没有看过,不过我刚看过原著小说。但您从在北京电影学院创作的短片《草原》到后来的作品我都看过,那时候藏语电影还没有形成话题,还没有“藏地新浪潮”这个概念。
 万玛才旦(以下简称万玛):那时候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藏语电影。所谓的“藏地新浪潮”,其实最早出现在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好多年前我去那里做了一个展映,他们提出了藏地新浪潮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是从那儿开始的,它其实是用来区别以往的藏族题材电影的。
万玛才旦(以下简称万玛):那时候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藏语电影。所谓的“藏地新浪潮”,其实最早出现在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好多年前我去那里做了一个展映,他们提出了藏地新浪潮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是从那儿开始的,它其实是用来区别以往的藏族题材电影的。
王:对,以前连藏语电影也没有。过去的藏族题材电影都是说汉语,或者是将藏语对白翻译为汉语来放映。所以,您一出现,就成为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大约在2011年冬天,我们在亮马桥附近的宾馆做过一个下午的对话,我觉得,那是一次非常沉静的对话。当时有一个深刻的感觉,您对于我所有的问题不逃避、不躲闪,都在认真思考和回答,知道多少就回答多少,包括我们策展时请您来。这些交往都让我感受到了导演您身上的特别美好的品质。我一直说,这是一种属于藏族导演的或者说藏族人的美德。于是,我现在的问题就来了,其实从东部的汉人来说,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就分不出哪些是您个人的东西,哪些是属于民族的东西,我们总是要赋予您一种代表性。我觉得这是评价您的创作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文化传播甚至您创作时可能要面对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万玛:对。一方面跟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另一方面可能跟生长环境中的文化等有关系,比如说藏传佛教。所以你在那样一个环境中长大,自然就会受到这个方面的影响。所以在藏人艺术家个体身上,或他的作品里呈现的这样一些特质,是跟他的文化,跟他的传统,跟他的信仰有关联的。
王:对。您关注的还是藏区存在的具有文化普遍性的问题。那次对话,我说过,因为藏族没有出现过导演,万玛才旦导演是第一个,这个时候大家必然把您符号化,将您的创作看作是一个民族的代表性发言,必然赋予您一个重要的文化使命,也许您有些时候也愿意背负这个使命。这是一个双刃剑,它既是一种便利,又是一种枷锁。对您有利的方面可能是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另外一个方面则是会对您的电影有一种很高的要求。现在随着您(执导)的影片越来越多,大众认知度越来越高,藏族人也知道得越来越多,这时候反而质疑的声音也会慢慢地起来,我不知道您是否遇到过这个问题?
万玛:会有一些压力,刚刚说的这种使命感肯定也是存在的。但是从创作本身讲,它肯定是出于一个创作的目的,无论任何形式的创作,不论是写小说、拍电影,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创作的一种欲望的实现。现实层面,因为你所处的这个族群,所处的这个文化,它一直是处在弱势的位置,以往无论是文字还是影像来反映你的族群的时候,它和你的族群的文化或者宗教,其实是有很大偏差的。所以就自然地会产生一个使命感。以前在学习电影之前,你会接触到一些藏族题材的电影,包括自己,包括我身边很多普通的观众或者一些知识分子层次的观众,他们会有很多的遗憾,会有很多的不满足,然后大家就会感慨、感叹,说如果将来有一个真正懂自己民族文化,对自己的民族比较熟悉了解的创作者来拍反映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生活的电影,那肯定就不一样。这种现象不单单存在于电影领域,文学领域也有,就是文学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描写、类似的表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绘画,甚至音乐领域都有。
王:就电影来说,您认为这些偏差主要是哪些方面?
万玛:我觉得主要就是对人的忽略。你看那些作品,对人的忽略,对藏人也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忽略是非常普遍的,无论文学作品还是电影作品你几乎看不到一个丰富的、立体的、活生生的人。你看到的更多是表面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区别。这样,你作为这个族群中的一员,你自然就会有一种使命感。当你从事这样创作的时候,别人也会自然地赋予你一个使命。所以,作为创作者,一开始可能会带着双重的使命去创作。但作为创作者,终究我自己是希望成为一个纯粹的创作者的。
王:我能够理解您所说的观点。这个可能涉及到创作思路和创作时的文化心态的问题,还有传播时的文化策略的问题。当将这些作品看作是一种族群的代言的时候,就给予了自己一个非常宏大的要求,也就成为创作的负担。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那种族群发言的特点也是必然和无奈的选择,因为随着信息交流的深入和社会发展,藏区文化必然面临更为强势和主流的现代文化和政治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这个时候这个群体的命运还是具有一种整体性和统一性的。也许每个人的态度和机遇不同,在很多层面还是处于一种共同命运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当您说让自己成为一个更为纯粹的创作者的时候,其实这去除了自己的心理负担。
万玛:这种赋予的使命会影响别人对你作品的判断,甚至你去参加电影节,很多人觉得你这个题材会有一些优势什么的,会把你的创作实际的成分缩小,会把其他的一些成分强化放大。对于一个创作者,这些都是不公平的。我也在很多场合说过,我作品中反映到的只是藏区的一部分,并不能穷尽所有的藏区、藏区所有的当下。一部电影作品很难穷尽一个族群或者这个族群的当下,这很难做到。但是你会试图去表现这个族群或者这个族群当下的一些共性。比如《寻找智美更登》就有这样的出发点,它的情节设置其实是一种有意的设置,通过一个公路片的形式把藏区具有代表性的一些点串联起来,比如草原、农区、机关单位、文艺团体、学校、寺院,等等,通过设计很多这样的点来还原藏区的概貌。通过剧情,通过人物把这些点串联起来,就可能做到了把那个特定年代藏区的一个基本面貌还原出来的目的。像《老狗》,它带出的是藏区的一个点,不是全部。
幽默感与高原现代性的表达
王:您作为导演的出现,改变了一个文化格局。就好比说,女性主义者经常批判某些影片没有体现女性主体,而这些影片往往是男性导演的,一个男性导演必然带着自己的生理特性去感受世界,要改变整个文化格局,更有赖于女性导演自己去创作。对于藏族题材电影来说一样,不是要求某个电影中表现出来藏人的主体性,而是让藏人在电影的生产关系和权力格局中获得主体性,当藏族导演出现,一切就不一样了。这其实也是万玛才旦导演出现的文化意义。我们知道您的学习经历,是在大学学习藏语言文学,但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主流的教育体系,另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您的创作方法也是后来慢慢学习得来的,其实您的视角和经验已经与一般藏民不同了,您的文化表达和文化感受,其实还是区别于一般藏民的感受。
万玛:这样的经历,这样的学习过程,会带来很多的反思,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信仰,你可能会对很多方面做很多的反思。走到今天,单单从信仰层面讲,就很难说自己是一个很纯粹的百分之百的佛教徒。有一本书叫《近似佛教徒》,我觉得跟这个描述是比较接近的。你身上其实已经掺杂了很多东西,甚至有时候可能有一些扭曲。但是这样的挣扎、这样的扭曲,我觉得对一个创作者是很重要的。
王:对。这会带来一种富有现代性的思考,就是面对过去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开始带有一种审视的态度。而且我相信,导演所有的这种挣扎,也是一种普遍的挣扎,很多藏民也会有类似问题,很多信仰者可能也不是百分百的信仰。所以您的影片里,必然带来一种文化冲突的表达,不仅仅是空间的冲突,还有一种时间的冲突,就是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有藏族朋友也许会说,万玛导演的电影为什么不表达现代性的东西?现代藏族也有现代生活啊。其实您的作品恰好是现代性的,文化现代性是对于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恰恰是对于社会现代性、经济现代性带来的不适的一种反应。但是这个现代性的反思的展开是否深刻和丰富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最近看您的新书《乌金的牙齿》,发现这本小说中的无比的幽默感,联想到您电影中的场景,经常将人物置于现代文化和前现代文化交错的地方,比如《静静的嘛呢石》,小喇嘛想看电视剧《西游记》,小活佛也想看,他也是一个孩子,但是看电视剧影响学习,小喇嘛戴着孙悟空面具,手里拿着电视剧VCD空盒的段落,里面有一种忧伤的幽默感。在《乌金的牙齿》中,乌金是“我”小学同学,数学总是不及格,每次考试都抄“我”的。乌金成为活佛后,大家都回忆他平时有什么不同的品质,“我”觉得他没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除了从小数学不及格。这里面似乎有反讽,但是故事慢慢展开,我们看到了态度的复杂。“我”开始回忆他的往事,想起来他的确很善良,为了救一条鱼费尽力气。而且当时抄“我”作业的时候十分虔诚。所以作业很整齐,乃至老师每次都表扬他,而不表扬“我”。
万玛:小说也写到这位同学成了活佛后,天文历算学习得特别好,也是一种反讽。
王:对,我也注意到了,这里的含义就很复杂,可能这个同学的智力是很好的,只是当时的教育环境让他无法发挥个人潜能。所以这部小说中对于活佛的态度犹疑又认可,总之比较暧昧,但是又特别幽默,所以我发明了一个观点,这种幽默正是您现代性表达的方式,往往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方式。
万玛:一方面跟自己性格有关系,另一方面跟自己所处的文化、信仰也有关系的,就像上面讲的。每个人都有个性,但是又有被那个大的宗教文化传统以及环境所塑造出的共性。比如说对生命的态度,对死亡的态度,当你面临这样一些大的问题的时候,那种共性的东西又出来了。
王:这是一个辨证的关系。最新的电影《气球》我 还没有看,但是这篇小说让我感到惊喜。这部电影就是 完全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对吧?我记得《撞死了一只 羊》是根据两个小说改编的。
万玛:对。《气球》根据一篇同名小说改编的,故事主线是一样的。这篇小说,其实是先有剧本,后有小说,当时写完没有拍出来,所以就先把小说发表了。
王:小说的幽默感和荒诞感更强烈。小说的表达时常涉及到性的暗示。两个孩子拿着父母的安全套当气球吹,导致了父母意外怀孕。这时候孩子的母亲还不知道,她其实是要去做节育手术的,因为她不想当生育的工具。小说还设置了父亲去找公羊为自己的羊配种的情节,父亲和爷爷都对动物生殖的行为充满了欣赏。之后,慈祥的爷爷去世了,但是活佛告诉他们,爷爷会重新转世到他们家,而这个家庭主妇正好得知自己怀孕了,这个胎儿她似乎就很难自主做决定要还是不要了。这个故事涉及到女性的身体、信仰和生育等等,走到了一个新的表达层次上。不知道这部电影大家看到后是什么反响?
万玛:不错。很多人觉得可能主题上又回到了以前的,像《老狗》《塔洛》的主题层面。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区别。
电影藏语的进化与可能性
王:刚才说到的幽默感,但是您小说文字里面包含得更为充分,更为淋漓尽致,电影里面也有,但是给观众的整体感觉往往是另外一种东西。您从一个作家转变为导演,表达上的转换,您如何评价?
万玛:其实电影涉及到的比较单一,小说更宽广一些。电影有很多方面的制约,你可能自然而然就跑到了那样一个方向,那样一个题材的领域。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不太自由的创作,但是文学相对就自由一些,纯粹创作欲望的一个实现。那这种实现最终的落点就在你身上。电影一旦完成,最终要通过各种渠道去跟观众见面,去面对市场。但文学,写出来就完成了表达,对我来说发表或是不发表都一样。以前可能发表是很重要的,渴望发表,渴望被很多人看到,现在可能已经过了那个年龄段,创作成为了一种很自然的创作,作品呈现出来的样貌也会很自然。文学和电影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语汇,表现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
王:对。其实我想聊一下您的电影语言的发展问题。您的小说语言风格很明显——简约,电影方面的语言也有自己的特点。最早看您的电影,当时就觉得整体上有点木讷,从人物表演到场面调度,后来我专写过文章为此辩护过。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像别人批评的那样,把您的作品自动合理化了。但还好,我去过高原深处,觉得可能与气候有关,那里的人的行动节奏和表情相对迟缓。
您的电影也喜欢长镜头调度,和您的小说一样,电影也有一种极简主义风格。但是这种极简风格其实是那个环境所给予的,您只是将这个环境的本来的特点利用起来。我觉得高原非常像一个剧场,因为剧场的设施具有示意性,都是相对简约的,而高原的外部事物也相对简单,这是物质环境的事实,似乎也是符合宗教追求的。所以我说高原非常像剧场,而且高原很高,我们在东部低洼处的人们时常仰望。事实上,我们将西部高原上的事物看作是神圣和神秘的。当然我这个比喻,不是要强化和建构一个看与被看的不平等关系。若在城市里面,会发现它相对嘈杂混乱,很多事物堆积在一起,彼此消解映照,但是高原上由于简洁,反而更容易提炼,很容易寻找到作为修辞的物体。比如《塔洛》中,照相馆、酒吧都可以作为一个喻体,从银幕视觉上这些比喻也很容易被观众把握。所以,可以将高原比作一个剧场,高原剧场。
万玛:您讲的这种剧场的特点,很有意思。您刚才讲的,一个城市参照的东西太多,场景很丰富,有很多角度,对拍摄很有便利。但是在藏区就会面临一个挑战,因为场景太单一,没有太多参照,所以在那样一个场景,比如说草原,要拍出一个很丰富的东西,相对就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可能在那么一大片的草原上,走到哪里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景致。
王:就说这个镜头语言是根据外部世界的特点来运用和营造的。如果在一个场景上,推拉摇移都是一个景色,那这种运动似乎也就成为没有必要的。其实镜头语言,和自然环境相关。
万玛:所以每拍一部电影的时候,怎么摆脱那种比较单一的感觉,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每次拍电影的时候,希望多找到一些角度,多找到一些视点,在那样一个相对单一的空间里去呈现比较丰富的细节、比较丰富的视点。
王:这些年,您的电影语言还是变化很大,直观上比以前流畅多了。我觉得这个变化是从《五彩神箭》感觉到的,我看了那部电影以后,很惊讶,它很像一般的戏剧化电影,而且人物组织动作和语言都很流畅,没有那么木讷,那些演员也都是藏族的吗?
万玛:对,专业演员。
王:其实万玛导演的另外一面没展现出来。
万玛:对我来说,题材确实很重要,题材的内容决定了讲述的方式,也就是说内容决定形式。《五彩神箭》要讲一个很特殊的、有戏剧冲突的故事。这个故事需要面对大众,所以就选择了那样的方式。另外,如《撞死了一只羊》,它有那样的风格,也是跟它的内容有关系的。
王:到了《塔洛》,镜头语言包括构图就特别不一样,人物的脸部都不在画面的主体位置,而是在边上。这个变化,您自己是有自觉性的吗?
万玛:对,就是找到了一种适合这个故事的讲述方法。《塔洛》的文本就决定了它的视听语言。这样的影像的风格,是一个自然的选择。像《撞死了一只羊》也是,你在面对这样一个题材的时候,你肯定得找一个适合它的影像风格。
王:但是从影像上来说,《撞死了一直羊》确实有影像先锋性。
万玛:它的文本本身就有先锋性,这篇小说就是先锋小说,所以也让影像具有了这样一种先锋的特质。
王:您的作品一直有一个特点,如果把它作为一个负面的东西来描述的话,看您会怎么回应。您的作品有些抽象的东西,尤其像《撞死了一只羊》。另外,我以前说您是作家电影,跟法国作家电影相似,您的电影由自己的小说转变过来,所以感觉很喜欢使用隐喻这种方法。我甚至说过您的《塔洛》有点学者化电影的倾向。因为有些电影是直接调动您的感性,利用生命气息的相通,马上让对方感觉到并且理解。您的很多作品包括镜头语言,有些地方要依赖于文化修养去解读,就是说,比较理性化,当然这也是一种电影方法。但是您的好多作品,需要我们再去阐释和解说一下。比如说在《塔洛》的那个不均衡构图,人在画面边缘,我觉得是这个人主体性丧失的一种隐喻。这样一个评价,您如何回应?
万玛:创作本质上是一种感性的表达,是从感性出发的。但是需要一些方法来呈现。比如电影,在面对不同题材的时候,你会选择一种语法,用适合它的语法去呈现那样一个内容。就像我的小说,我汉语小说的语言可能跟其他汉族作家的语言使用或表达方式也不太一样,这跟你对某种文字语法的理解、掌握,包括对自己本民族语言的语法的理解,掌握,以及融会贯通、互相影响是有关联的。它可能是比较混杂的、复杂的。
王:其实关于藏语电影的语言问题,我2012年初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电影藏语》,我说的是电影藏语,不是藏语电影。如果说,藏族的语言有自己的独特性,藏族的电影语言有没有它的独特个性呢?您也说了,您的电影语言的使用必须和题材和场景相关,不可能发展出一个非常独特的但又没有根的东西,它的根就是藏地的文化和精神世界,那电影的藏地语言和语法是什么,这东西是否可以追寻?
万玛:它会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但是这种独特的东西目前我很难去总结,去陈述它。就比如说空间、时间的描述,怎么呈现,怎么在那样一个空间、时间之中展开你的故事,怎么把你的人物放置在那样一个空间时间里面,让它显得丰富,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你在拍每一部电影的时候都需要思考。这也是我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
王:现在藏地电影新浪潮的作品还不够多,以后再总结也不晚,但您也认为还是可以说的。隐喻、空间,还有很多可以归纳的,比如节奏。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摄影机运动的节奏是跟人物心理节奏相匹配的,香港电影导演王家卫的节奏和万玛才旦的高原节奏就完全不一样,这也是由独特的空间和独特的精神文化所塑造的。
“藏地新浪潮”群体与文化翻译
王: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您作为藏地新浪潮的带 领者或者说核心人物,以您的阅历和创作的数量,以 及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推动了藏语电影创作。今年的 藏语片《旺扎的雨靴》也有不错的反响。现在我们可否 将镜头稍微拉开,来谈论一下这些现象?
万玛:“藏地新浪潮”是对这样一个现象的概括,不像法国新浪潮是一种创作方法的概括。“藏地新浪潮”其实是一个比较,区别于以往的藏族题材电影的比较。它们有一些明显的、不同于以往的藏族题材电影的特点,也是对这样一个现象的总结。2005 年制作的《静静的嘛呢石》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藏语电影的诞生。之后激励了很多藏族年轻人,更多的藏族年轻人想进入电影这个领域,想通过影像做自己的表达,后来就
有了松太加、拉华加等导演。
王:这和以往制片厂体制下的电影生产不一样,您的工作方法很有特点。我记得您说过,以前你们团队大部分是藏族人,现在整个格局还是这样的吗?
万玛:差不多是这样的。
王:这种配置可以说为藏族地区培养了很多电影人才,也为藏文化输入了一种现代性事物,因为电影是现代性的,不仅仅因为这是一种新技术,而且因为这种艺术形式带来的一种反思性。或者说,仅仅是它带来了的一种表达手段的丰富,就是非常可贵的。我发现您介入了很多藏族导演的新片。
万玛:对,参与的相对比较多,比如说看看剧本,为整体的创作把把关,帮着找一些主创,甚至一些资金什么的,自然就牵扯进去了。这可能跟当下藏语电影的格局也是有关系,因为没有太多的人来做,对这个行业、对这样一个创作方式了解的人也不多,年轻人他想做自己的作品就自然会找到你。可能对我来说也成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义不容辞的事情,但是很消耗精力。
王:《旺扎的雨靴》也是您监制的吧?我不知道您在里面介入有多深,但是这部影片,很多方面和您的作品也很相似,也很擅长使用隐喻,这个隐喻我以前以为是一个表达策略,后来听您说我才知道,其实藏族文学有这样的传统。旺扎的雨靴在那里似乎代表一种新的生活和文化,但是要穿上这个雨靴,就要去偷走防雹师的神剑,让天上下雨,追求这种当下的生活就要去将一个神圣传统阻断。我自然而然就产生了这么一个解读。
万玛:这部电影我参与比较多,是我的一个学生拍的,包括那个防雹师的人物。我自己以前也拍过一个防雹师的纪录片,叫《最后的防雹师》,Discovery系列中的一部。导演在写剧本的时候,我就让他看那部纪录片,里面很多的细节其实就来自那个纪录片。它这里有一些有趣的对比,就像刚刚您讲的这个,就看怎么解读,这样解读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但确实有点意思。
王:您说第一次听到,我也感觉有点惊讶。我是觉得那个意味是比较明显的,虽然这是一个温和的含蓄的表达,但也许是一个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处于一个大的思想环境中,就是一个信仰遭遇了现代化的过程,这其实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万玛:可能创作者没有想到那个层面,他可能更多是从剧情安排的需要去做了那样的设置,因为最后他要在一个两难之中结束这个故事。小孩等待的那场雨也许就要来了,也许不会来。电影是由一篇小说改编的。小说里面雨来了,我是建议他的电影做那样的结尾。你刚刚讲的那种潜意识的东西,我觉得作者有时候是没有意识到的,但是你作为观众可以做那样的解读。所以一部电影作品完成之后,就是读者或者观众在不断地丰富它。当你完成了一部作品,就已经把它交出去了,就像一个小孩,把他培养成人了,剩下的路就要他靠自己走了。
王:也许评论者的一个任务,就是去发现创作者的潜意识。这就涉及到一个文化传播的问题,藏文化让人觉得有神秘感,电影表达的一部分就是一种文化翻译,就像《撞死了一只羊》,之后可能讨论比较多的是电影像密码,有隔膜感,很多元素大众不理解,如何将独特文化转化成普遍人性,这可能是藏地导演要面对的问题。
万玛:如果你对某一种文化不熟悉、不了解,那天然就有一种隔膜感。同样一个题材,这个导演拍跟那个导演拍,就肯定不一样。这个导演拍,你会有很熟悉的感觉,另一个导演拍了,可能就有一种隔膜感,这可能就是它的表达方式带来的不同效果。
王:一个是表达方式的问题,另外当然还是文化差异的难以消除。当我去要求一个藏族导演进行更深入的文化翻译,要让这个宗教的特点更加被普遍化理解的时候,这可能也存在一个霸权的问题。我们汉族的人去表达自己的文化,比如祖先崇拜,就不会考虑这么多。而藏地导演呈现自己的文化脉络,我们就要求他解释,这可能也是一种不平等。
万玛:对。我在进行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做着对于强势的文化或者对一个更大的群体或者一个强势的市场的妥协。
王:在对您作品的理解上,是不是汉人观众比国外的还要好一些呢?因为毕竟是一个共同体,有更多共同经验。
 万玛:对,有这个基础。文化层面、政治层面、信仰层面,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东西。比如说《塔洛》,在大陆,大家知道这个电影在讲什么,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但到了一些西方国家,观众就有点难以理解了。观众可能更多体验到的是关于人的孤独、人本质的一些东西。
万玛:对,有这个基础。文化层面、政治层面、信仰层面,还是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的东西。比如说《塔洛》,在大陆,大家知道这个电影在讲什么,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但到了一些西方国家,观众就有点难以理解了。观众可能更多体验到的是关于人的孤独、人本质的一些东西。
王:沟通是一个过程。有一些很难,有一些相对容易。比如《寻找智美的更登》,女主角在寻找爱人的过程中,司机通过讲自己的故事,让她放下。当时我写过文章,我说这里有佛教教义——放弃我执中的情执。最近一个藏族朋友跟我聊,说这其实不是藏族特有的,在好莱坞编剧课里就是把“不停的放下”当作一个人成长的标志,所以我们仍然相信交流,相信差异化下的普遍人性基础。藏语电影的一个功德就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巨大的交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