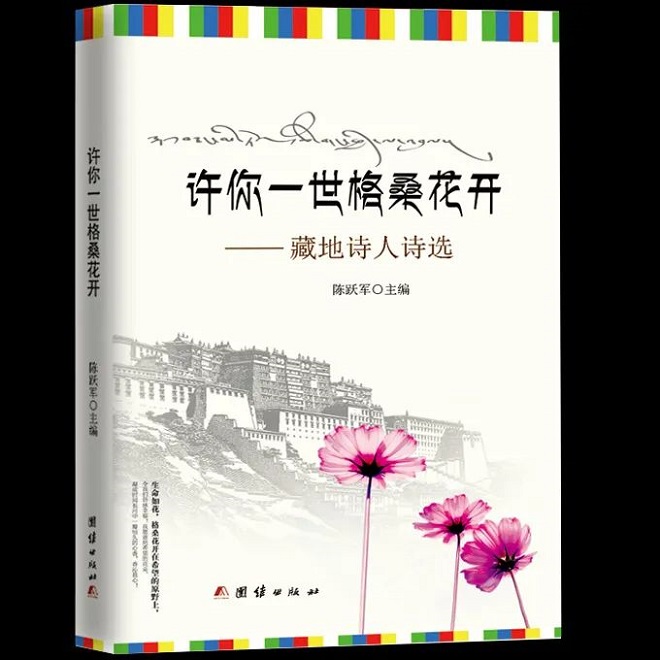
《许你一世格桑花开——藏地诗人诗选》(陈跃军主编,团结出版社出版)
诗歌,是朝向灵魂深处的扎根,是广阔的精神之探求,是纯粹的精神之家园。西藏,这片高地厚土是产生伟大诗人和优秀诗歌的沃土,格萨尔史诗在这里千古流传,米拉日巴道歌影响至今,仓央嘉措诗歌也广为传唱。藏地独特的地域文化为诗人提供了丰厚的创作源泉,藏地诗歌因此成为藏地风貌之画卷、藏地精神之凝练、藏地文化之精华。自西藏和平解放后,藏汉诗人共同构筑起诗歌创作的繁盛景象,共同点缀着文学的璀璨星空。主编陈跃军先生多年致力于诗歌创作,他以其赤诚之心一方面从事着繁重的行政工作,另一方面,在推广西藏文化,繁荣诗歌创作方面功不可没。此次,他将其编辑的21位诗人的诗集《许你一世格桑花开》交给我,让我写个序,并嘱我对诗歌做一个简单的点评,钦佩和感动于他对西藏的热爱,对诗歌的一片赤诚之心,我当然是不能推辞的。诗集中收录21位诗人的诗作,这些诗人中既有在诗坛上跋涉多年,有一定影响的优秀诗人,如吉米平阶、陈人杰、刘萱、陈跃军等知名诗人,更有挚爱文学,默默耕耘,以诗歌作为自己精神后花园的年轻诗人,如希贤、陌上千禾、木朵朵、德西、咚妮拉姆、萨娜吉、才旦多杰、安拉加、丹增曲珍、德西、嘎玛旺扎等。虽然他们职业各异,经历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对文学葆有热情,对西藏充满深情。
藏族作家吉米平阶的创作往往植根于本土的文化想象和阐释,他十分注重对诗歌创作文体和技艺的探求。收录于本诗集的《纳木娜尼的传说》是一首独具魅力,内蕴丰厚的长篇叙事诗,是近些年藏族诗坛不可多得的优秀诗篇。作者根据藏族民间神话传说演绎而来,生动地讲述了纳木娜尼和冈仁波齐及拉昂措的爱恨纠葛。作品感情充沛,气势磅礴,充满着瑰丽的想象,展现了洪荒年代天地的状貌,人类原初的情感:“在天地洪荒、混沌初分的时候,/在地球的极西之地,/那时候这里还不分昼夜,/太阳和月亮轮流逡巡,/所有的星星都长在地上,/有属于自己的领地、家族和牧场……”。在这片孕育着辽阔生命的大地上,纳木娜尼和冈仁波齐命定地相遇结合。纳木娜尼的爱真挚而炽烈,当发现冈仁波齐背叛后,“黑暗是从纳木娜尼的心头升出来的。/银河泯灭、星星散逸、天地顿时漆黑,/是的,这就是那个叫黑夜的东西。”她的出走缠绵而凄婉,“纳木娜尼和冈仁波齐遥遥相望,/空气中弥漫着无尽的悲伤,/悲伤像荒原野火那样强烈,/灼伤了众神云霞的衣裳。”吉米平阶在文字间翱翔,在想象中进行追忆,以喷薄的激情,绚烂的想象和倾泻的文字描绘了洪荒年代豪放诚挚的生命意识,闪烁着神奇的魅力。
诗歌是源自心灵的至真情感,是个体灵魂的真实写照,作为援藏干部,陈人杰和刘萱的诗歌均具有独特的精神质地。陈人杰一路向西,从江浙大地至青藏高原,他的诗作既对故乡满驻深情,同时又将满腔豪情寄予在这雪域大地。他的诗歌将所见所感汇成文字来抒发对自然、生命的探寻,雪域大地在这个豪迈的男人笔下尽显了柔情,《纳木措》中,诗人写道:“高天澄澈,湖水绚烂 /如果你还不知道圣水的纯净,一定是/在尘世的镜子里过于流连/我绕着念青唐古拉雪峰在走/大梦无形,圣贤出于幻象/而自己的心,来自一步一个的脚印/一步一莲花,远山起滚雷/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天堂,一定是/我没有带你来,没有带你/出现在伟大事物的身旁。”诗歌《秘境》中描绘人间密境南迦巴瓦峰:“南迦巴瓦朝人间张望/雅鲁藏布为大海洋分泌胆汁/白天鹅带来了雪/晚归的豹子让夕阳迟疑/怒江去了云南,/一条鱼留在那曲/声、深壑、幽暗鱼鳞/都是秘境/扎加藏布,央金笑着,小腹隆起/高原上多汁的人儿/比大地更清楚水系的甜蜜。”作者以细腻而饱满的想象呈现了雪域的胜景秘境。大爱无声,陈人杰将西藏独特的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尽显于笔下,创作出具有生命感悟的诗歌,他的诗句中透着一种孤独、悲凉,然而又生发出信念和理想,在寂寥中呈现出旷达阔远的情怀。
作为一位两度援藏并选择调入西藏,最终栖居在藏的诗人,刘萱的足迹走过西藏的神山圣湖、东南西北,她以自己蓬勃的激情构筑了新的生活场域,也以浪漫主义的气质营造了丰厚的精神家园。《西藏三章》是她数年“在西藏”的见证和吟唱,也是她对雪域高原深厚的痴迷和情感上难以割舍的诗性呈现。诗集《西藏三章》以独特的“三章体”形式,把西藏的自然、地理和人文景观并置于这部诗集中,形成一个独特的西藏地域景观图。诗集的篇章布局清晰明了,诗歌以地理坐标命名,涵盖西藏的几乎所有地区。西从阿里“阿里三章”,东到藏东“藏东三章”;北面“藏北三章”“藏北无人区三章”,南到喜马拉雅山和珠峰“珠峰三章”“喜马拉雅三章”。每一章选取最有代表性的风物意象作为视角和切入点,映照出西藏不同地区的自然地理风貌和人文历史景观,而这些代表性的物象集置于西藏这一文化地理诗意的空间,使得诗篇既互为差异又浑然一体。刘萱的《西藏三章》从对西藏地理文化空间的建构入手,又能抽离具体场景通达人生和生命的追问和思索,诗歌以情感的真挚而动人,以抒发坚韧、美好的感怀而彰显其精神担当意识,而透过这些意义背后看到的是一个有情怀和精神气场的个人。
敖超多年致力于文学创作,正如他的小说创作一样,他的诗歌感情细腻,敏锐善感。他在细小的事物发掘生活的廖落和美好,他的诗温柔、安静、恬淡,在淡淡忧伤之中渗透出醇厚的暖意。如诗歌《夜雨》,晚上的雨通常是寂寥的,此时世界肯定是孤寂一片。但作者却有不同的心境,“雨夜/和你邂逅/你的心里总是/一片阳光/你用微笑诠释着/心里的俏丽”,在作者的笔下夜晚的雨是美好的,因为心里的阳光让漆黑的夜也有了光彩,山不动,水不动,是作者的心在动,夜雨也因为积极的心境而变得温馨美好。《写给子夜的心情》写道:“漫长的冬天/刚刚褪去/岁月开始朴素/越过那一半是白天/一半是黑夜的小径之后/每一朵花都竞相开放/散发着不一样的香。”这花香是生命中的永恒之美,温馨着生命中的孤独与荒芜。再如,《穿过草原的思念》“心里的故乡/总是那么远/连接着天边/穿过/风光无限美丽的草原”,这首诗是诗人思念远方的恋人,思念家乡,但在诗的结尾,却提到了风光无限美丽的草原,将诗的意境陡然转换,从思念难过到豁然开阔的美丽景象,这也体现了作者积极乐观的创作态度。
陈跃军这位年轻的诗人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诗歌创作,他葆含着热爱,充满着激情,以赤子之心在诗歌的海洋里遨游,以文字来通达对心灵和现实世界的探查。在本诗集中所收集的诗歌,大多以西藏的地名来命名,由此建构出他诗歌的地域空间,呈现出他对于西藏的至诚至爱之心。察隅、朗县、错那、隆子、洛扎、浪卡子……,这一个个地名串联起的一行行诗句满蕴诗人的挚爱之情,浪漫的想象和郁结的千回百转幻化成一幅幅景象,升腾在诗人的心中,流淌在笔下,让我们得以通过一首首诗歌进入到一个质朴而丰富的内心。在察隅,“思念的河在奔腾”,“朝着魂牵梦绕的地方出发”,“离别的脚步怎么也迈不开”;在普兰,“这是一种不离不弃的陪伴/这是一种望眼欲穿的守望”;在樟木,“本来想和你相守一生,真的没有想过告别”;在定日,“珠穆朗玛,一直想来看看你”;在吉隆,“这个春天让人伤感,我无心欣赏怒放的杜鹃/雪花连成一条哈达,为远去的亲人送行”……陈跃军的诗歌浑朴自然,没有那么多技巧的运用,也没有华丽的辞藻,他把自己的情感放在平实的语言中表达出来。诗歌的背后映现的是一个鲜活的灵魂,陈跃军对人是赤诚的,诗歌的心是赤诚的,朴实而厚重的情感让他的诗歌在灵动中蕴藏着感人的力量。
希贤的诗歌往往用凝练传神的文字,展现了她的生存之思,如她的诗句“生命所有的时态,都呈现在落满灰尘的光柱之中”“那些可能拥有却并未拥有的/卧在冬雪之上/度过不被了解的一生”,映现出苍凉的人生感受和美感意蕴。此外,她的诗歌往往用充满跃动感的意象来建构他的生命之思,“我喜欢行走,/看最美的落日/这并不影响我更喜欢/你奔跑的样子/你跳跃,翻滚双脚/让清晨有了欢乐的律动。”“细雨倾斜/深壑中流淌着月光/云杉浅绿色球果摇晃/岩壁上青草变形为一副哲学面孔/盛满龙舌兰的酒樽已不是昨天那只/不散的宴席顺从了日升日落/顺从了一日三餐和四季”。这些意象的点缀使得希贤的诗歌从寂寥沉重中孕育出单纯澄澈之美,同时,她的诗句在苍凉的人生感受中又生发出不甘和期冀,“去吧,岁月将你押解他乡/我喜欢你仍似湖水的平静”,“一些事物在静静死去/它们永远不会孤单/春天闪耀着光芒”。
马相村的诗歌以情绪的饱满和深沉见长,他的诗歌中亦有对西藏的挚爱至深之情,如诗歌《此刻》中“我要朝有山的地方走,珠穆朗玛在嘎玛沟的顶端”,“我要朝有花的地方走,墨脱的山石榴已开放到世外”。此外,他的诗歌还抒写了对亲人的深情和眷恋:“我们不谈理想,不谈诗歌,甚至不谈/现在和将来/只谈,那些令人怀念的日子/那丝温暖,那段友谊/那种令人泪奔的/你我静好的感觉”。有抒发对女儿的愧疚之情的:“孩子 请你不要抱怨命运/我踏上高原的时刻/就注定今生的飘零/你是步我后尘的使者/只能在远离我的岁月里/失落童年/和蒲公英似的笑容”“孩子 你长大了/而你的父亲已在高原上/随风老去/在一个迷失英雄的年代/我依然背负着强者的行囊/在起伏的群山间/静静看雪。”正如他的诗观“诗人在救赎自己的同时救赎他人”一样,他的诗歌还充满了哲思、超脱、救赎的意味。如《致徒儿》中诗人借着对处在困境中的徒儿的建议展示的是对人生的开解与救赎。“满眼的油菜花儿”、“温暖的春天”、“我们上路吧,天色尚好”, “不要害怕哗啦啦的无源之水/你看,那朵莲花/已在污泥中绽出笑意”“河谷里充满了丁香的气味”,不要纠结于“山上的杜鹃是花名还是鸟名”,都显示出了诗人的超脱的精神境界和对人生的旷达。
陌上千禾的诗很多都与内心的风景有关,她将细微的感受与外界的景观相连,从而照见的是隐微的内心世界。面对繁杂物欲的世界,寻一方净土,安放自己想要的生活与心境,借字词的缱绻通达心灵,展露爱和希望。在《将我的心跳寄给你》《西藏,情人般的木碗》等诗中,诗人以少女倾吐心事的语气表现着旖旎婉转的内心世界,表达着对拉萨、对林芝的深沉爱恋。在《雪未眠》《莺歌的瓷器》《穿过流星中一朵莲花》等小诗中,诗人善用修辞技巧,诗作中赋予西藏的日月星辰、山川景致以人的情感,冲击读者心灵的法门。她的诗歌因“爱与希望”的映现从而流溢着一种心神俱在的愉悦,令人产生强烈的共鸣。《走进楚布沟》、《桃花泪》中,诗人以情入境,情景交融,创造出一种远离尘嚣,自然清氛,和谐无间的“初心”味道,也传达出作者细腻的情思,也让读者在她营造的这种明朗具有浓厚神秘意味和情趣的境界中一再沉醉。
诗人木朵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她的诗歌中有很多独到的意象,这些意象都与藏地特定的地方性经验有关,是从她的生命中很自然地流出来的,在她自由的挥洒中呈现出藏地的自然诗性之美和现代性扩张所带来的郁结。在木朵朵的诗歌中,“夜晚”、“寒凉”、“疼痛”、“焦灼”、“担忧”、“残忍”、“遗忘”、“缺氧”、“等待”、“忍耐”这样的字眼不断出现,在表达对西藏自然之美的赞叹中,也包含着诗人内心的挣扎和希望。其《照片》《唯一能做的》《执念》《头痛》《所以不用担心》抒发了诗人在现实重压下被裹挟而行的疼痛与无助。在这里,“杀死一片海的眼神”、“空茫的留白”、“发着寒光的满天星斗”、“沉甸甸的石头”、“北风一路向南”、“不断的挣扎”、“焦虑无限放大”,它们隐喻一种超脱不得、负重而行的人生状态,显示了内心的挣扎和焦灼。但经历了生活的磨炼与岁月的沧桑,即使有时“哭泣”,甚至“遗忘”,但“却没有丢弃”,这表明在生活的创伤面前,诗人会反抗心灵的奴役,选择承受并自我拯救。生活的沉重使得诗人精神疲惫,但烦忧会消解在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里,那沉重的叹息也将随风而去。《回到西藏》《飞》《老西藏》《高原的天空》《窒息》《加若拉山口》《卡若拉冰川》《浪卡子》《夜幕下的羊卓雍湖》等诗歌中自然景色的浪漫描写,在不经意的流淌中,抵达了举重若轻的艺术化境。
诗人德西以独有的言说方式建构她的诗歌世界。在其诗歌创作中,抒情与叙述并置,并巧妙的融入民族元素,使诗歌的纹理有着藏区的生命性的脉动和文化记忆。朴实的文字间不仅仅是对自己情感的抒写,更是对民族文化、对藏区故土、对人生情感的深刻体味。《酥油灯里的阿妈》《阿妈的佛珠》《归来》等诗歌中对于阿妈离世的苦痛以回忆性的话语诉说,“酥油灯”燃起的那一刻,诗人似乎与阿妈再次重聚,由“酥油灯”这个意象铺展,灯下阿妈温暖的面庞和身影构成诗人记忆里的图景,一切仿佛同维米尔油画记录的瞬间一般宁静而永恒,并与现实记忆交叠。而“酥油灯”燃灭的一刻,“在盛满梵音的酥油灯中,在最后一盏灯燃尽的时候,天空飘过一阵阵雨,落下刚好冲掉脸上的泪水”,故事性的话语却有一种锥心的苦痛,形成于文本外精神世界与现世的对话,产生一种不可言说的张力美感。《澜沧江的爱情》《类乌齐伊日大峡谷》《可是你终将是我错过的情人》等诗歌置身于藏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从中焕发出奔腾的生命的激情。诗人德西以对故土、对藏区文化、对自我个人体验进行诗性写作,灵动流丽的语句交叠、色彩交叠、意象交叠充盈于其写作想象空间之中,创造了属于诗人自我的诗歌艺术空间。
咚妮拉姆的文字如同冬日的一米阳光,总能给予人以温暖和慰藉。这种温暖记录在缓慢流淌的岁月时光中,诗人缓缓以温柔的语气叙述着来自母亲怀抱的思念之情、来自故土直抵内心的清香、来自抗击疫情期间祖国、人民、英雄逆行者们让我们为之动容的点点滴滴。诗人咚妮拉姆的《阿妈,别哭》感情充沛而节制,通过一幅幅画面,描写了母子间的深情。诗人对拉萨有着深沉的感情,《想念拉萨》中包含着诗人的乡愁情愫,在一种平静的叙述中,精心为我们营造了拉萨神秘的画卷,这种画卷不是全景式的,而是一种点状勾勒,诗人寥寥几笔“空气”、“天空”、“小城”、“风”、“格桑花”、“布达拉宫”跃然纸上。除此之外,诗人关注时事疫情,在抗击疫情期间发表了大量正能量的佳作。《我们的湖北》《三分钟》《花之天使》《逆流而上》《口罩》《元宵2020》等诗歌里,诗人把饱含关怀的目光投向了疫情下的中国。作为一位诗人,她在生活的真实与文字的诗意之间,找到了恰切的视点和聚焦,缔造了她诗歌可贵的底层视角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在文字的背后,有一颗温柔善感和充满悲悯的心。
张燕梅善于以纤秀的语言吐露内心的真我,情感的朴质和抒写的温婉构成了其诗歌的主情调。《雪山上的月亮》中月亮柔美的光、暗淡的星星、积雪缠绕的雪山似乎构造了一副空灵、柔美却暗含孤寂的雪域世界,在这种氛围之中,内心的情感总是伴随环境喷薄而出,乡愁在此时得以流露,作者借雪山寂寞空灵之境忆起故乡的“桂花香”、“枫叶红”、仿佛于此时听闻母亲对自己的呼唤,以“月”为笔触,置放如水的思念。诗人于此诗之中将寂寞的月光、雪山与故乡的桂花、枫叶、母亲的呼唤并置,月光和雪山的洁白与桂花的的灿黄、枫叶的艳红形成画面上的色彩冲击,在两种图景的对立之中使思念之意味得到自然升华。诗人张燕梅似乎很善于将自己的个人体验巧妙融入她的诗歌创作中,她以个体的感受写在西藏日常生活的图景,似乎更能发现掩于氆氇里的笑颜,体会到“冰川雪峰,戈壁瀚海”世界中的草长莺飞,杏花春雨,目睹藏区春天里独有的桃花映雪峰之境,这种异乡的陌生化视角将西藏带入诗歌之境中,将生活的经验内化为诗歌创作的灵魂性存在,诗歌多了几许真实,生活亦多了几许诗意。
女性诗人往往擅长以女性的柔韧、细腻、哀婉展现对生活的多元思考。除上面论述的几位诗人外,其他几位女性诗人的创作也各具特质。邱培秦将对天地万物和生命的细微都呈现在那纤弱而又有力量的诗句中,有着神秘、悠远、空灵、苍凉之感。如《光》中对生命的思考,“渡,迷惘的魂灵/迎接千年的梵音/在心中种一颗菩提/待到涅槃重生时/便是,直抵天穹之外的觉醒”。普渡迷惘的亡灵,佛光漫天,众生皆得到了度化,充满了神秘、空灵的佛教氛围。此外,她的诗善于营造意境,如《霞光》《风雪牧归人》等诗歌中的诗句,“霞光落水的刹那/蜿蜒的湖泊/流水宠辱不惊,泣血/染透天地”“雪山起伏连绵,黑白交融中/一纸水墨,晕染牧归的心”,这些画面有着强烈的冲击感,永恒的灵魂在这里飙升。萨娜吉的诗歌映现的是对美的纯净追求。在她的笔下,美是游荡在蓝天上的几缕白云,是依偎在山间的几丝残雪,是落日余晖下的雅鲁藏布江,更是雪山荒野下抱团取暖的小野花。世间一切温暖皆源于对美的热爱,向往和追求。丹增曲珍的诗歌呈现了女性的细腻敏感,敏锐的心灵与外在进行着对话,在稚嫩的诗句中呈现着对怅茫人生的思考,在孤独迷失中有着对温暖美好的期冀。此外,作为军嫂,袁豆豆的诗歌中尽显了一个军嫂对丈夫的支持和浓浓的爱意,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诗集中收录的诗人毛惠云、嘎玛旺扎、李德林、安拉加、才旦多杰等的诗歌也尽显独特的魅力。毛惠云对现实生活细节和美有着敏锐的发现,他与大自然进行灵魂的沟通,生命的力量与自然的平和便随着这份喜爱自然而然融入到他的诗歌创作之中,独特的生活体验在其笔下得到有机舒展。他对生活有着自我的思辨,由此生发出被忽略的自由之力,无论从其诗歌的语言构造、结构形式亦或抒写对象,还是从诗歌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倾向来看,其诗歌中往往具有一种自由的生命空间,如他所说:“从小的习惯除了秩序我别的一直在保留”。在其诗歌中,有着敏锐的发现和细致的抒写,生命的力量在悄悄蔓延生长,这可以说是其诗歌的特有品性。嘎玛旺扎的诗歌诚如他的诗观,是最赤诚的坦白,他以深沉寂寥的文字搭建起独特的诗歌天地,其诗歌的中心意象是秋天、秋叶、青稞、黄叶,这些意象反复出现在他的诗作之中,既展现了耕种的希望和收获的喜悦,又有秋尽之后的寂寥,和从寂寥中生发的希望和挣扎。透过这些意象,呈现出的是诗人对土地的深爱,内心的困惑和挣扎。李德林注目于现实社会人生,诗句中满蕴的是对西藏的拳拳之爱和对母亲、大地和故乡的深情,在含蓄内敛的诗句中映现出诗人敏感而悲悯的心灵。安拉加在其诗作中展现了对故乡的眷恋和离开故乡的孤独,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才旦多杰的诗歌不仅瞩目于个体心灵的思考,还将笔触关注社会现实,呈现出鲜明的理性思辨色彩。
21位诗人的创作风格各异,呈现出藏地书写的多元风貌。在这些诗人中,虽然一些年轻诗人的创作还显得较为稚嫩,他们的一些创作流于表层的抒写,或者仅局限于个体的悲欢和小情小爱之中,缺乏深远的灵魂探求,诗艺还需更进一步开拓,但从他们的诗歌中可以照见的是生命的激情和对西藏的挚爱。置身于雪域高原,置身于这片圣洁的土地,诗人们采撷枝叶果实,采撷风月精华,孕育成一句句诗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地理的诗性空间,涓涓细流汇聚而成大江大河,以集体性的力量共同呈现了对雪域大地的抒写,对生命的关切,对存在的哲思,对永恒的追问。诚如陈跃军所言:诗歌是灵魂的歌唱,诗歌不朽,灵魂永恒。那灿烂的格桑花盛开在喜马拉雅的春天!

徐琴,女,陕西汉中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藏族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