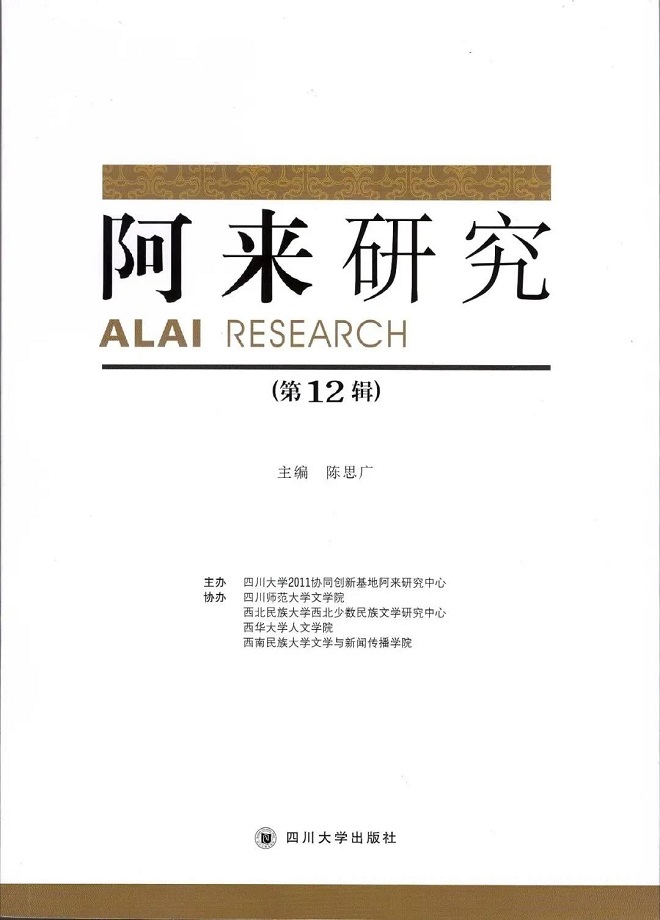
在经历了上千年失语、两三百年“他者”书写之后,作为第一次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康巴作家群的崛起被阿来称之为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然而目前学界关于单个康巴作家、单部作品的文学评论不少,但是从整体上探讨康巴作家群集体崛起的综合性研究尚不多见。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而言,在整体层面上,李德虎、黄群英、雷昌秀、李长中等学者陆续就康巴作家群的生态审美体验、地域特征、空间化书写、多元化特征等多维视角展开了分析。其中,李长中立足于人类学、美学的综合视角,提出当前学界以地域文学为标识是对康巴作家群及其文学的误读,他认为康巴文学不是张扬的对抗美学,而是强调多元文化/族群“和解”的美学表示,预示了多民族文学发展某种新的可能。的确如此,康巴作家群的诞生有其独特的多民族文学协同发展之路,改革开放40年来康巴作家群的形成有其特有的语言表达、文化惯例、行为指向的互动与演变机制。本文拟从发生学角度,分析以“康定七箭”为代表的康巴作家群的形成与崛起路径,试图在整体性层面揭示多民族文学协同发展的特征标和特征码,探索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本土化解读。
一、从无到有:康巴作家的诞生(1978-1990年)
1983 年,第一位康巴作家意西泽仁出版当代藏族作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大雁落脚的地方》,开启了康巴作家自我书写的新时代。而孕育康巴作家诞生的大环境因素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康巴作家诞生的基石是历史上多元文化的积淀。正如石硕所说,康巴地区作为一个民族迁徙走廊,其民族的流动性很大程度与其开放性相关,正是由于开放、由于有新的民族成分源源不断地加入,才带来了康巴地区民族的流动性及各民族间的不断接触、互动与交融。而正是这样一种多元文化的不断融合,才培养和孕育了康巴作家的诞生,有力地促进了多民族文学的协同发展。徐其超就曾经指出意西泽仁是以母民族血缘文化为根基的“文化混血”型作家,意西泽仁的诞生地康定,既有汉藏“交叉文化”的影响,又有印度、英国等东西文化浸润其间,正是这样的文化环境孕育了康巴作家意西泽仁的诞生。
其次,对康巴作家的诞生来说,更为直接的影响就是改革开放时期思想解放的思潮。意西泽仁在《松耳石项链》代后记中提到,他觉得自己的创作生命,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徐其超曾就70年代末80年代初四川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蓬勃兴起的大环境作了专题论述,他介绍了各级党政机关贯彻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情况。而在文化机构的设置上,甘孜州创办刊物《贡嘎山》,西南民族学院、康定师范专科学校等高校设立少数民族高等教育体系,《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开设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专栏,吸引了大批各民族的专家学者参与其中,对康巴文学的起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代康巴作家的诞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荒芜边地的异军突起,而是始终与当代中国文学地图形成共振。1969年的意西泽仁同样被席卷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治洪流所裹挟,来到泸定偏僻的山沟插队,继而又前往更为偏远的色达草原做宣传干事。文革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浩劫,一方面让他从知青那里借来了许多诸如《战争与和平》的书籍进行大量阅读,为今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另一方面也让他深刻意识到城乡以及偏远草场之间的巨大差异,对牧民的深切同情,直接促使他拿起笔开始进行文学创作。
作为康巴作家诞生的标志,意西泽仁《大雁落脚的地方》中的所有短篇小说都定稿于1980-1982年之间,写作地点主要集中在北京雅宝路作协讲习所、康定和昆明三地,作品既受到当时文坛主流的文革文学、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影响,又有藏族小说创作独特的手法。可见作协少数民族作家讲习所的学习、多民族作家的交流对于康巴作家的诞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关键的是,以此为契机,在边地这样一个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下,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使作家们得以更好地吸收多元文化并与之对话。徐其超以“背负草原,面对世界”为题归纳了意西泽仁的小说创作论,笔者认为这一标题相当有概括力。立足于草原、民族自我书写的同时,又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潮中,身处多元文化交汇的边缘之地,拥有更多突破陈规的便利,更为开放地吸收苏联、拉美、美国等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是意西泽仁作品鲜明的特色。在其随笔中,意西泽仁记载了与沙汀、艾芜、周克芹、阿来、马识途、陈之光、流沙河、李焕民、梁上泉、土家族作家周辉枝、回族诗人高深、木斧、蒙古族伊德尔夫等各族作家交往的经历,多次提到老一辈作家对刚刚诞生的康巴作家的关怀与指点,勾勒了康巴作家诞生时期多民族充分交流的公共空间。
对这一时期的康巴作家来说,意西泽仁绝非个案,他的创作道路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而意西泽仁、列美平措这些康巴作家的诞生,又对当地的文学爱好者起到了相当大的引领作用,逐渐形成了以《贡嘎山》为中心的甘孜文学圈。伴随着全国文学的大热潮,仅甘孜州给《贡嘎山》杂志社来稿的作者就超过千人,许多康巴作家脱颖而出,开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在《阿戈的老屋》一诗之后,梅萨曾经描绘了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康巴作家们在列美平措的老屋,跟随中国文学的主流意识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尝试“非非”、“先锋”、“朦胧”等各类派别的写作,大谈马尔克斯、塞菲利斯、黑塞、卡夫卡、海子、顾城、北岛、张承志、“第三代”的情景。
由此可知,诞生于80年代的康巴作家,虽然初涉文坛,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属于刚刚起步阶段;但是他们一方面与当时的全国文学地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保持同步;另一方面凭借自身多民族族源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积淀,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思潮影响下主动吸收世界各国的多元文化,融合多民族的自身资源和特色,为下一阶段作家群的初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康藏研究新热点与“康定七箭”的初步形成(1990-2011年)
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文学热潮逐渐降温,康巴作家文学创作趋于冷静。但是到了2004年,二十多位康定作家都在名字前面冠以“康人”二字为标识,集体创作了中国首部长篇接力小说《弯弯月亮溜溜城》,连载于《甘孜日报》,以“康定七箭”为代表的康巴作家群初具规模。
从90年代文学热降温到2004年康巴作家群以“康人”为名的集体亮相,笔者认为,短短十年间康巴作家群的形成与康藏研究新热点的兴起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甘孜州藏学研究所等康巴研究中心的建立,涌现出一批以格勒等人为代表的康巴研究专家,整理出版了多种有关康区的文献和一系列康巴研究成果。特别是2000年以后,学界有关康巴地区研究呈现出研究视野拓展及研究路径改变等明显的新趋势,使得康巴地区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新进展。
正是在学界对康巴研究的热切关注之下,大批民国时期乃至更早的康藏史料研究得以陆续出版问世,康巴学术新热点的兴起,为康巴作家群的形成奠定了学理依据,开拓了康巴文学书写的新领域,促使康巴作家以史诗的方式、民族自觉的意识,重新建构自己民族的历史,通过作品再造文化记忆,对康巴作家群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达真的《康巴》为例,这部着眼于近代风云跌宕的康巴历史的长篇小说,创下首版销售突破3万册的记录。阿来在《<康巴>:民族融合的人性史诗》一文中,评价《康巴》是一部藏人用多元的视角深度呈现康巴“秘史”的长篇小说,作品以云登格龙、郑元龙、尔金甲这三位不同宗教背景的主人公的故事为主线,描绘了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回教、基督教等多种宗教在康区多元共生、互相融合的全景式历史景观图。作者借云登土司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康定这座城市的看法:传说中的康定是诸葛出征时一箭成名之地,又是格萨尔王烧茶的地方,名副其实的交汇地。如今这里又集中了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汉地的儒释道的庙、坛,康定的包容性就如成都的一道名叫杂烩的菜……
关于打箭炉的传说,格勒认为这一传说与史实不符,《三国志》及其它史书中均未记载在打箭炉造箭之事,诸葛亮并没有西进入康定,最多只可能派人在康定办理军粮和军务。那么达真等康巴作家为何会对类似这些民间传说青睐有加,积极地吸收借鉴,并不断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
笔者认为,作为“第一次自我书写者的集体亮相”的康巴作家群,之所以被阿来称之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其意义正在于此。正是康巴作家们从本土的立场,对于民间史料的采集、发掘和再创作,与我们所谓的“正史”形成互补,才体现了厚重的历史多样性,展现了民族历史记忆重组的方式,成为重拾康巴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共同体的重要环节。以格绒追美的长篇小说《隐蔽的脸》为例,就是一部藏地村庄历史演绎的史诗。格绒追美的小说集《失去时间的村庄》和《隐蔽的脸》都是有关故乡藏地村庄的描绘与追忆,藏地村庄的民间传说和地方记忆成为他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
而对于康定这座城市的描写,尹向东在小说集《鱼的声音》中对多元身份冲突的寻求,则为我们展示了康巴作家对于当代文化、文明冲突等问题的现实主义思考。在《晚饭》这部作品中,尹向东借宋瑜之口,表达了从上海归来的康定人的烦恼。在上海的时候,走康定路成为她确认、寻求身份认同的一种途径;而回到康定,她却发现,自己多年来自我建构的康定人这一身份认同的自欺性和虚幻性,现在康定已经不再是她想象中、记忆中的那个康定。故事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宋瑜最终选择了死亡来结束多元身份认同的冲突和焦虑。不同于黄洁认为这体现了作者较强的悲剧意识,笔者觉得这是作者对现代性、全球化视野下多元文明冲突的看法,是作者对于康巴多元身份的一种表达。
正是在康定这样一座交汇之地,以“康定七箭”为代表的康巴作家笔下,不同文明不再是彼此冲突的对立面,而上升到对人类文化交流、多元身份融合等问题的关注点上,使得康巴文化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多元并存的状态,这样一种文学康巴的企图重塑着康巴社会的文化共同体,为正式形成“和而不同”的康巴作家群奠定了基础。
三、“和而不同”:康巴作家群书系的出版(2012年——至今)
早在2013年,参与“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的与会评论家就一致认为,康巴作家群形成了具有浓郁康巴地域特色和鲜明艺术风格的作家群体,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惊喜和独特的审美经验。
以“康巴七箭”为代表的康巴作家群的边缘崛起,与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化、宣传政策不无关系,得益于甘孜州等地方政府有意鼓励与扶持文学生产的发展策略。在国家层面上,2012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中国作家协会正式推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这项工程得到了中宣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进一步加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从培养人才、鼓励创作、加强译介、资助出版和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在甘孜州层面上,2011年以来,在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文化强州、繁荣文化艺术创作的政策指导下,甘孜州委宣传部把康巴作家群作为重要品牌,在资金投入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正式启动“康巴作家群”书系出版工程,四川省作协领导和甘孜州委、州政府领导人总策划和编委;甘孜州人民政府设立文学艺术奖等。在文化机构上,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全国格萨尔办公室、四川省巴金文学院、甘孜文联、玉树文联、昌都文联和迪庆文联、《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30余家主流媒体等文化机构参与推进。而笔者认为最能代表康巴作家群的特色就是“和而不同”的创作风格。
首先,“和”体现在康巴作家群创作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多元文化的融合观。有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作家本身混血背景所导致的结果。而笔者认为,血缘的融合或许是原因之一,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作家在长期多元文化交流影响下产生的多元文化意识。李绍明、任新建指出康巴地区,在一个民族地区内就包含如此多的文化形态, 在世界范围内都可算极为罕见。更为难得的是康巴地区的各种文化彼此互不干涉, 各民族都能保持自己固有生活方式与习惯, 这使得康巴地区成为藏区和全国中文化多元和谐共存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也造就了康巴人的开放意识和宽容理念。如此多元的文化景观无疑为康巴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最好的素材,成为康巴作家文学创作关注的焦点所在。这样一种多元文化融合的状态,在尹向东的《风马》中以“命名”为关键词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康巴作家面对多元文化的冲突不仅游刃有余,而且凭借汉藏文化的多元融合而显现出独特的魅力。在尹向东的《风马》小说中,刚从草原流落到康定的兄弟俩,便被康定城里的流浪汉稀里糊涂地赋予了“仁泽民”、“仁立民”这两个汉文的名字。一般来讲,给人取名,你的名字只能在特定语言的有限词汇里加以配置,而且根据文化惯例,名字的选择更是慎重的行为。然而,《风马》主角名字的得来,不再伴随着与生俱来的身份,却是如此的随意和漫不经心。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样一个糊里糊涂得来的名字,却伴随着这两兄弟在康定数十年的生活,就算离开康定,回到草原,他们依然是用的是自己的汉名名字。正是通过对汉文姓名的认同,康巴作家在作品中实现了多元身份的构建。而这一构建的过程中,也有身份的错置和交融。比如,仁立民喜欢上了卓嘎。卓嘎的皮肤非常白皙,爸爸是汉族,妈妈是藏族,他们俩讨论起各自的名字和身份:将藏族的姓名等同于藏族的身份,汉族的姓名等同于汉族的身份,而这一身份认同又因各自的外貌特征而形成矛盾,令人感到身份的错置。紧接其后,作者却安排了一盏电灯震惊了所有的“康定人”的情节。在作者的笔下,康定人成了代名词,再也看不到藏人和汉人的刻意区隔,在这汉藏的边地,形成真正的多元身份的认同和融合,形成康巴作家独有的多元文化视域。不仅如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从作家笔下描绘的汉藏习俗的交融,来体会这样一种多元文化的特质。尹向东详细描绘了兄弟两人第一次跟着锅庄主清明节上山上坟的情景。这样一种将风马旗装饰坟头、点燃“斯折”的清明节习俗,可以说是康定人的首创。倘若放在汉地亦或是草原的任何一地,都会显得如此的突兀和怪 其次,“不同”体现在康巴作家群创作风格的多样性上。格绒追美常常在作品中解构原有固化的思维模式、叙事风格,用梦幻般诗意的语言,向作家这一权威身份本身挑战。在《青藏时光》这部散文集中,格绒追美将自己的创作隐喻为“像个偷窃者耸直双耳四处听闻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一转手就把人家的故事变成了自己的‘作品’”。他如此描绘康巴作家多元文化身份认同:“语言是个好玩的东西,它让我在两种迥异的世界里不断流浪、寻找活着离开”,他在《荣归故里》这篇散文中,创造了一位衣锦还乡的藏人,当他离开村子前应邀在欢送会上讲话,讲出的竟是异族的语言,在这里语言成为一种符号,丧失母语成为一种隐喻,叩响了作者对多元文化身份认同的反思。在《青藏辞典》这部长篇小说中,格绒追美更是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辞典的编撰模式,打破了时间、疆域的限制。作者在作品的开头坦言:“这是一本来自青藏的个人辞典”。虽然他自称“不合格的编撰者”,但是却希望除了显现作者自己的心灵轨迹外,更为重要的是,能要遥望青藏高原隐秘的智慧河流,沐浴到来自雪域的灵性光芒。在个人访谈中,格绒追美坦言《青藏辞典》是一个实验的文本,它并不在意的都是构建一个完整的东西,而是希望通过非常自由的形式,把作家的精神感悟从文本中流淌出来。格绒追美以其多元文化视域,编撰着《青藏辞典》,正如他在“边界”这一词条下所写:
“人类总是确定各种边界:你、我,民族、国家,艺术,教派,内和外,上与下,小说和散文,传统与现代,物质与意识,等等,只要存在边界,人类的狭隘永难突破。边界消失,人类终将获得深广的智慧,并与宇宙相融一体。”
正是通过这一打破边界的尝试,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格绒追美实现了从边缘向中心的突围,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创作风格。
而雍措笔下的《凹村》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乡土叙事风格,雍措对大渡河畔故乡鱼通深深的思念,化作凹村的一切让人历历在目,一如沈从文先生笔下淳朴恬静的湘西风俗画卷。单单是凹村的风都是有故事的:凹村的风养活了借风传信的张溜子,是收割麦子时节农人们的期盼,是杨二的媒人,更有着治愈缺失的疗效。雍措的行文是如此的简洁和独特,没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夸张,却总能显露出家乡鱼通的文化传统赋予雍措的与众不同的叙事视角。鱼通在文化上属于嘉绒藏区,是原始苯教的发源地,后又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而最与众不同的是鱼通地域的语言有“两村相邻,言语不通”的特点,每个村庄的小区域内都有自己独特的口语系统,当地人称之为地脚话。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方言,使得雍措的作品总能产生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体现出独特性的叙事手法。
综上所述,作为多民族文学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以“康定七箭”为代表的康巴作家群在改革开放40年中,先后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诞生期、初步形成的发展期和正式亮相的崛起期,其创作始终与多民族文学的协同发展同步,呈现出聚焦地方记忆、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特质,对探索多民族文学协同创新发展和建设文化共同体有其独到的意义和价值。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2辑

俞蓓,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讲师,在《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国际汉语教育》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主编《秘书英语写作》、参编《新编民间文学教程》《民族风情》等书籍。

朱霞,女,陕西武功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7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与藏族文学研究。先后主持完成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发表相关研究论文数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