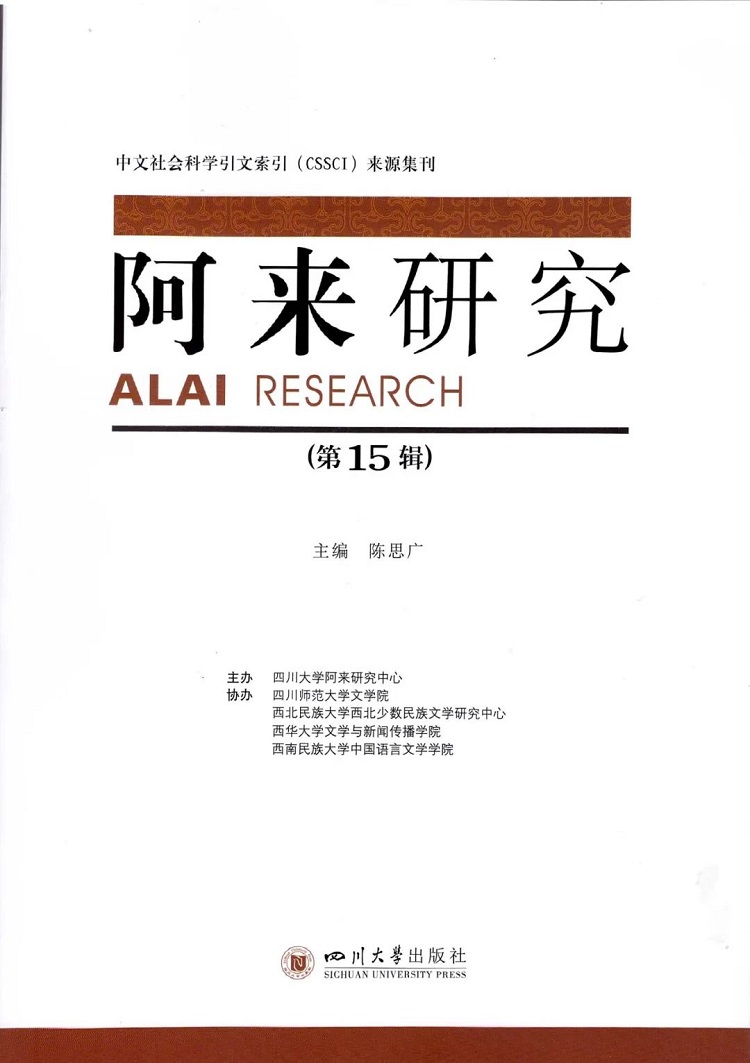
梅卓是中国当代文坛成绩斐然的藏族作家。她在诗歌、散文和小说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小说创作,在题材方面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 一些新的艺术景观。其中,长篇小说《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对生活在草原上的藏族部落历史的艺术描述,最能够体现她对当代藏族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在当代藏族文学领域中,以广阔的历史风云为背景来描述草原部落历史变迁的小说,在梅卓之前还不多见,益西卓玛的《清晨》算是开拓之作。但《清晨》深受阶级斗争意识的左右,只是从革命的角度反映草原人民与领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还不能从更为广博的生活中表现草原部落的生存情状和人们的爱恨情仇。而梅卓的《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则表现出了更为阔大的艺术视界,让读者能够从中探视生活在草原上的“独特的群体”的生活风貌。当然,梅卓并没有在小说中刻意渲染独特性,而是重在表现生命存在的无奈与荒谬。这种主题取向使其作品超越了地域、时空,拥有很强烈的艺术魅力。《月亮营地》就是这样一部佳作。
一
对于人的命运的不确定性的认识与反映是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一主题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和中国先锋小说那里表现得相当突出。在这类小说中,个体短暂的一生充满了瞬息万变的不确定因素,人真正成了飘浮在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命运成了一条难以把握的绳索,在人们茫然无助的失措中牵引着他们走向生命的尽头。这样的境况的确让人哀伤绝望。但毋庸置疑,它也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人的存在的某些本质规定性,比如人生的不确定性、生命活动的偶然性、未来前景的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性,从而在为自己的生命长吁短叹的同时,清醒地寻找存在的出路与意义。这无疑也是此类小说所具有的一个相当重要且颇具价值的审美维度。梅卓的《月亮营地》虽然在艺术格调上没有现代主义小说那样冷峻、坚硬的质地,但它在主题层面上,也从侧面揭示了与之相同的存在境遇。在“月亮营地”这个充满了浪漫气息的地域,一群有着自己文化习俗和生命理念的人们,以其存在方式,为我们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普遍主题,那就是人的命运的难以把握与掌控。
我们如果仔细梳理《月亮营地》中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就会发现,其中布满了无法把握的偶然因素。这些偶然因素往往会出其不意、难以预料地影响或决定人物的生活命运,使得他们不得不偏离早已规划、设计好的人生途径,从而走上一条与自己的意愿相背离的道路,也由此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无奈与痛苦。这样一种叙述模式或人物命运的安排可以说是《月亮营地》这部小说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审美追求。正是这一审美追求,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小说的艺术魅力,成了彰显其艺术吸引力的一个“绝妙武器”。阅读这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活动于这部小说中的人物算不上很多,人物之间的关系也算不上纷繁复杂。按理说,这样的长篇小说如果没有一些显而易见的艺术高妙之处的话,往往会流于平庸、简单,成为流水账似的记录。但《月亮营地》并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并不复杂的人物身上蕴藏着能够激荡读者生命体验的因素,比如偶然性对人生轨迹的改变、未来人生的难以把握等,这些因素就深深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它使我们在检视虚构世界的人物的命运时,能够感同身受地体味自己的生命痛楚和无法摆脱的无奈、伤感。
甲桑是这部小说着力塑造、刻画的一个人物形象。这个人物形象拥有一副强健的体魄和勇武的胆气,他能在每年的登山朝拜中获取头名,从而得到活佛的赐福。在广阔的草原上,像他这样的男子汉应该能够拥有理想的生活,获得崇高的敬意。但是他的这些先天的优越条件并没有带给他应有的荣耀。在小说中,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甲桑都生活在众多的难以理解的偶然事件中,他的生命流程就是由偶然事件决定或组成的,他的喜怒哀乐也都是在偶然事件中释放流溢的。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但他几乎每天都能见到自己的父亲。这对一直渴望知道父亲是谁的甲桑来说实在是一个残酷的现实,而正是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得他的一生遭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从而让他无法直面自己的人生。
他与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打赌,偶然中杀死了无意伤害他们的大白熊;他恨情人绝情地抛弃了他,却不知道她为他生了儿子;由于不明真相,他在无意之中误杀了他的同父异母妹妹……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发生的。在误杀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后,他一度把自己封闭起来,试图通过宗教行为来完成心灵的救赎。这个原本坚强的男人在生活面前竟然成了一位无言的承受者,人生的悲哀就这样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人生图景,但这还不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东西。在审视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我们关心的并不是他所面对的那些事与愿违的不幸遭遇,尽管这些不幸遭遇确实能够激起包含着人生存痛楚的生命波澜。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些不幸遭遇的诱因,因为这些因素是藏匿在不幸遭遇背后的悲剧动力源。那么这个悲剧动力源是什么呢?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及的那样,这个悲剧产生的动力源就是不可预知的偶然和不可预测的命运之神。这样说听起来也许有些玄秘,但这的确是现代人自我意识、主体意识觉醒后感受到的最为惊心且难以回避的生命感受。作为有理性思维能力的人,没有谁不想让自己的生命轨迹在自己设定的轨道上延续下去,没有谁不愿意让自己的人生在掌控中走向辉煌,但残酷的现实却往往使这些主观意愿显得黯然失色、柔弱无力。很多时候,一个个体即使有强大的生命活力,也无法躲避来自生活的意外打击与折磨。甲桑的生活遭遇就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寒气逼人的冷峻事实。人类的这种境遇在西方现代主义文艺作品中已经得到了反复多样的描述和展现。这种历史性的存在境遇会发生在任何地域,即使在像“月亮营地”这样山高水长的浪漫之地,也同样不断地演绎这种的悲剧。当然,这一切首先都是由作为现代人的作家的心灵感受和生命体验决定的,因为正是作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其对人的存在的荒谬性有了清醒、深刻的认识,从而把这种感受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传达了出来。甲桑身上发生的一系列无法预料、难以躲避的荒诞事件,是甲桑生命存在的阴影,也是“月亮营地”里的众多个体生命存在的阴影。推而广之,它其实也是现代生活留给孤独、无助的现代人的阴影。
在“月亮营地”里,我们还能够从其他人物的命运遭际中感受到这种挥之不去的阴影。比如甲桑的父亲阿•格旺。这个地位显赫的贵族首领表面上风光无限,其实是一个被外在力量牵着鼻子、找不到自我的弱者。他原本有一个对自己忠贞不渝的恋人,而他本人也对她情有独钟,但权力的诱惑却使得他鬼使神差般地放弃了这段美好的感情。他自以为把人生交付给了最可靠的权力与地位,却事与愿违。一次连他也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权衡的选择,把他的人生带上了充满痛楚的旅程,而所有这些痛楚,他只能在心底独自承受,甚至都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亲朋好友。权力、地位的光环无法掩饰其内心的寂寞与哀伤,也无法消除情感的折磨与煎熬。更让他感到悲痛欲绝的是,他的亲生儿子从来就没有尊重过他,甚至变成了杀害他女儿的仇人。他曾经为拥有权力而自豪, 却为无法保护部落的安全而绝望;他为了权力放弃了爱情,却无法摆脱那份真爱的呼 唤……这是一个痛苦的生命,他一直生活于人性缺陷的阴影当中。他表面上掌握着自己的生命轨迹,其实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精神上,他都没有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他的情感是无根的浮萍,寻觅不到可以停留的水域;他的精神是迷失方向的船只,找不到可以停泊的港湾。他是一个情感的流浪者、精神的漂泊者。
《月亮营地》通过这两个主要人物的生命历程,艺术地揭示了人的尴尬境遇,呈现了人的存在的无奈和绝望,确实让我们感觉到了生活的荒寒与凄冷。当然,这并不是这两个人物的不幸遭遇留给我们的唯一的感受。在感到人的存在的无奈与绝望的同时,我们也能从他们的一些主动选择和内心隐秘意识中感受到人世的温暖与活着的希望。甲桑的一生是破碎与幻灭的一生。在他的一生中,许多事情都不是他主动选择的,他是被外力主宰的一个不幸者,但他对生活毫无怨言,在任何情况下都默默地承担着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当无意中杀了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后,他主动地接受了这一惨烈后果带给自己的精神折磨。他在悔恨中把自己封闭起来,以镌刻玛尼石的方式来为自己的暴虐行为忏悔。他的这种过于自责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了存在于困境之中的人的勇气与力量。它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无法避免生命之中的那些意想不到的不幸与痛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意义,成了行尸走肉。能在不幸与痛楚的重压下勇敢地承担生命的重负,本身就昭示了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甲桑破碎的一生的确令人唏嘘不已,使我们深感生命个体在强大外力挤压之下的柔弱无力,但他的那种勇于承担的精神也让人们从灰暗中看到了希望的光亮,这也是作品呈现给读者的希望之光。即使在阿・ 格旺这个令人生厌的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生命挣扎的力量所在。尽管无法摆脱权力 欲望的诱惑和身份地位带来的荣耀,也不愿意损坏自己的声誉和颜面,但他在内心深处仍无法忘怀曾经的恋人,也无法原谅自己对她的伤害。在情感世界里,他一生都无法做到坦然自若,一直处于自责的煎熬之中。也许我们在情感上无法原谅他的始乱终弃,在伦理道德上要谴责他品质低劣,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他还不是一个泯灭了良知的 人。他的生活逻辑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复杂,感受到了情感的脆弱,体味到了命运的不可捉摸,而他内心翻滚奔涌的悔恨之意,也使我们看到了人性趋向良善的可能。
二
与人所面对的外部经验世界相比,人的内在精神世界要复杂纷繁得多。如果说人的外部经验世界是一汪池水的话,那他的精神世界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大海。现代心理学已经证明,这绝不是艺术化的夸张,而是一种科学事实。这是自现代以来人对自身认识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它又一次表明了人的存在的复杂性与心灵世界的难以预测,正是这种突破性的科学认识使得人类开始探究自身深邃幽远的内心世界。除作为一门学科的心理学对人的心理、意识进行了大量精细的研究之外,现代艺术在探索、开掘人的心理、意识方面,一直走在其他领域的前列。当然,现代艺术对人类幽秘深邃的心灵世界的探究方式和路径与科学研究是不一样的。艺术不求科学上的精确结果,它讲求的是通过多样的手法呈现人心灵世界的幽远深邃,并以此来揭示人的存在的复杂多面。在文学领域,对人的心理意识的艺术剖析展示最为充分与广泛的是现代主义小说流派中的意识流小说。从那些典型的意识流小说中,我们不难感觉到人的精神世界的广袤阔大与复杂多变。即使不以人的意识流为主要表现对象的现代作品,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呈现人的隐秘复杂的精神世界,从而在超越客观现实的层面上认识人的存在的复杂多面。《月亮营地》虽然不是意识流小说,也不是那种以人的心理活动为关注重点的小说,但其中穿插的那些剖析人物的内心隐秘活动和精神状态的片段,却仍然可以为我们展示人的像河水一样奔流不息的内心世界。具体来说,在《月亮营地》中,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为我们展示了人的内心世界的躁动不安,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阿•格旺的心理刻画体现出来的。在小说中,阿•格旺是一个地位显赫、颇具权势的贵族老爷,这是他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外部形象。但这仅仅是他的一个侧面,是人们看得见的一面。在另一面,在不被人知的那一面,他却是一个精神的痛苦者、灵魂的愧疚者。正是这隐秘的一面,更能揭示其形象特征,表现人性的复杂。
独自一人时,就是他内心感到痛楚的时候。这种痛楚的主要体现是,他无法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心安理得地面对现实。他深爱着自己的初恋情人,却在权力的诱惑下选择了另外一位女子,看到昔日的恋人辛辛苦苦抚养他的儿子,他深感内疚自责。作为一个有情人,他无法斩断那份柔情和亲情,却又没有勇气放弃现有的地位和身份,去大胆地接纳被他抛弃的孤儿寡母。因此,他只能忍受情感与利益所构成的冲突的挤压、折磨,内心无法获得片刻安宁。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严重的人格分裂症患者。在现实的日常生活、事务中,他必须扮演首领的角色,依仗自己的地位、权势来管理部落,并且不得不掩饰他与初恋情人之间的关系;在卸去首领的面具后,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往昔的甜蜜,从而陷入内心的不安与挣扎、自责与愧疚,不能自拔。他知道自己有“罪”, 因此,许多时候他愿意承受内心不安带来的痛苦折磨,自认为这是他应得的下场。他的这种不安与挣扎在他的昔日情人尼罗死后达到了顶点,使他几近疯狂。当得知尼罗的灵魂托生于他家的那只白耗牛后,他内心更是不安。他丝毫不怀疑那是尼罗的报复,她不散的阴魂投寄在耗牛身上,是对他始乱终弃这一不义行为的回击。同时,他还认定,家中发生的一些不吉祥的祸端也是这只牛带来的。为了得到尼罗的原谅,救赎自己的罪恶,他格外地关照那只白耗牛,给它最好的草料吃,给它最干净的水喝,不允许仆人挤它的奶,不允许人们打它。这还不够,他认为只有自己才能照看好这只牛,甚至搬到牛棚里与白耗牛为伴,在它身边不断地自言自语,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安与愧疚。小说正是通过这一系列充满奇异色彩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人物腾跃翻滚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艺术处理,在表现手法和审美效果上已经与现代主义小说相当一致了,它使我们通过隐秘的心理活动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
三
对于一个创作者,尤其是小说创作者来说,艺术想象或艺术虚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手段,即使是那些忠实地信奉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作家,也不可能完全按照客观现实的本真面目进行写作,对现实做机械的模仿,而不展开任何想象。《月亮营地》尽管不像浪漫主义小说那样,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想象作为延展故事情节、构建文本世界的核心手段,但其中的一些片段或章节却充溢着超现实的奇异瑰丽的想象。这些片段或章节尽管不是文本的主要部分,所涉及的人物也不是小说重点刻画的形象,却发挥了重要的艺术表现作用。它不但对于塑造人物形象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对于揭示人物精神世界的细微幽秘也有着其他艺术方式无法比拟的独到之处。如果不算苛责的话,我们认为,《月亮营地》这部小说整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假如说局部地方还有令我们感到眼前一亮的审美聚光,那就是那些充满了神奇色彩的想象片段。正是那些具有梦幻色彩的想象,使得这部小说在审美这一层面具有了足以激活读者艺术欲望的力量。
在小说中,围绕一个并不起眼的人物一一尼罗,作者放开手脚,大胆地开启了想象的发动机,让它释放出了超拔的能量。原本已经去世的尼罗多次“起死回生”,与活着的人进行对话。小说就此打破了生与死的界限,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塑造开辟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这个艺术场景也可以在藏族文化的视域之中加以认识、理解,并能得到恰当的解释,比如它反映了藏族文化中生死轮回的宗教观念,是对藏族传统文化理念的艺术展现——去世的人把灵魂暂时寄托在其他物体上不愿离去,不断地来到曾经驻留过的人间。我们相信,这一思路对揭示文本的文化内涵,开掘作者的文化心理必定大有帮助。但我们更愿意尝试着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对此做一些分析、阐释。在此思路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浸染着超现实色彩的艺术想象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带给了我们超乎寻常的艺术享受和美学启迪。
第一,它通过奇幻怪异的方式展现了人的精神/心灵世界的丰富与广博,使我们看到了在无限阔大纷繁的现实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为阔大纷繁且隐秘深邃的精神世界。 由于此,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说,它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了人的存在一一精神世界的真实境况。
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欣赏、研读与评判,习惯于从外围入手,看它是否很好地反映了客观现实,是否与人的现实经验相吻合。这种认识方式遵循的是现实法则和经验法则,它意味着我们希望艺术作品能够以现实存在的景象作为叙述的参照物,以实实在在的人生经验作为叙述的根本,认为依照这样的法则创造的作品才能真实地揭示人的存在境遇。这样的文学认识思路当然有其合理性,但就文学全面反映人的存在的真实境遇而言,这样的创作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心理学的发展已经不可辩驳地告诉我们,与现实存在相比,人的精神存在要复杂得多,也阔大、丰富得多,这就意味着人的精神世界其实比人所经历的客观现实更为丰富,更为复杂。我们如果打破以客观现实为唯一真实的认识逻辑的话,就会惊奇地发现,人的精神/心灵的真实的确要比客观真实更为丰富,而许多时候,我们的精神/心灵真实可能比所谓的客观真实更具有可靠性。何以如此呢?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受各种外力的制约,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本来意愿,戴上 “面具”;同时,我们有限的经验也会限制我们的生活体验。但在精神世界里,我们的心灵感受不会欺骗自己,它会毫无遮掩地将真实面目展露出来;同时,我们还可以借助想象,突破、穿越现实的层层幕障,在精神世界里营造一个更为辽远的天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某种程度上,通过表现人的精神/心灵世界来揭示人的存在状况,似乎显得更为真实。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作家指出:“真实并不存在于生活之中,更不在火热的现实之中。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强大的、现实主义的。哪怕从内心生出的一棵人世本不存在的小草,也是真实的灵芝。这就是写作中的现实,是超越主义的现实。”①说“真实并不存在于生活之中”似乎 些偏颇,但说“来自于内心的、灵魂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强大的、现实主义的”,却是在理之言。这些真实不是我们的肉眼所能看到的客观物象,而是我们的情感能够感受的经验。它虽是无形的,却也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它存在形态的独特,在艺术世界里,为了形象地表现它,往往需要借助一些奇异超常的手法。
在《月光营地》中,为了表达尼罗情感上的细微涟漪和内心的真实需求,作者设置了富有宗教文化色彩的转世情节。尼罗的死而复生尽管在现实逻辑上显得奇异荒诞,却能够让读者感觉、体味到尼罗的内心世界以及她对自己现实遭遇的态度。尼罗是一个被生活和爱情抛弃的弱者。年轻时,她与阿•格旺相互爱慕,并为阿•格旺生育了两个儿子,最终却被阿•格旺抛弃了。对于这种不幸的命运,尼罗虽然没有做出正面的反抗,内心却怀有怨恨与不满。她在无望的等待中走向了死亡,却死不瞑目。死不瞑目,或者说死不甘心,是尼罗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基本态度。生前她虽积怨在心,但因顾虑重重而把所有的不满与怨恨深藏心底。为了表现她对现实遭遇的不满和对苦难命运的愤恨,小说设置了其死后阴魂不散的情节,让她多次出没在活着的人们中间,带给他们不安与恐慌。这样的艺术构思显然已经超出了客观现实的范畴,无法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既定标 准去衡量它的真实性。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以“人死不能复生”的认识逻辑去判定这一 情节的真实性,而只能遵循艺术想象的逻辑去感受它所传达的真实体验。事实上,通过 这种虚构的、夸张的、想象化的奇幻情节,我们能够更为强烈地感觉到,尼罗内心深处 挤压的长达一生的不满与怨恨是多么强烈。毫无疑问,作品通过想象完成了对人物内心 世界的真实表现,这种真实也映照着现实的真实。
第二,艺术想象是对艺术自由品质的最有力的体现,也是对艺术自由的强有力的维护,同时还是对人的自由梦想的艺术化实现。《月亮营地》中有关尼罗超越生死界限的 情节就充分体现了艺术的这种品质。
首先,尽管文学创作离不开现实依据,但文学从根本上说还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运动,可以说,自由是文学艺术的一种内在品质。因此,真正的文学作品在把根系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的同时,总是要竭力地超越现实,从而尽可能地去追求自由的风采。如何有效地达到这一艺术目的呢?毫无疑问,充分运用合理而高妙的艺术想象,是一条很好的途径。真正自由的文学作品绝对不可能是对现实存在亦步亦趋的描摹,也不是对过往历史的逼真再现,它是精神展翅飞翔的姿态,是想象火焰发出的热量。优秀作品无不拥有这种高贵的品质。《月亮营地》中,作者依托民族文化的有力支撑,通过大胆想象,为读者展示了艺术的自由品质,使我们感受到了艺术突破客观现实的羁绊而努力飞翔的强烈冲动。虽然能够体现创作主体强劲想象力的艺术片段在《月亮营地》中并不多见,但已经出现的那些片段,还是让这部作品拥有了令人思绪飞动的艺术感染力和冲击力。
其次,尽管艺术作品具有多种功能,但作为一种虚构的产物,它最终所体现出来的其实是人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人们常说,艺术是作家的白日梦,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艺术的此种特殊功能的形象概括。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各种局限的大量存在,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不得不面对被制约、压抑的生存境遇,但人的天性之中有一种追求自由的强烈冲动,当这种冲动在现实中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人就会想方设法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得满足,而文学艺术就是一种非常巧妙且有效的方式。人就是在一个接一个的艺术梦想中,不断地满足着自己的自由冲动。在这一个过程中,艺术想象就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人正是借助它来实现对自由的绝对追求的,而人也正是在自由想象中体验到了绝对的自由。“绝对自由只有在想象中才能达成,它不必求助于经验,它纯粹是内心 生活,纯粹是反经验的反现实的形式冲动。”②在《月亮营地》中,我们也正是通过尼罗这一人物的奇异经历感受到了人的精神世界的自由无碍,从而也感受到艺术带给我们的奇妙无比的审美享受。
就艺术特色而言,《月亮营地》呈现给我们的当然不仅仅是奇异怪诞的想象。但相 比之下,其他方面的艺术特色所具有的审美冲击力要弱得多,还无法成为撑起这部小说 艺术穹顶的支柱。坦率地说,如果不是那几个充满奇异怪诞色彩的想象片段,这部小说 的艺术特色将不会给我们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在笔者看来,正是那些突破现实存在逻辑的奇妙绚丽的艺术想象,赋予了作品一种难得的诗性,把我们带入一种奇妙但无比真 实的存在境遇。
注释:
①阎连科:《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受活》,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70页。
②吴亮:《缺乏想象力的时代》,林建法、傅任选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117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5辑

胡沛萍,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藏族文学。在各类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先后出版《多元文化视野中的当代藏族汉语文学》《边地歌吟—阿来与扎西达娃的文学世界》《“狂欢化”写作:莫言小说的艺术特征与叛逆精神》等学术著作七部。

于宏,女,汉族,吉林辽源人。现为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教授。在《民族文学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西藏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合著)。先后主持、参与校级、省部级、国家课题五项。

梅卓,女,藏族。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青海湖》文学月刊主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青海省优秀专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太阳部落》《月亮营地》,诗集《梅卓散文诗选》,小说集《人在高处》《麝香之爱》,散文集《藏地芬芳》《吉祥玉树》《走马安多》《乘愿而来》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奖、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拔尖人才、全国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第四、五、六届省政府文学作品优秀奖、青海省四个一批拔尖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