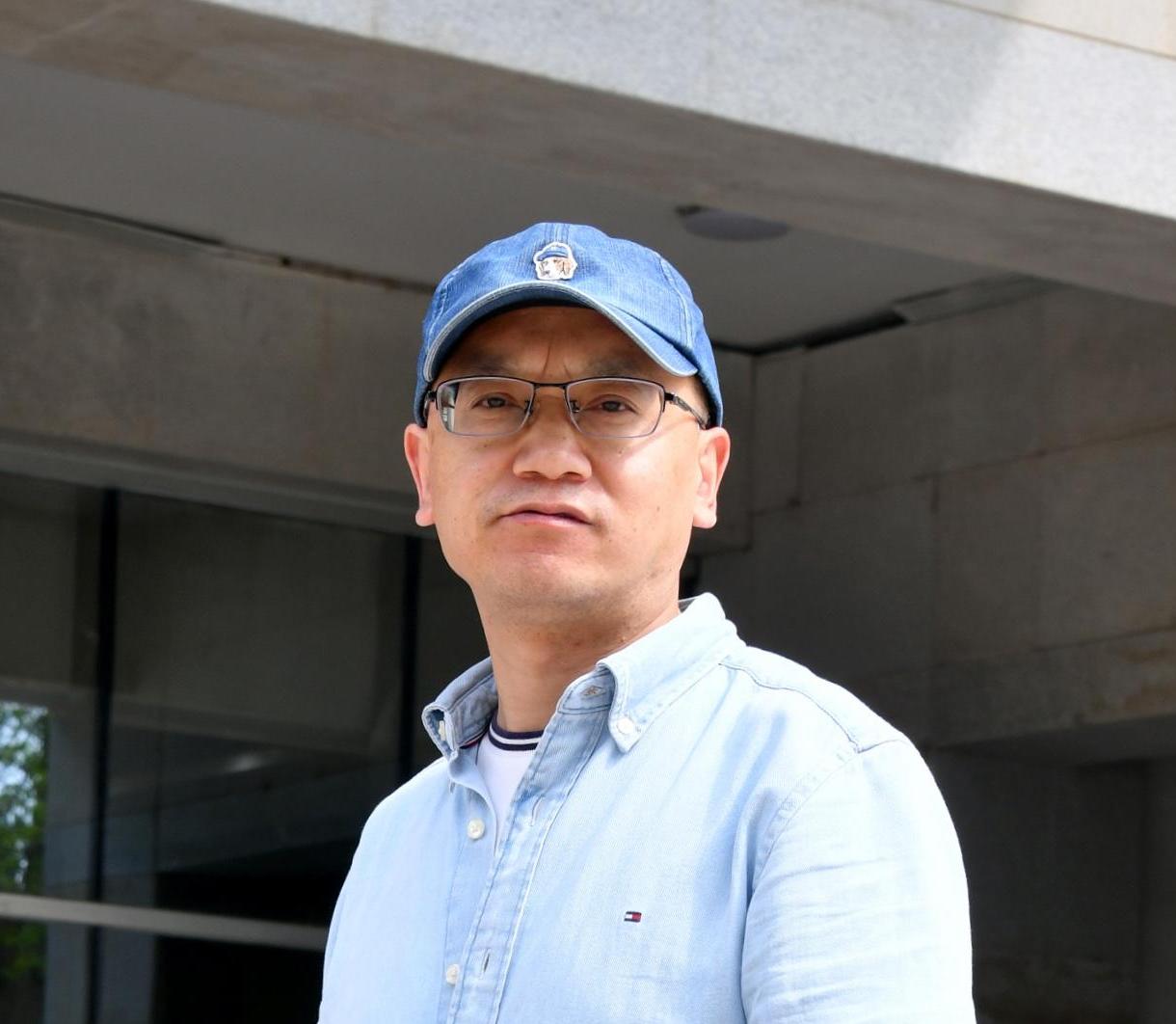你们都是花
在格尔木到都兰的路上,偶尔发现一个地方名叫大格勒。进去看看吧,叫这样的名字,一定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漫长的进村道路,两边高大行树,行树外是汹涌水渠,水渠外边,都是一派浩瀚的沙漠戈壁。这些风物几乎是沙漠戈壁地带村庄的标配,常年在大西北四处行走,早已不把这类风物当风景了。
接近村口时,正午阳光当头猛照,决定在水渠边的大树下休整一下。说是休整,也就是到附近转转看看呗,这是多日浪游形成的基本模式。转转,看看,无预定目标,心中没有预期,只是转转看看,每次总会有新发现,这也是常年浪游所得的经验。
道路右边的水渠里,水流若游丝,呜呜咽咽,但大树成荫。左边水渠的渠水,浩浩荡荡,周边却以沙生植物为主,树荫不足以遮挡高悬的太阳。
在缺水地带,我向来把流水喧哗当成铁板铜琶的天地大音去听。那是生命的歌唱,那是摊开在大地上的,供所有生命激情诵读的宣言书。
两米宽阔的水渠,一米左右的水深,大约是地势的自然坡度使然,一条渠水可以酿造出一条大河的气概,澎湃激越,一往无前。忽然,水渠边一片杂草杂花吸引了我。
有一种花,扯着几米长的藤蔓,从根儿到梢儿都开满了花朵,而花朵从盛开到凋谢集于一身。有的部位正在盛开着那种黄澄澄的花朵,阳光下,花朵艳丽鲜活。有的部位花朵正在凋谢,花心已经吐出丝线,而花朵还不肯就此落幕。有的部位呢,花朵完全陨落,代之以一团团绒球。有的绒球,如一位耄耋老者的头颅,稀薄的白发耷拉在头顶,无风静伏,有风微微波动。有的绒球花丝呈金黄色,如瀑布般披散下来,阳光下,金光莹莹,微风中,像金发女郎的那种大波浪,令一方天地为之眩晕。
细看,在当大波浪随风飘荡时,浪涛下有那么一撮撮细细的绒毛,时刻准备着随风飘荡。
我知道,这就是这种花的种子,它扎根于大地,种子随风播撒于大地。而在同一株花上,犹如一张四世同堂的全家福,可以同时呈现同一朵花,从孕育、繁衍、盛年和衰年的全过程,实在令人心生感慨。
小时候,在家乡河边的沙地里,见过这种植物,想不起它有什么具体的功用,我们把它叫作铁线莲。到底该叫什么名字,我将图片发布在微信圈,很快就有了很多读者反馈。有的说这是卷毛狗娃子,有的说是毛毛头,等等。
我知道,每一种植物都有拉丁文的学名,有习惯性称呼,更多的是所在地的乡土名字。这些乡土名字,有的从植物的外形而来,有的从其功用而来,有的呢,仅仅是一个称呼。正如有些人名指涉着具体的含义,而有的人名,只是人人都需要一个名字罢了。我的好友,一位植物学博士留言说,这是甘青铁线莲。
要进村去了,我指着那一片在干旱的沙地里,奋勇生长着的甘青铁线莲说,你们都是花。
阿柔,阿柔
一个姑娘的名字如果叫阿柔,我们不由得会想象这一定是一位美丽的姑娘,即便与这位有着美丽名字的姑娘缘悭一面,那也不必过分沮丧,一遍遍叫着这样的名字,整个世界都是美丽的。
可惜了,阿柔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它是一个地名。从祁连县的俄堡去往祁连县城的路上,要经过阿柔。路过时,记住了这个让人怦然心动的名字。过了几天,专程来到阿柔,要把美丽的名字落到实处。前几天路过时,阿柔下着小雨,几天后专程去膜拜时,阿柔下着大雨。
阿柔是旧时代一个藏族部落的名字,时代变了,名字留了下来。阿柔部落所在的地域,正是祁连山的山脊朝南铺开的部分,由高山草场一路垂挂下来,到了阿柔腹地,已经是缓坡草场了。这类山地草场正是行风兴雨的地方,青海湖的湿润一路攀爬到这样的海拔高度,很容易幻变为降雨。雨水落在山顶上是雪,落在缓坡上是雨,无论在山顶还是缓坡,这些来自青海湖的湿润,最终都会以河流的形式回馈青海湖,如此周而复始,营造出了一片美丽天地。
下雨天的阿柔,远远看去美丽非常,要是身临其境,即便是大暑天,也要做好抗寒准备。在三十年时光里,我曾经四次经过阿柔地界,都是大暑天,无一例外,都遇到了大雪,也无一例外,我都没有提前做任何抗寒准备。四次经过这里,都是临时动议,而老天爷却在时刻准备着为大地生灵恩赐风雪。
这次虽是专程来阿柔,而且真正来到了那个名叫阿柔的地方,同样也没有做什么抗寒准备,而老天爷却已经在天空蓄满了雨水。在祁连县城的几天,每个夜晚都是整夜的雨,好在每个白天都是晴天。从祁连县城出发时是大清早,昨夜的雨却没有停下来,漫天漫地都是雨水淋漓。看见阿柔的路牌时,雨水澎湃起来,雨滴砸在路面上,一滴雨水绽放一朵很大的水花,整个路面像是一条浪涛汹涌的河流。公路左边是高山草地,大雨并没有影响它们吃草,庞大的牦牛在低头吃草,娇小的羊儿在低头吃草。公路右边是平缓草坡,牧群稀少,那是留给它们冬天的草场,在雨雾中,几棵可以看见的青草趁着这短暂的生长季在迅猛生长。
一片房屋排列在公路两边,而此时,大雨像是被谁按下了暂停键,变成零星小雨。一些人佝偻着身子,从低矮的房屋里蹀躞而出,抬头看看天,向远方瞭望一眼,然后不紧不慢整理铺面。一些人佝偻着身子,去这家店铺提拎几样蔬菜,在那家店铺带几只馒头,或一把生面条,不知是要准备午餐还是早餐,因为这是上午十时许,早餐迟了一些,午餐又早了一些。一片看似要废弃另迁的院落里,野草疯长,野花盛开。正在街上溜达,雨势又大了,暂停了一会儿的天空大地,白雾茫茫,草色新雨中,雾气如潮水,一波一波荡漾开来。
在尕牧农脑儿
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尕牧农。事先完全不知道这条山谷里还藏着这么一个村庄,迎面相遇,一眼望出,竟然觉得有些气虚。
这是门源县境到处都可看见的小村庄,区别只在于,尕牧农的美,有点过分了,那种让人止不住心颤的美。
尕牧农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尕牧农和下尕牧农,我们就统一叫作尕牧农吧。我是先到下尕牧农,再到上尕牧农的。本来就是一趟走哪算哪的浪游,遇到好地方,那是幸运,遇不到什么好地方,也是另一种见识:这里没有什么好地方。
门源的村庄都是很美的,在县境浪游几天了,真的还没有发现不美的地方,而当进入尕牧农时,我的心里还是吃了一惊,以至于,有那么不短的一会儿,思绪发生了错乱:我究竟来到了一个什么地方?
不是世外桃源,不是身负千年盛名的膏腴之地。这里是门源,一个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的荒寒山区。世界有时候真的像一枚陀螺,当现代之光让人们目迷五色无所适从之时,那些在高歌猛进的现代化浪潮中的后进者,恰好因为传统元素保存较多,反而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引领者。尕牧农就是这样一个所在,当人们从楼宇的森林里突围出来后,这里正是一个适合大口喘气的地方。
徜徉其中,何如抽身其外。尕牧农的制高点是一座名叫尕牧农脑儿的独立山头,山头上悬着一座白色佛塔,在灿白的阳光下,白光连通天地,而佛塔前面的大片空地上,清一色的银露梅花开正盛。灿白的阳光,灿白的佛塔,灿白的银露梅,底色却都是青草地。青草尖上漂浮着的一层白光,好似阳光飘洒在浮云之上,天迷离,地迷离,好一派迷离天地。脑儿,故乡黄土高原一个普通的常见的地名后缀,张家脑儿,李家脑儿,前沟脑儿,后沟脑儿,无数的脑儿。
脑儿,就是一片高地凸出来的部分,或凹进去的部分,像人的脑袋,有凸有凹。尕牧农脑儿就是整个尕牧农这一块地方伸出来的一颗硕大的头颅。在广场看杂耍热闹,小孩最喜欢骑在爸爸的脖子上看,不在于看见了什么,而在于那种骑在爸爸脖子上的自豪和傲娇。站在尕牧农脑儿上看尕牧农,就是小孩子骑在爸爸脖子上睥睨四方的那种感觉。
两条小溪流各自从雪山上下来,在一片开阔地见面后,合成一条较大的溪流。小溪流旁边,大树下,掩藏着三五个院落,或红顶白墙,或红墙蓝顶。大溪流两边,大树下,错落着三五十户人家,或红瓦白墙,或红墙蓝顶。河滩里,密布着闲花野草,偶尔有老鹰在空中盘旋。看不出来老鹰有什么打算,也许仅仅是待在窝里没事儿,出来看看天空,看看大地。老鹰好像在专门向人间展示自己的滞空飞翔能力,好大工夫翅膀都不用波动一次,让人怀疑,这只老鹰也学会了使用威亚。
村庄的两边都是缓坡庄稼地,不是那种被整修成梯田式的庄稼地,而是保留了地形的原始坡度。青稞,洋芋,油菜,间杂镶嵌在缓坡上。给人感觉,不是因为气候或休耕轮种等耕作技术的需要,而是出自审美的考量。一片黄色,金黄灿烂,一片绿色,碧绿莹莹,一片紫色,紫气冉冉。
门源的色彩都是那种大色彩,色度最高的那种,门源的色块也都是大色块,色泽最铺张的那种。而各色块之间又是互嵌互衬的,黄更黄,绿更绿,紫更紫。而天上的白云,远处的雪山,山脑儿上的白塔,还有白塔下的银露梅,在各种色彩的晕染之下,置身尕牧农,让人恍兮惚兮依稀仿佛,不觉时间在流逝。
香日德点滴
香日德我去过四次,前两次都是路过,后两次是专程去的。专程去的这两次,去年一次,今年一次。去年是疫情结束后,全家出来散心,今年这次,是兰州疫情正烈,回不了家。
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去香日德,当然不愿意以任何灾难为背景,“浪游湖海一身轻”的那种。
在藏语中,香日德的意思是大树众多的地方,有人估计,如果以一米株距列队,这里的大树可以从香日德出发,走青海湖一路,过西宁到兰州。到底怎样,不必去为一棵树一棵树做排队练习,肯定含有形容的意思,是为了形象地说明这里的大树确实多。
香日德地处昆仑山浅山地带,按说已经属于高寒地区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树呢。理论是灰色的,你去转一圈就明白了。周围都是大山,中间一个盆地,很大很大的盆地,很平坦很开阔的那种盆地,在视觉上真是一只全封闭的大盆。虽是很大的一块地方,在地理学上仍然属于那种小地形。小地形有小气候,几条河流在这里汇聚,周围高山消解着高寒,灌溉渠蛛网般纵横,田园焉能不富饶,草木何愁不茂盛。
其实,我反复来这里,是要看吐谷浑大墓的,最著名的当然要算“血渭一号”大墓了,网络小说中说是“九层妖塔”所在的地方。实际上,这里是一个庞大的墓葬区,成千上万座吐谷浑和吐蕃时代的墓葬汇聚在这里,迤逦在察汗乌苏河两岸的旷野里。
在墓葬区官方出具的说明书中,也毫不讳言这里风水的卓越,吐谷浑和吐蕃人虽是少数民族,但对中原地区的风水观念,可谓是全盘接受了的,他们正是看上了此地的风水。所以,“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你是唯一的一块埋人的地方”。时代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安妥灵魂的意愿是相通的。
我研究过风水,但咱不说这个,仅从对山水的普遍认知出发,这里也算得上好山好水好风光。去年是初秋季节来的,周围的山头都是那种浅灰色的,因为那几天这里没有下雨。今年是大暑天来的,周围的山头却是白茫茫一片,因为昨夜这里下了一场大雨。一位浙江人带着全家在这里旅游,指着周围群山兴奋地说,我们来到雪山了。我笑说,这是有雪的山,不是雪山。雪山终年积雪不化,周围这些山头上的雪,只要太阳出来,半天就没有了。
我想顺着一条小河,看看到底能不能走到有雪的地方。高山草地野路,砂石路面,一车宽窄,两边都是坚实沙地,一般不会出什么危险。山谷越来越窄,道路越来越陡,雪地近在眼前了。停下车,昨夜大雨的痕迹遍地都是,一条沙河纵贯沟谷中间,那边的山根下,有一户人家,远远看去,彩幡猎猎,炊烟袅袅,白云在上,孤零零的一屋桀骜。心里正在怅然,脚下一滑,右脚踏入泥坑中,膝盖以下半腿黄泥。
从这条荒沟退出,拐进另一条有硬化路面的山谷。那是通向一个建制乡的公路。走出几十公里,不能再走了,昨夜大雨冲毁路面,施工队正在紧张作业,去高山牧场看看的行动就此落幕,而察汗乌苏河因为有了众多小河的支持,正在一路高歌奔向香日德。
从察汗乌苏河谷进来,又从察汗乌苏出去,接上香日德盆地。在旧时代,也包括新时代,香日德都是一个四方冲要之地,成为广阔内地与广阔高原的一个衔接点。在整个柴达木盆地,香日德盆地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宜农宜牧,可居可进,居则自给自足,进则四通八达,安居乐业之地,其实就是所有风水宝地的精髓。
两条大河见面的样子
黑河是河西走廊最大的河流,从祁连雪山发源后,一路向南,到祁连县城与八宝河汇合后,转个圈儿,又转头向北。这一下,一北不再南,一举洞穿祁连山,让河西走廊中部的沙漠戈壁变成绿洲后,索性再穿过北山,在阿拉善的居延海,才停下脚步。八宝河呢,发源于祁连山的另一座雪山,由南向北,沿途接纳了同样发源于雪山的众多河流,当水势已具有大河气象时,在祁连县城与黑河相遇,随后,作为一条河流的名字,却从此泯然于黑河之中。
按说,无论从长度和水量,八宝河非但丝毫不逊于黑河,可能还要胜过一些,可是,两条河自从在祁连县城见面后,八宝河却隐姓埋名,甘愿成为黑河的一部分,这真是让人到哪说理去。
黑河和八宝河不需要说理,叫什么名字都得像一条重要河流的样子,担起哺育沿途万物万灵的责任。黑河虽不能冲破陆地的重重关隘,直奔大海,但自己却可以独立成海——居延海不是海吗?
去看看两河见面的样子吧。我困居祁连县城那几天,内心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亲眼看看这两条实力在伯仲之间的河流见面的样子,那一定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次去寻找两河见面之地是在一个早上,从昨天黄昏到朝阳升起时分,一直在下雨,淅淅沥沥一个晚上。大雨在朝阳升起之前戛然而止,雨后天晴,漂浮在天地间的色彩就是一幅油画,流荡于天地间的空气,要是能有办法聚拢起来,尽可放心饕餮一顿。当我找到了地图标识的地方后,却没有看到两河见面的盛大场景。
第二次去寻找还是一个早上,天阴,但无雨,凉风吹拂,衣衫飘飘,在这大暑季节里,为了自己这么一个奢侈的理由,而尽享天地奢侈之赐予,流落异乡的某种沮丧,霎时涓滴皆无。遗憾的是,还是没有找到两河见面后的恢宏现场。
马上要离开祁连县城了,这个小小的愿望如果不能实现,绝对会是此行的一个遗憾。这天一大早,冒雨远行数百里,在深山峡谷中找到了黑河源头。黄昏时分返回县城后,大风携大雨,大雨助大风,一遍遍扫荡着目力能及的所有天地山川。还是前两次走过的路线,出县城不远就找到了目标,这不就是前两次来的地方嘛!
问题出在哪里呢,前两次不是找错了地方,而是我心中为两河见面预先描画了一个愿景。在我的设想中,两条大河见面,未必有两列火车相撞那么惊天地泣鬼神,但一定是两排浪头,像一群公羊或公牛打群架那样,浪浪相撞,浪花如火花般让人目炫。那一定是,也必须是一场盛况空前的双雄会。想想啊,在蓝天白云之下,在群山耸峙之中,两条从不同方向,一路开山裂石,摧枯拉朽而来的河流,在这样一个造物主预设的战场里激情相逢,如果不够惊心动魄,又如何展现冥冥造化之天地神功呢。
顺八宝河逆行,河水在地上平躺着前行,大雨从空中倒灌,天地一色,一色都是漠漠一白的水。来到前两次到过的一个叫油葫芦的平阔处,只见两片水色略有不同的水流,在这里混合,很快地,化为一色的水。一块巨大的河心洲,看得出是两水共同塑造而出的,大雨中,河心洲里,杂树哗哗,杂草瑟瑟,杂花默默,一起深锁在弥漫天地的雨雾里。两水同时得到缓冲,就像两个一口气奔跑数百里的人,在见面前,坐下来,缓一缓,喝杯茶,待心情平复后,互道契阔,再相拥并行。
两条河的源头都在雪山上,都是一路冲破千山阻隔来到祁连县城的,彼此鞍马劳顿,风尘仆仆,而见面之处正好是一片开阔地。四面高山都在远处,开阔地上,万树招摇,千草迷离,百花次第绽放,两河见面后,徜徉于无边美景之中。却原来,这并非天地为两河预设的战场,而是一块歇脚地,待力量积蓄足够以后,还有更漫长艰险的路程,需要那条名叫黑河的大河,一路突破大山重围,去创造作为一条大河应有的辉煌。
原刊于《青海湖》2023年第2期(责任编辑:宗哲)

马步升 甘肃合水人。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主席。现任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有小说、散文和学术论著约800万字。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陇东三部曲》《江湖三部曲》等8部,中短篇小说集2部,有散文集《纸上苍生》等10部,有学术论著十多种。曾获中华人口文化奖、老舍文学奖等二十多项。多次担任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骏马奖等国内重要文学奖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