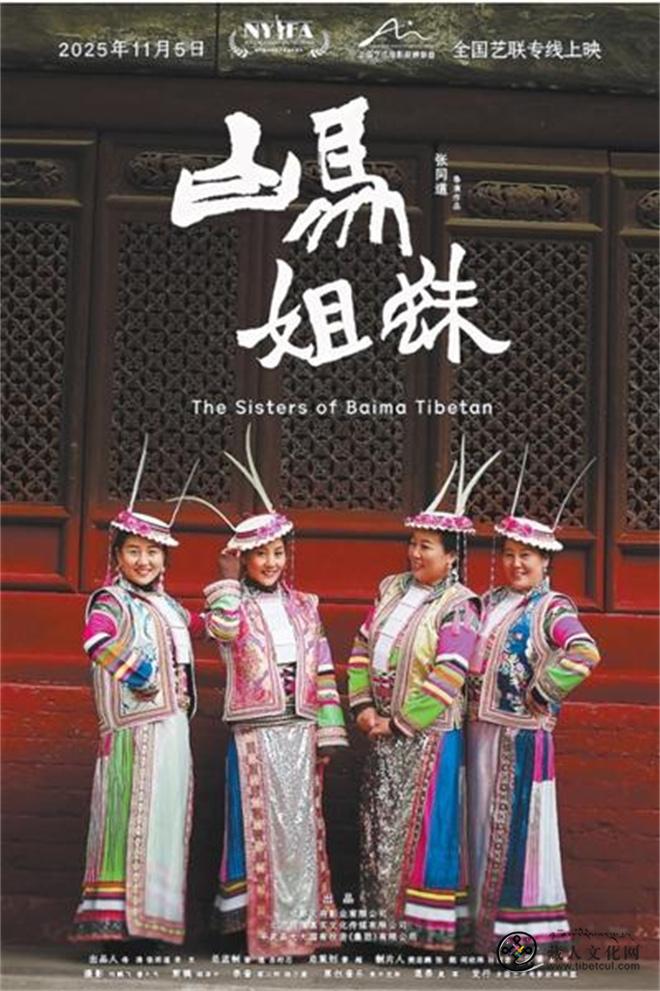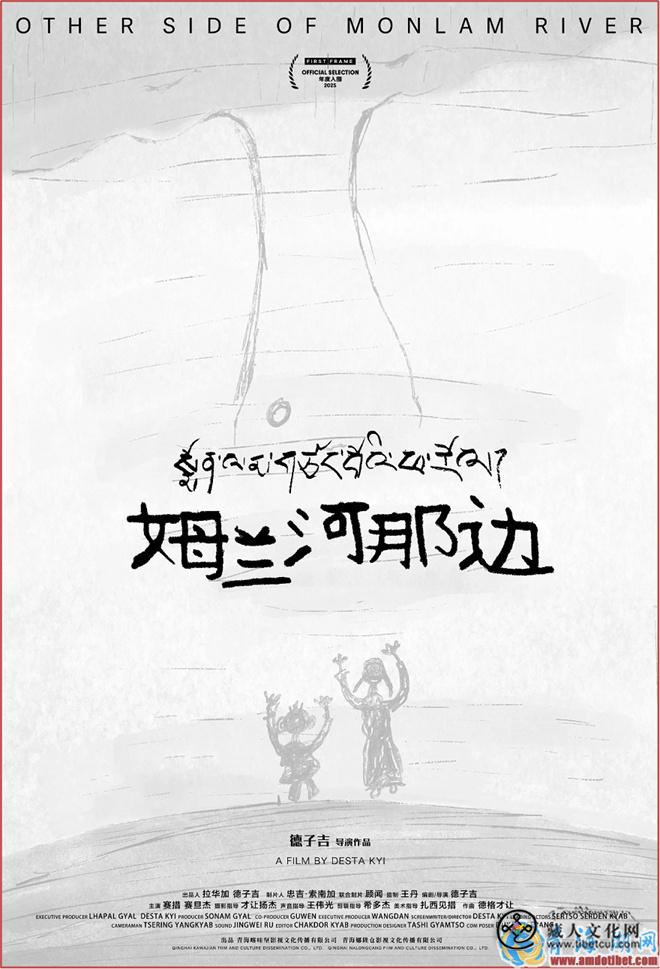中国藏人藏语电影作品在21世纪初才方兴未艾。然而,这些电影作品已经在国际电影节中屡次公映并频频获奖。并且,这些作品展现的藏族文化景观与国内及欧美既有的涉藏电影中的景观存在显著差异。当代中国藏人电影景观和人物刻画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体现出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本文以著名藏族电影人万玛才旦的电影为案例,对其电影的国际化创作过程进行阐释。同时,还将论述万玛才旦如何运用电影语言来描述当代中国语境之下全球化与现代化对藏族佛教价值观的冲击。钦则诺布仁波切的《高山上的世界杯》(1999)和艾里克∙瓦利的《喜马拉雅》(1999) 在20世纪末推动了藏语电影在全球范围的普及。21世纪的今天,越来越多的藏人自创电影人及其优秀作品的出现反映出这两部藏语影片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国际电影数据库(Internet Movie Database,简称IMD)目录中列出的15部最著名的藏语电影中,万玛才旦的《寻找智美更登》(2009) 、《老狗》(2011)、《静静的玛尼石》(2005) 被列为世界藏语电影发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曾在东京银座影展 (Tokyo Filme 最佳作品奖)、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 (The Locarno Film Festival金豹奖)、曼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奖)上获奖(以上仅列出了小部分获奖名称)。
本文以笔者与万玛才旦在北京的教学合作和参与其部分影片摄制作过程之经历作为基础进行民族志叙述和影片阐释,以期能为当代藏人电影研究的多元化贡献一已之力。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将本文置于当代中国的语境中,并非是要将万玛才旦的电影生涯地方化,而是希望强调其电影创作的跨族、跨国属性。“跨族”和“跨国”这两个词是来源于英文的transnational, 这个词通常的中文翻译是“跨国”,但是从英文词根上看,还有“跨民族”的含义。因为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在本文中暂且翻译为“跨族”但包含跨国的意思。因而,在文中,跨族(transnational)意指地理方位、个人和专业流动性以及来自不同地区资源的同步链接。在此,为了更清晰地理解万玛才旦电影的跨族性,笔者罗列一下“跨族”在文中的几层意思。首先,跨族指的是万玛才旦工作和生活的双重焦点(bifocal) 或两地 (bi-local) 栖居模式。比如,北京通常是其影片前期资源筹备、后期制作和进入电影市场的地点,而青海(安多藏区)是其家乡和电影拍摄基地。在此情况下,跨族与全球链接性 (global connectivity) 是同义词。因而,跨族也就意味着万玛才旦的电影制作过程是一个跨族与跨国的多重性流动过程,诸如拍摄所需的物力和人力资源的集聚以及影片完成后的国际影展活动等。在这个意义上,跨族意味着一系列的大都市和网络链接点,作为赢得来自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电影制作资源的口岸。自从万玛才旦在亚洲、欧洲和北美逐渐赢得了观众后,跨族还意指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社会状态和政治环境中、在藏人和非藏人当中佛教是如何被解读为藏族文化传统的核心的。最后,从影评的角度看,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中,跨族还与导演本人如何通过电影语言来表述藏人文化能动性及其公共话语相关。
构建跨族藏人电影
2002年,万玛才旦来到北京追求他的藏语电影事业。他当时才三十出头,却早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作家了。在好友们的支持下,他开始在中国唯一的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影制作。北京电影学院是“中国好莱坞”的腹心地带,是培养和聚集众多知名电影导演、编剧、摄影师的圣殿,诸如张艺谋、田壮壮、谢飞、张献民、黄丹等。他们之中大部分都在圈内享有盛誉或身居要职。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上海被视为是“中国的好莱坞”,那么现在北京则是中国电影制作的中心。这座城市聚集了大量人才、资金以及国有的和私有的影视制作公司。中国电影工业20%的年增长率通常是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各种会议室、工作室、咖啡馆、私人会所里被营造出来。如果说孟买被称作是印度的宝莱坞,那么笔者当然也可以称北京为“北莱坞”(Beillywood)。通俗地讲,北京是一个强力磁场,吸引着年轻的男男女女,进入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电影工业。不过他们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实现自己的电影梦,更多人则在“北莱坞”的外围等候时机的到来,其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国家体制或大型电影企业之外制作他们影片。这种趋向日益被学者们记录和研讨,诸如裴开瑞、毕克伟和张英进。万玛才旦便是属于那些选择独创制作电影的群体中的一员。
目前,国际学界对中国电影的研究已有大量的文集和专著。裴开瑞的多卷本《中国电影》文集证明了中国电影日趋多元和扩展的规模对学者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然而,在这些数量不断增长的自创电影作品中,诸如万玛才旦那样的非汉族电影人的经历常常被笼统地概括为“少数民族经验”或是“少数民族电影”。相关的学术讨论仍然停留在中国的“族群”和“民族”等宏观政治学方面,从而忽视了非汉族电影人多样的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无庸置疑,“族群”政治在北京是至关紧要的,然而,把蒙古族、藏族或其他民族的电影人合并在一起,把他们统称为“少数民族”,却有意无意地就把多数民族以外的人群单一地族群化和种族化了。这种学术倾向事实上是一种以汉族为重心的科研视角,通常忽略了来自其他族群的电影人的多样性以及他们各自作品的复杂性。在此,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在任何国家里,“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都属于一类国家或政治建构概念,而不是个体内在的文化意识。但是,一旦此类概念体化为社会现实时,它有其社会生命,因而,如同其他多民族国家一样,“少数”和“多数”的社会构建被体化到个人意识里便不足为奇了。
万玛才旦常常谈及他电影制作的理想是要建立藏语电影——不是要在21世纪主张藏人的自我封闭,而是要叙述藏人在这个巨变的世界、在中国现代化、藏人文化国际化中的经历。在万玛才旦创作剧本、塑造人物、执导拍摄过程、用藏语将活力注入故事中的同时,他也鼓励自己的同辈和未来的藏族电影人这样做。他的电影导演方式已被身居中国城镇中同样全球化的藏族艺术家们广泛接受。在这个背景下,万玛才旦的电影创作既是藏族式但同时又处于中国电影发展的跨族、跨国扩展的趋势里。在当代中国电影研究里,“跨族电影”或“国际化电影”(transnationalcinema)涵指日益增长的地方多元性和全球连通性。
在田野民族志工作中,笔者发现藏族学生与艺术家常常将万玛才旦尊敬地称为“新藏人电影”的奠基人,意指此类藏语电影由藏人来编剧和导演,而不是由国家或非藏人电影人来制作。对藏族观众来说,新藏人电影与他们常常提及的“本土藏人电影”是同义词。在其中,藏人期望建立对自己文化传统、习俗和社会问题的公共表征,原因是在过去还没有过藏人自创电影。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藏族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家注意到重构藏文化传统的正面形象成为了一个“藏族化”的过程。其中万玛才旦的电影制作是当代藏族艺术家集体努力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汉族电影人和影评人都对万玛才旦在“中国电影新势力”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无可否认的是,万玛才旦的电影魅力,特别是其早期作品,是建立在他对藏人世界以佛教为主的正面描述上的。对于境外的藏族电影人来说,这已不是新手法,而是一种被批评为用佛教语汇来刻版化藏族文化的形式。但是对于国内缺乏对藏族文化史了解的观众而言,万玛才旦的电影为之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因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内的主流人群已经习惯性地将藏文化与“落后”等社会发展概念等同起来。相比之下,万玛才旦的影片给观众们带来对藏文化新的描绘与理解。
新藏人电影中佛教的再生
万玛才旦电影制作的开创时期是藏人文化认同再生过程的一部分,其中佛教呈现为藏族文化历史的核心。当笔者在北京教授视觉人类学课程中有关影像与文化认同专题时,万玛才旦和笔者定期合作讲座,主持有关藏族电影制作和藏族传统文化恢复的讨论。他常常将其核心队员带来,与学生们交流。谈话中提及当藏语电影制作作为藏族文化恢复的一部分时,藏传佛教是一个重复出现的话题。万玛才旦经常提到自己在创作中如何捕捉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对他而言,传统在其电影中是藏传佛教的同义词。正如他所指出的:“离开了佛教,藏族文化便不存在”。
佛教的正面审美在万玛才旦早期的作品《草原》中充分地表达出来。这部20分钟的短片是他在北京电影学院的毕业作品。在剧本进入拍摄阶段之前,电影学院导演系前系主任谢飞力荐其获得学院的拍摄资金支持。出品后该片获得了第三届北京电影学院国际学生影视作品展中国学生最佳短片奖。谢飞回忆到:“万玛才旦的剧本,非常小的事,但是非常有意思,而且,不是藏族人是写不出这么个剧本的。”
谈及他的画面选择时,万玛才旦常常说自己偏好用16毫米、18毫米和21毫米的广角镜头。对他来说,电影的本质是在银幕上还原现实,观众由此可以移情地体验藏人的生活。通过导演的视线,笔者看到《草原》中的藏地景观是作为“主动背景” 来体现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他的电影画面的前景而不是背景。它支撑并饱含着人物的心灵景观及其社会行为。万玛才旦电影中的西藏景观其实是个转喻,它们“并不提示完整性,而是表示出更深远、更宏大的概念和关联性,因而,它们具有提炼性而不是全融性”。一个转喻式地境的功能是拓展观众的视野及其银幕之外影像联想。换言之,它直接赋予了直觉中的物理地境以生命,同时,通过拟人化手法,它凸显出地境的灵力或灵魂。
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佛教意味着藏族地境的灵魂。《草原》中,在村长才周和阿妈措姆抵达其目的地之前,阿妈措姆手中的经筒伴随着天空翱翔的秃鹫、在冬天干黄草地上移动的脚步、风中飘动的经幡在转动。在中途,一位玛尼石匠向他们问候致意。这位石匠端坐在一块羊皮上,錾刻着一块石头,不远处有一堵玛尼石堆起来的墙,每块石板上全都刻着佛教咒语和经文。摄像机随之特写到石匠饱经沧桑的双手。这一特写不是一种从上而下的角度,而是与双手水平。观众的眼睛情不自禁地移向这双正在石板上錾刻着经文的手。以此,凝视成为一种以视觉而引发的触摸。《草原》中这些微妙而精炼的全景扫摄和特写画面呈现出佛教的中心位置。无论触及到谁,都会被其中的佛教情感所触动。电影艺术中的“触动”或“被感动”与电影(cinema)的希腊词根kinema暗含的动态和情感意思有天然的联系。在这一意义上,电影是一个接触面、一处交织带、一条动态与情感的纽带,是一个处于某个地境中的、体化为人文原生要素的媒介。
因而,万玛才旦影片中的地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因素。地境中包含了人物身体的举止,体化在玛尼石上、风中的煨桑里、与空气共鸣的祈祷声,以及内心中因佛教引发的道德情感波澜。佛教在影片中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被限定在寺院环境中的教义教规,而是深深地融入在人物的“精神领域”中。从电影学的视角来看,这个“精神领域”是“一个触觉的眼睛和视觉的感触延伸的地方”。
感触藏地景观的肌肤
在万玛才旦过去几年的作品当中,以佛教的正面审美观和气候现象来反映家乡的自然地境的作品越来越少。在其观众以及评论家看来,以僧侣、寺院、经幡、草原、冰雪覆盖的群山、赞颂性的民歌等为标志的藏区地境的影像描述已发生了突变。在其近期的影片中,佛教画面似乎从以寺院建筑和带佛教标记的人文化地境为主的前景退居社会和个人空间的边缘,甚至隐入记忆的空间。
《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这两部他最近的获奖作品标志着这种从对藏区地境的正面审美画面转向了对家乡社会现实的揭示。这两部影片的故事情节虽然不同,然而,它们所反映的社会氛围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即:小镇和村落迅速变迁的物理空间,以及变化中的传统价值、公共道德、人际关系。万玛才旦的电影景观已不再传达“可爱家乡”的影像信息。相反,他起初以纯厚的佛教灵性来描绘祖辈土地的画面被迷失、怀旧、流离以及荒芜等景象所替代。但是希望和坚韧依然体现在影片中的人物里,他们在找寻自己的失乐园,在坚守着祖辈的记忆和传统道德。
主题和风格上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万玛才旦的导演手法试图要脱离佛教精神及其物质文化。恰恰相反,他显然是想更广泛地、更深入地进入人们的众多社会现实中。他期望履行起初到北京时立下的目标——叙述当代普通藏族人的故事。在《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这两部电影当中,他确实以其独特的现实主义风格兑现了他对观众许下的承诺。万玛才旦目前阶段的现实主义更倾向于表现一些使藏族佛教传统习俗失衡的现代元素。他引导观众见证并触摸其家乡地境,似乎它是一具正在变形的身体:它的外表正经历着一场巨变。在这多重变迁中,佛教成了藏人搜寻民族魂的对象。同时,佛教在万玛才旦的电影前景里成了银幕上下、人物之间、观众群里的一场无形道德争论。贯穿人物内心和外在世界的所有事件和情感基调都被笼罩在势不可挡的现代化生活模式及其价值观中。藏区地境不再是一个由佛教世界观及其习俗所构成的景观。现代化及其物质影响正在以另一套不同空间和心理秩序透入藏人佛教地境并改变其面貌。
在青海拍摄《寻找智美更登》期间,万玛才旦邀请了笔者教授的视觉人类学班的八位学生观摩这部公路电影(road movie)的摄制。公路电影是一种电影类型,常常用于讲述场景移动中的故事,例如朝圣、寻找一件失却的圣物、与遗失爱侣的重逢或因战乱逃离家乡等主题…..这一传统藏族“公路剧”可被视为一种藏民族对慈悲与觉悟终极意义的寻找,这些意义并非以抽象的教规语汇,而是以有血有肉的行为和情感来表达。因为笔者有幸参与了该片的一些后期制作工作,就借机在工作室和小范围初评活动中向万玛才旦问及他的创作意图。他起先的回答是让观众来琢磨影片的涵义。直到某个下午,他让笔者把片名翻译成英语时,笔者提议把藏文片名“寻”(འཚོལ།tsol)字面翻译成英文The Search。当时他和摄影师松太加都说单独用“寻”这个词还“不够具体”,笔者便坚持要求导演直白影片中一车的电影人寻找一位演员的究竟意义。最终,笔者得到了答案:寻找的是西藏文明的本质或灵魂。在万玛才旦的观察中,很多年轻一代的藏人正在失去古老的佛教文化。在他看来,不断扩展的现代价值观正在削弱藏人的佛教心灵。
导演把自己追寻藏文化精髓的思考植入到寻找一位演员的故事片中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在笔者开设的电影课上,万玛才旦告诉学生们,《寻找智美更登》可以是《静静的玛尼石》的续篇,因为藏戏《智美更登》在《静静的玛尼石》中是一个十分关键的主题,被安置在影片的中间时段,有25分钟左右的戏。佛教作为藏人鲜活的信仰被置于影片的中心地带:这个地带不在寺院,而是在普通人群中。为了顺利地完成《静静的玛尼石》中这25分钟的戏,万玛才旦花了许多个日夜在安多地区寻找合适的藏戏男女演员。这是《静静的玛尼石》幕后万玛才旦自已的“公路故事”。在《静静的玛尼石》的前期准备中,他着力物色一个乡村藏戏团以便在影片中表达藏传佛教如何扎根在民间。他寻找藏戏演员的经历成了他编剧、导演《寻找智美更登》的基础。
作为一部公路片,《寻找智美更登》的手法、摄制方式、导演的视角与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导演的《随风而逝》(The Wind Will Carry Us,1999)类似。在这部影片中,一位工程师试图记录下当代伊朗库尔德省的一个秘密葬礼。这位工程师及其队友驾着吉普车穿过田园乡村进入库尔德地区。基亚罗斯塔米的长镜头画面展现出多重地境:红土地、金色的麦田和工程师的目的地——一个僻静的村庄。在这部影片中,一切都在动感和感动中发生。吉普车带动地境移动,地境移动又引出吉普车的移动;吉普车中的对话描绘出基亚罗斯塔米电影叙事的时间线索。在此,我们能看到万玛才旦的创作受到了其偶像基亚罗斯塔米的影响。《寻找智美更登》借鉴了《随风而逝》的拍摄风格,运用大量广角镜头和长镜头,把观众们带入到藏族地境和主要人物(吉普车里的都市藏族电影人)的心境中。
在此,万玛才旦的拍摄风格不再依赖于传统特写手法来传达人物的感情,并以此与观众建立亲密感。相反,就像基亚罗斯塔米的《随风而逝》那样,他在《寻找智美更登》中运用了大量广角镜头和长镜头,不仅通过人的脚步和自然元素,更是通过行驶中的吉普车来抚摸藏区的地境。观众反观性地置身于行驶中的吉普车,把自己移情为司机或者是其中一位乘客。新的视野和景观不断地涌入观众的视线中。当吉普车的轮胎在公路上向前滚动时,观众的眼睛与万玛才旦的镜头是同步的:触及吉普车所到之处、镜头所摄之境。
这是一个感触西藏的旅程。万玛才旦的电影视界为观众创造了这个旅程。尽管吉普车内的空间狭窄,但却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视界。通过银屏与藏区地境的双向感触,观众进入了当代西藏“灵魂”的社会状况。但是佛教在不同场景里显得残缺和零散。剧组想要把完整的佛教找回来。显然,剧组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然而,公路电影的活力不是在于结局,而是在如同朝圣般的旅程中。如果没有获得圣物,朝圣者至少毫无疑问地被自己用朝圣之路所绘的精神情感地图所加持。在路上,《寻找智美更登》剧组在现实生活中先后找到了一位智美更登王子的典范、有丰富记忆的老一辈藏戏演员、最佳女主角、最理想的男主角,尽管他们分散在不同的村庄和城镇。在影片中,佛教受制于世俗中的错位、再定位、衰退和重生,因而完全处于有情众生轮回之苦里。藏戏《智美更登王子》分散地体现在于电影中每一位角色身上,比如,一段记忆、戏中的一段唱词、或者对智美更登王子精神行为的颇具争议的表述里,而非以一个整体出现。尽管男女主角曾经在家乡因同台演出而相爱,但最终还是出乎意料地分手了。故而,剧组期待的完美结尾也因此落空了。
然而,寻找的成功并不决定于最后是否找到了演员,而是在于剧组在藏区的旅程。这个关于藏传佛教濒危的主题开始于《寻找智美更登》,然后在《老狗》中达到高潮。在《老狗》中的一切——人、动物、土地——都进入到马丁·麦史罗恩(MartinMcLoone)所说的为生存意义而进行的“本能挣扎” 。与吉姆·谢里丹(Jim Sheridan)的《田地》(TheField,1990)比较,笔者觉得这部爱尔兰人作品的叙述风格与万玛才旦很相似,特别是通过乡村与公路之间的对立关系来表述父子之间的血亲和道德纠葛。当这些在爱尔兰和藏族地境里人类本能的挣扎及其空间性并列起来时,它们在影像上是相对应的。但是,由于不同的价值观、渴望和现实意义,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抵触的。《老狗》中的小镇对于儿子而言是一个充满获取物质利益机会的地方,而对于父亲来说却是痛苦之源。
草场对于父亲和儿子来说都是他们的家园。父亲觉得根植于它,而儿子觉得被它所束缚。草场与县城之间的路带来了一个又一个不堪忍受的变化。这条路引领儿子骑着摩托车去县城里卖他家的狗,也带着父亲骑马去县城从狗贩子那里追回被卖的狗。整部影片中,这条路把家园与县城连接在一起,它带来了盗狗人、狗贩子、派出所长,并且老狗最后死在了路边。令人震惊的是,在影片中老人的本能挣扎以他勒死自己的爱犬而结束。在《老狗》中,由于万玛才旦持续地使用广角镜头和长镜头,片子的情感基调不是通过对儿子贡布、父亲以及他们家狗的特写来表露,而是把人物情感的波澜导入到他们家乡村子和县城的环境里。因此,县城里的戏显得特别重要,那是家里老狗被卖和被赎回以及父子和好的地方。影片里,贡布的摩托车,父亲的马,他们的老狗和警车是剧情的线索,把村子和县城相互交织在一起。万玛才旦的电影手法使观众不得不去体验无序和心理错位。换言之,使观众感触到人物生活世界的“别无选择”,其中充满了压抑的气氛和对渐渐失去的佛教传统价值观的绝望。
影片的结局引发了观众的各种评议与情绪反应。一些万玛才旦家乡的忠实观众觉得最后老狗的死是不应该的。他们对父亲的不安、愤怒和绝望等感受表示出同情,但是他们认为贡布的父亲应该去保护它,将其视为一位家庭成员。一位来自牧人家庭的观众感言道:“狗的生命属于狗而不是他的主人”。父亲最终与他的儿子和解,却无法保护他的爱狗并且令人费解地勒死了它。
作为一位地境摄影者,笔者觉得万玛才旦对藏区城镇和乡村地境温和但却坚定的影像记录是一种对其跨族群观众“让自己去感悟”的邀请,使观众们对当代藏区有切肤的真实感触。在影片里,万玛才旦的镜头很少对老狗进行特写,但却对它在挣扎中死去的画面却有持续的特写,尽管略去了脸部,但却细腻地刻画了它被勒在栅栏杆上痛苦抽搐的身体。老狗的死亡似乎承担了给人类驱罪的角色,为家庭带来一个新的开端。或者说,老狗是一位不情愿的殉道者,平息了其主人家庭的张力和困惑。然而,在银幕之外,这一艺术效果却在海内外藏人中激起了新的波浪,引发了有关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语境下对佛教伦理和藏族文化之完整性的讨论。
跨族藏人电影景观效应
万玛才旦的电影制作过程是与多种元素交织在一起的:本人的电影创作愿望、响应当代保护藏文化的呼声、在藏区以外获得的电影技术培训和来自不同个人和单位的制片资源。他的制作团队成员通常是多民族的,包括藏族、汉族、欧美人士,他们担任策划、表演、翻译和发行工作。同样,他的观众群也是跨区域、跨族际和跨大陆的,例如,藏区的农村、内地都市、北美和欧洲。因此,对他电影叙述的反馈来自许多不同民族和国家,无论是针对个人还是藏区的社会问题。
在国内藏区和汉地之外,万玛才旦的电影放映渠道通常都不在影院里,而是在很多大学校园里和电影节上。2011-2012年,他在美国访学期间的活动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其欧美观众群的特点。2011年秋,万玛才旦来到了纽约。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的影片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耶鲁大学喜马拉雅中心、印第安那大学中亚和乌拉尔语系国家资源中心以及其它著名大学和机构展映,诸如亚洲协会、利众基金会、独立数字电影公司、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和纽约时报等组织和媒体以专题的形式大力宣传了万玛才旦的影片,报道了对他的影评和访谈。在北美的这一年成了他电影的一个喜庆年。
万玛才旦从北美访学回国后,他的电影继续在欧美国家公映。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电影展(AAS)在2013年3月展映了《老狗》。在藏人和汉人社会中,万玛才旦有多样的观众群体。作为一位成功的藏族电影人,他在汉族观众眼中是一位新秀。万玛才旦在电影节和相关媒体的出场,是针对中国主流观众群的文化视野带来藏人对自己文化的表述。而主流媒体通常把他作为一个成功少数民族的故事来报道。因为大多数国内记者和节目主持人对藏族历史和文化了解不深,他们的访谈内容花了很大篇幅在他的个人经历上。比如《电影艺术》中李韧对他的采访以及北京电影学院崔卫平代表《今天视野》对他的采访。
居住在都市中的藏人通常在家中或者在自己的单位、学校观看万玛才旦的影片。笔者在北京工作时发现很多藏族观众对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观点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观众是一致的。笔者的藏族学生和朋友们从最初对万玛才旦藏语电影的赞扬,演变为对于传统与现代化是否是相互排斥的讨论,同时也对是否可以使用现代方式来保护传统文化进行探索。很多藏族研究生和博士生在为藏人导演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的同时,也开始更深入地研讨万玛才旦影片,并对影片中反映出来的现代化、传统文化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各自学科上的梳理和反思。笔者在和藏族学生和学者讨论万玛才旦影片中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时,我们梳理出了他的一个创作规律,即:万玛才旦的很多影片通过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其中老人坚守传统价值观和习俗,而年轻人容易偏离传统价观念。这个创作情结凸显在《草原》、《静静的嘛呢石》和《老狗》三部影片里。这三部片子里都有儿子的角色,但是只有在《静静的玛尼石》里的儿子,一位年轻的出家人,从老一辈继承了传统的价值观。而其他两部影片中的儿子则撒谎或犯了偷窃罪,不过最终父亲原谅犯错的儿子并与之和解。传统在万玛才旦的影片中终究获胜,但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总之,万玛才旦的电影不仅带动了一个国内外新的观众群,而且也在推动跨学科的藏人电影影评学。
原文正式发表于《中国藏学》2017年第1期,为选段。限于篇幅,删除了注释
作者:郁丹, 云南民族大学环喜马拉雅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译者:刘冬梅,云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