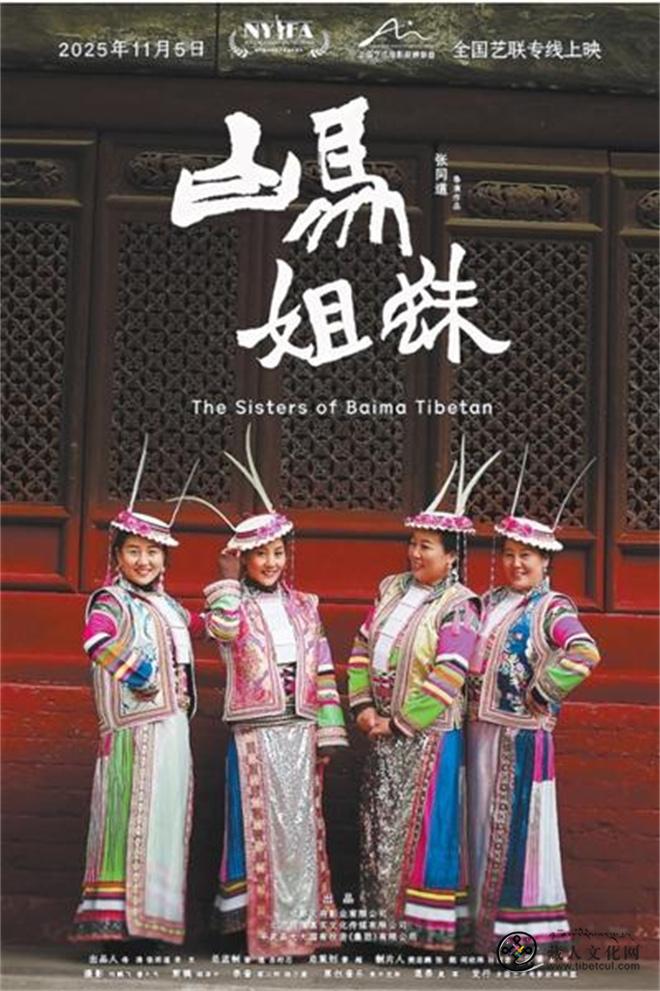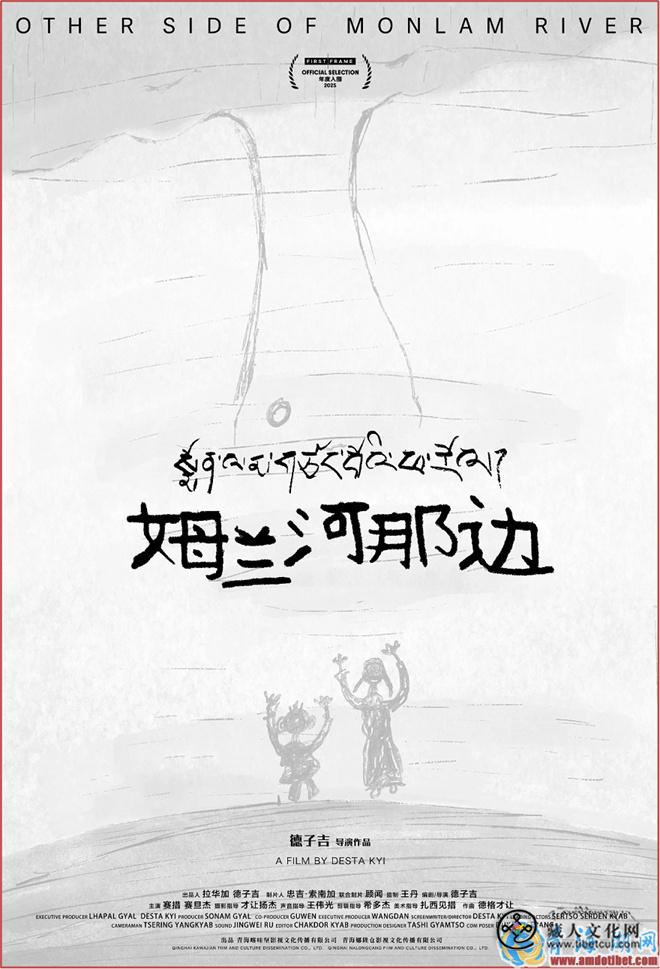西德尼玛不安地坐在镜子前,与镜子平行粘贴的台湾组合SHE的海报因为时间久远已破败不堪,杨秀措站在他身后拿起推刀,双手发抖。西德尼玛可从没想过自己会剪掉这根留了17年的辫子,在藏区,这根辫子几乎已经成为他的标志,人们看到小辫子,就知道西德尼玛的喜剧演出要开始了,“他在藏区喜剧表演上的成就类似赵本山在汉地达到的高度”。直到万玛才旦到找到他,在考虑了两天之后,西德尼玛才说:“为了艺术,就做一次牺牲吧。”
在万玛才旦的新片《塔洛》里,西德尼玛扮演放羊人塔洛,这次不是一个喜剧角色,他的小辫子被心爱的姑娘杨措一口气剪掉,摄像机拍摄由镜子反射出的他们,定镜头,画面黑白,在一种虚假的关系里,塔洛丢失了辫子,也丢掉了自己,西德尼玛为此在内心落泪。
塔洛是个记忆力很好的牧羊人,人到中年才第一次下山办身份证,在警察局里他用念佛经的口吻一口气背完了《为人民服务》:“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在那个时候的塔洛看来,放羊的这一生,即便是死,也是可以重于泰山的,可办理身份证的路途,却让他第一次遭遇了爱情,遭遇了“身份危机”。
在2015威尼斯电影节,万玛才旦带着《塔洛》去展现给世人看一个新鲜但稍显慌乱的藏地,与蓝天、碧瓦、高原红无关,更多是关于现代化带来的疼痛。这并不是万玛才旦第一次展现自己故乡的困惑,这种困惑在不经意间好像就变成了他的宿命。
唐卡
是到了33岁,万玛才旦才有了机会与电影近距离接触。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他的观影经历来自儿时村庄里的露天电影《地道战》,或者黄河边水电工程队礼堂的《摩登时代》,因为热爱,所以电影是一个又近又远的事情。
远在于,藏区基本没有拍电影的条件,他只靠文学创作来表达自己;近在于,当他一步步舍弃老师、公务员这些职业的时候,电影一给他机会,他就全身扑过去了,深厚的文学功底有力地支持了他的电影创作。
他在电影学院第一次看到伊朗导演阿巴斯的作品时,或许就像阿巴斯在睡前站着刷牙的无意间就看完了费里尼的《大路》一样,两者都受到很大的震撼。伊朗与藏区,虽然在宗教、文化背景上存在不同,但于生存状态、街道、村庄等精神面貌上,万玛才旦觉得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使得他们的电影有共同的主题——故乡。
这也是在剧变的中国,青年导演喜爱涉猎的题材,一代人处在失去与寻找的时间缝隙中。早年有贾樟柯的汾阳老家,到了近几年,万玛才旦、郝杰、李睿珺等一干青年导演仍在坚持这种一贯的表达,欲求不满的张家口和沙里淘金的甘肃,城市生活的单调与猛烈来袭远不如逝去的家乡有魅力。
就这样,在电影学院5年,万玛才旦全身心扑在电影上。2005年,他有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作品《静静的嘛呢石》,讲述一个小喇嘛回家3天的故事。这部全部用35mm胶片拍的电影,用李陀的话说是“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他称这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合二为一,天衣无缝。
一个镜头打天下,无论是全景还是中近景,都没有明显的景深和透视变化,影评人杨潇说:“这种拍法对于经受严格视听训练的电影学院学生来说或许是不成气候的:40mm拍全景,切成近景还是40mm。可是我恰恰认为这一拍法极其适合这片视域广阔、性情憨直的西藏土地和人民的,对于西藏人来说,这片辽阔得很难看到参照物的土地是否存在明显的透视?”
对于万玛才旦来说,这种远距离给予藏区的生活一种平凡感,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藏区,是他熟悉的故乡。与此同时,这样的拍摄也不容许观者有亲密感,成为真正的旁观者:我们所看到的藏区是荒凉的景象,单调的生活,以及一个家庭每日挣扎着面对全球化带来的压力。
平静的日子也充满浓稠的隐喻:小喇嘛和弟弟在看《智美更登》(传统藏戏),觉得无聊便跑去影厅看香港电影,没钱又跑去正在演出的“智美更登”要了10块钱,小喇嘛遇到电影里的色情镜头赶紧跑出来,要回了钱去买零食,买了“唐僧肉”、娃哈哈和孙悟空面具。
这场戏在时间轴上并不是万玛才旦所要描述的主要事件,按照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万玛才旦扩展了所述事之中的一些事件,时间总是消失在他的叙事中。这种勾勒故事的方式,在美学上像传统藏画,像唐卡。
但在《静静的嘛呢石》里,新与旧,外来与本地,摩登与传统,还尚且能平静相处,未有你死我活的激烈对抗,暗涌初开始。
到了万玛才旦第二部长片《寻找智美更登》时,他也还在不辞疲惫地讲智美更登的故事。智美更登是谁?他是西藏民间传说中的一位王子,释迦牟尼的化身,舍弃荣华富贵,踏上虔诚的修行。在修行的道路上,他将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妻子,自己的眼睛都施舍给了比自己更匮乏的人。在这种几近不合人情的奉献中,他达到了修行的绝境。?
这个故事伴随着万玛才旦的成长,流淌在传统藏人血液中,虽然到了今天的藏地,也有学者会基于人权角度质问智美更登是否有权力施舍自己的妻子与孩子,但对于万玛才旦而言,这个佛教的象征人物,仍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寻找智美更登》讲述一个电影摄制组,要拍一部有关智美更登的电影,一路寻找扮演智美更登和他妻子的男女演员,找到的女孩很合适,可她的要求是,要找到她变心的前男友,来演智美更登。不同于《静静的嘛呢石》故事发生在一个小村庄,《寻找》是一幅藏区生活画卷,像一部短暂的“西游记”,最终寻找到的“经书”(男主角)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中经历的故事与人,交织在一起,促发迷惘和感伤。
片中有三种藏族人。一种代表旧日的藏族,淳朴、真诚,信奉旧日的宗教,散发智美更登的光辉。他们是扮演智美更登妻子的农村女孩,是把自己的妻子施舍出去的老者。
另外一种代表今天的西藏,比如酒吧里蔑视爱情的歌手,女孩的前男友,扮演卓别林的藏族演员,以及不会唱藏戏的藏族表演团孩子们。他们越来越不像传统的“藏族人”,反而像个城市人。片中导演向藏族歌手陈述智美更登的核心精神为“慈悲,关怀,宽容和爱”,后者,一位藏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的反应却是嗤之以鼻。但至此,万玛才旦也没有跳出来大声疾呼。
还有一种人,投射了万玛才旦本身,即是片中摄制组一群人,处于旧日与今天之间。他们仍在寻找智美更登,他们仍相信怀念旧日的爱情,但也仅能怀念无法触碰。退回旧日的西藏如此不可能,迈入今天的西藏又如此水土不服,但他们就是此刻最真实的藏地。
徘徊
迄今为止,万玛才旦的团队多半都是藏族,在跟随万玛才旦之前,他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录音师德格才让早年是兰州的地下摇滚乐手,十年后,他变成资深录音师,说着流利的京片子。而万玛才旦曾经的摄影师松太加,已凭借自己导演的电影《河》进入柏林国际电影节。
万玛才旦一边需要电影所需的一切资源,一边又向往着从前边陲乡村的生活。去年,他硬是把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儿子送回青海的一所寺院学校学了一年藏语藏文。
相对于《静静的嘛呢石》的不安,《寻找智美更登》则更多表现出了藏地的失落与无所适从。
到了万玛才旦的第三部长片《老狗》,情绪可谓是“决绝”。电影里没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白云,更多时候是破损的残酷街景,现代化建设中的藏区满路泥泞。万玛才旦用数字设备进行拍摄,意在描绘这个扁平,落寞的家园。录音师德格才让花了十多天的时间来录制家乡在电锯中建设的声音,不知声源的《格萨尔王》苍凉无力地播放着,无处诉说。
这是这几年藏地现实对万玛才旦的一次集中刺激,剧本五六天就写完了,视听设计过程中,他感到极其压抑,有时觉得喘不过气,“在很多放映场合,我都不忍再看这部电影”,万玛才旦说。
儿子要将家里养了13年的藏獒卖掉,不然他料想这老狗迟早会被小偷偷走,近几年城里人养藏獒成风,卖掉自家的藏獒已是普遍现象。父亲反对,找到买狗人把藏獒要回。儿子、父亲、买狗人三者由此扭结在一起,老狗的命运陷入极度的悲剧中。
贫困的牧民如何在国家支持的经济发展下越发边缘地面对日常生活?原本自由的草原被铁栅栏围起来,这是出台不久的新政策:结束牧场的公共使用。在一场戏里,一只绵羊被卡在围栏中,挣扎着要进入草原另一半的羊群,这是喜剧穿插,也是围栏政治。
买狗人试图说服老者,告诉他老狗到了城里生活会更好,老者反问:“那城里人为什么要养狗呢?”当买狗人加价到两万时,老者的绝望到了极限。他带着心爱的老狗,在这铁栅栏的柱子上,结束了老狗的生命。
就像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乡愁》中的那个疯子,他手举着蜡烛走进水中。一个有尊严的人如何处理入侵带来的复杂影响。
这或许成为描述藏獒这个高原犬种发展的最后一部电影,无关于他勇猛的神话,却是他被迫无奈的商品化。
魔幻
万玛才旦也曾带着他的电影回到藏区流动播放。在拍摄《静静的嘛呢石》的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的村落,他们把大荧幕插在草地上,来了两三千人看他的电影,荧幕正反两面都坐满了人,大家用新奇的目光盯着那些熟悉的面孔,至今,万玛才旦回想起这些画面,还觉得感动。
拍摄时,一些僧人在看了一两天现场之后,觉得拍电影特别没意思,“他们说如果知道电影是这样拍的,他们就不会去看电影了。他们之前可能把电影里面的事都当成了真的,看了实际的拍摄过程才知道是假的,”万玛才旦笑道。
相对于万玛才旦小说里的藏人生活,电影实在显得太无趣了。真实的藏族人是生活在神话里的,即便是史学著作,也会把历史事件和神话故事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要搞历史研究,妄图从那些史学著作里寻找史料很强的内容是比较费劲的”,万玛才旦说。
他们执拗地相信,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没有那么清晰。这也是小说世界里那个更自由的万玛才旦。
相对于扎西达娃笔下藏人的神秘,阿来笔下藏人的澎湃,万玛才旦的小说作品,都是藏族生活题材,关于爱情、孤独、死亡,他笔下的藏人更充满了合理的温情与刻薄,更接近藏人日常的想象。
一个沉浸在恋爱甜蜜里分不清白天昼夜的痴情郎,一个为了体验瞎子的一天要用红领巾蒙上眼睛的小学生,或者一个和陌生的外国人在草原上抱头痛哭的牧羊人,每一个人都在高原各怀心事地承接自己的幸运与苦难,有的人有神相助,有的人独自死去。
“因为离开故乡了,就会有审视的目光,在老家,他们对信仰是没有疑问的,当你离开一段时间,再回头看,可能会有变化”,万玛才旦对记者说。
和他的电影叙事类似的是,万玛才旦总将人物的语言和动作巨细靡遗地写在纸上,穿插着牧羊人从母亲那里听来的传说,或者另一个藏族女孩复杂的恋情,转眼间,他又去描述一只藏獒备受煎熬的状态,张献民听他讲故事的时候总会忍不住问:“那后来呢?”
没有后来,“在他的叙述之外,是白茫茫黑压压的一片”,张献民说。
这种“瘦骨嶙峋”的叙述,在张献民看来与人到中年早已不瘦的万玛才旦不太相像。在中国和欧洲的一些古典绘画中,都会出现一个极瘦的老人周边常常是彻底的黑暗,万玛才旦的小说叙述亦是如此,只有一个核心的部分,再略带些皮肉。“空间是空的,你无法知道那个村子到底什么样子,也不好判断两个地点之间的距离,甚至没有风景。时间也不大重要,比如到底是现在还是20年前,到底是几天前还是好几个月前的故事,大量的东西都交付给虚空了”,张献民如是评论。
虚空之外,又是秩序的体现。21个卓玛、9个男人、8只羊,以及嘛呢石上的六字真言,每一笔描写都像一个寓言,但细节之外,没有结论。万玛才旦从不直接描写佛教教义,然而潜在的文化记忆和精神框架弥漫在文本之中,形成了一个个似幻似虚的现实故事。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藏地处处都是魔幻现实,人与神,人与灵,不得不共处一片土地。万玛才旦早期的小说《神医》《诱惑》《没有下雪的冬天》等,无一不触及偶然与荒诞的存在之思。也往往缔造出一种在虚无中追求、在绝望中反抗与徘徊的境地。
“我的小说都是写着写着就出来了”,万玛才旦说。创作《塔洛》时,他写下第一句:“塔洛平常扎着小辫子”,本是他脑海中的一个臆想,然后塔洛去办身份证,在没有框架的情况下,淳朴的牧羊人塔洛就这么在充满霓虹灯的县城悲伤地丢失了自我。
“生命像风中的残烛,财富如草尖的露珠。”
不是那个被猎奇的藏地,是另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
作家阿来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为什么藏族人就要睡帐篷给外地的游客看?”扎西达娃也怒斥:“正如多数人从没能走进草原深处一样,谁又曾走进牧人的心灵深处?”
在电影与文学里,藏地都处于悲观主义作者的无尽担忧中,“以后可能就没有像塔洛一样的牧羊人这个职业了”,万玛才旦说,迫切往外走的年轻人把荒芜的草地留在身后,近几年他们总爱唱《走出大山》一类的歌曲,但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比塔洛幸运,能找到自己的爱情,或者新生活。万玛才旦也一样,他把这片充满神话的土地装在行囊里,飞过大西洋,神话便在别的地方也生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