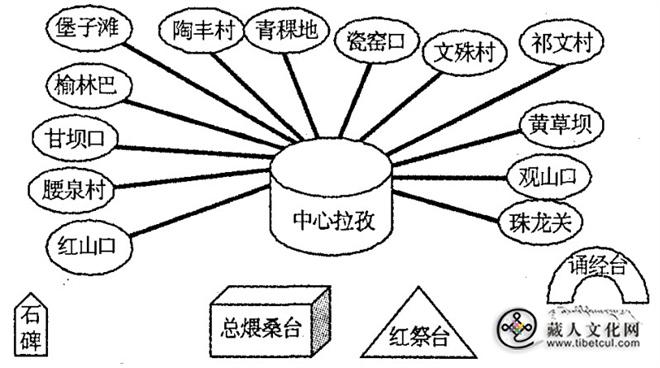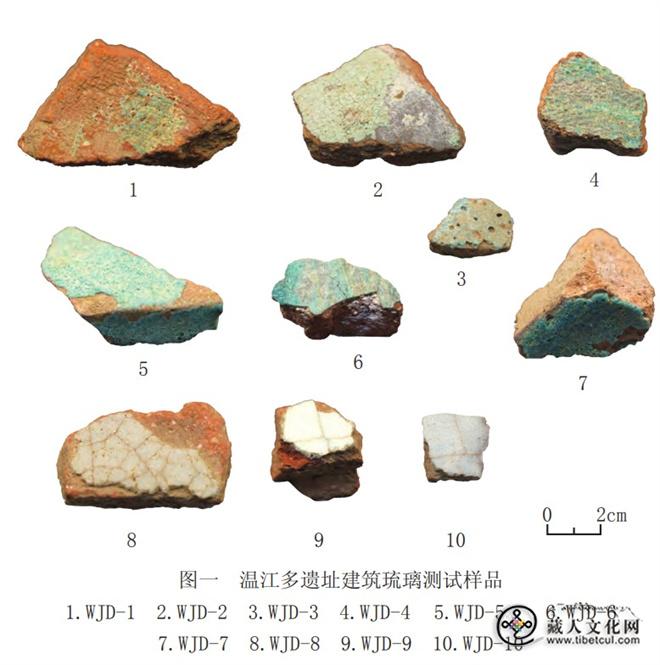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学界关于《大清律例》在西藏推行的时间一直没有定论。文章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汉文等多语种档案认为,在处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后,乾隆十六年(1751)清中央便在西藏全面推行具有国家法性质的《大清律例》。文章指出,《大清律例》在西藏的运用,一方面从刚开始对重大政治性案件的审理过渡到了对民间刑事案件的审理;另一方面,不仅汉族、藏族二族间在西藏发生的命案需遵照国家法来处治,而且藏族人之间发生的命案,凡告到官府,也可以用国家法来处理。这些档案文献的相关记载,反映了清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西藏地区推广王朝法律思想和加强法律内地化的强烈意志和具体实践。
关键词:《大清律例》;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刑事案件
一、引言
通过驱准保藏、平定叛乱、抗击侵略等一系列活动,清朝逐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在此过程中,清廷多次颁布治藏章程,在不断调整治藏政策的同时,对西藏地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和完善,如乾隆十六年(1751)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乾隆五十四年(1789)颁布《设站定界事宜十九条》,乾隆五十五年(1790)颁布《酌议藏中各事宜十条》,乾隆五十八年(1793)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等等。从乾隆朝至清末,在西藏颁布章程或条例凡十余种,但这些章程多属行政法令和规章制度,主要用来划定西藏地方行政官员的职责和权限、限制僧人干政、规范内地与西藏商贸活动等。我们注意到,对西藏民间刑事案件的处理,并无具体指导。
清朝在边疆地区施行因俗而治的治理方略,其突出表现为在维护清朝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在法律层面尊重和认可当地习惯法、部落法等。与此同时,清廷针对不同民族的不同情况,也颁布适应于当地的特殊法令,如在蒙古地区颁行《蒙古律例》,在维吾尔族聚居区颁行《回疆则例》,以此加强统治。
西藏地方比较特殊,有西藏传统的地方法,有清朝颁布的地方法,还有具有国家法性质的《大清律例》。关于《大清律例》在西藏的推行,国内学者也有所讨论。孙镇平认为,西藏刑事犯罪,汉人适用《大清律例》,藏人适用西藏地方法,甚至回人用回例,施行汉、番并行制度。马青连等人在研究清代西藏刑事案件审理和判决时,对《大清律例》的适用情况进行了分析。“就具体的司法实践来说,大体上遵循两条路径发展:一条路径是《大清律例》从刚开始只适用于西藏地区的汉人之间的案件逐步发展到汉藏等各民族之间的案件再到藏族人之间的案件;另一条路径是《大清律例》从开始仅仅适用于重大的政治性案件和影响较大的宗教案件,发展到重大的刑事案件到普通的刑事案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有清一代,朝廷对于西藏地方的民事问题基本不予干涉,因此《大清律例》中的民事法律部分基本不适用于清代的西藏地区。”黄维忠梳理了由清中央政府在藏颁布的所有类型法律文书,其中重点关注到《大清律例》在刑事案件中的运用问题。冯志伟等人分析了清代藏族与满、汉、蒙古、回等民族间众多案件,讨论了《大清律例》在其中的适用问题。尽管如此,以往的西藏刑事案件研究仍然多以《清实录》《理藩院则例》和西藏诸多章程为根本材料,而对作为清朝国家大法的《大清律例》在西藏的运用情况关注较少,尤其没有涉及其在西藏首次运用的时间。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无法找到充足的案例来论证,对清中央和地方档案的利用还不够充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藏有大量涉及西藏刑事案件的满、汉、藏文档案,通过这些档案资料,我们可以对西藏何时开始运用《大清律例》断案的问题,以及《大清律例》在西藏的适用范围等问题作初步的讨论。
二、《大清律例》在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中的运用
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大清律例》在西藏地方的首次运用是在乾隆十六年对反叛分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1750)同党的处治上。
乾隆十五年十月十三日(1750年11月11日),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二人用计除掉了谋叛的西藏郡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但两位大臣和驻藏官兵随后被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余党所杀。乾隆皇帝随即派四川总督策楞等人前往处理,并指示说:
俟总督策楞、钦差大臣兆惠、那木扎勒、班第等公同查审。照内地之例,分别首从,惟诛首恶及附和为恶者,其余胁从人等,俱从宽概无株及。所有擒获逆党之头目人等,著班第达查明,俟策楞到日,酌量赏赐,以示鼓励。其劫夺银两,事甚微末,当扰乱之时,乘机攘窃,无从一一查究,转恐累及无辜。其已追得者,交司员收贮;未得者,免其查追。朕此番办理,惟欲藏地永远宁谧。
策楞于十二月二十一日(1751年1月18日)到藏,将处理结果报告乾隆皇帝:
查各逆犯,聚众为乱,杀害大臣,劫夺帑银,凶悖已极,应即立正国法。随于二十五日将为首之卓呢罗卜藏扎什与领众放火抢夺帑银之阿喇卜坦、吹木扎特,杀死多人之车臣哈什哈,放鸟枪、弓箭打伤大臣之达尔汗雅逊、巴特马古尔济椿丕勒、妄介俱凌迟处死;听从贼首,杀人、运草放火、先行上楼助恶之尚卓特巴拉扎卜、曾本旺扎勒、曼金得什鼐等俱斩决;随从作乱之通使扎什喇卜坦等俱绞决;惧罪自尽之杯陇沙克巴、监毙之拉克滚布俱行戮尸,与各磔犯一并碎骨,仍各枭首示众。余党分别发遣,家产变价归帑。报闻。
谕旨中所提“内地之例”,当为《大清律例》。《大清律例》规定:
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官。若女(兼姊妹)许嫁已定,归其夫。(正犯)子孙过房与人,及(正犯之)聘妻未成者,俱不追做。
从量刑和处治结果来看,这一起案件的处理是完全遵照《大清律例》执行的,故引文所提到的国法指的应该是《大清律例》。按照《大清律例》以上律文,对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子女也进行了处治。乾隆皇帝下旨:“朕前已有旨曰,因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之子女尚年少,其父所为,与子女无涉,解送来京居住等语。今因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恶逆昭彰,理宜以叛逆罪依例处治……律例载:将谋反者之女,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据此似当将此二幼女同他犯共同押送至京为宜。”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发生后,拉萨社会动荡不安。“事后清查,还有千总二员、兵四十九名、家人商民七十七人被杀,共计死了140多人,市上大乱,粮务衙门官库的帑银八万五千余两被抢走。达赖喇嘛闻讯派近侍僧人和色拉寺、哲蚌寺上师到现场劝阻,乱众不听。”关于商民被杀情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所存《驻藏大臣班第纳木扎勒奏请将劫杀商人抢夺财物之首犯喇布坦正法从犯约尔扎尔等发遣折》,报告了以喇布坦、巴桑为首的藏族人杀死4名汉商、掠夺财物的刑事案件。这份奏折原文长达十余页,事主口供十分详细,以下为笔者节译: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指使我等与罗卜藏扎什(luobuzangdaxi)家奴约尔扎尔(yuljal)、曾本普尔普(sengbun purpu)家奴巴桑一同赴purbucuk山之喇嘛占巴处,侦视有何人送何物,并随时记录来往人员之举……约尔扎尔即赴罗卜藏扎什处问询,行至小召处,听闻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为诸大臣所杀,诸大臣旋遭杀害,且听闻居藏之汉人将被悉数杀尽之语。巴桑等言与吾:此处住有汉人四名,我等为何不将其擒(杀)之?然于寺院地方不宜动手,可将其诱诓至浪荡沟第巴处拿下。欲将之告知于罗卜藏扎什,途中遇车臣哈什哈,将之告与之,车臣哈什哈言“甚善!汝等将其杀死,送来首级,必将受赏”。……与巴桑一同返回第巴处,自吹木扎德(cuimjad)处取四名差役看守汉商。巴桑自汉商身上搜得钱十四两,喇布坦我搜得钱二两,挟令其行于前,我等行于后,至拉子(raci)城,遇四名不相识之番人,问其来由,言特来查拿汉人。巴桑言:若来查拿汉人,吾已捉来四汉人矣,汝等可将其取之。吾可遣回原四名差役,汝可至无人之处将其戮之,可得奖赏矣。……遂将此等汉人交与该四人,遣返自浪荡沟携来之四名差役,行至临小召之桥,巴桑下马交与吾看管。巴桑与四番人一同将四名汉人携至东部低洼之地,戕杀之。将汉人衣物等物悉数给予此四人。巴桑将四名汉人首级悬于鞍头,送往车臣哈什哈处领赏。深夜方至藏,未寻得车臣哈什哈,遂将首级携至巴木巴尔(bambar)地方抛弃。前往博绒沙巴(boirong šakba)处途中遇一队人马,夺去吾等所乘骑之马,适取巴桑乘马时,巴桑乘隙弃马逃脱,不知去向,吾所乘马驮有奶油、茶叶、猞猁狐皮等物;巴桑马驮有红毡子一张,吾所获赃物甚重,未及拆阅,我等商议待至博绒沙巴处后再分赃。约尔扎尔乘马无驮物。
驻藏大臣上奏了对该案件的处理结果:首犯巴桑逃亡,尚未归案。被抓获从犯喇布坦虽未动手,但全程参与了该事件,与首犯同罪斩立决。同伙约尔扎尔因参与将汉商诱骗至被杀地点并看管等事,判以流放罪,发往南方满洲军为奴,其妻子送交刑部。很明显是严格遵照《大清律例》来处罚的。该案件虽然看起来是桩典型的图财害命案,但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有关。罪犯之前在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手下办事,指使其犯罪的罗卜藏扎什和车臣哈什哈系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重要余党,后均被处死。故该案件属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的延续,从性质上来看属于重大政治性事件,与处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余党一样,用国法处治是理所当然的。
三、《大清律例》在西藏民间刑事案件上的运用
《大清律例》在西藏民间刑事案件上的运用,实际上也是在乾隆十六年。乾隆十六年六月十三日,西藏发生了一起命案,驻藏大臣接到报告后进行了处理,并就此事上奏皇帝裁决。笔者认为,该案件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普通案件,可视作典型刑事案件,能很好地反映法律适用问题。为更好地展示这一案件的过程,笔者将驻藏大臣满文奏报全文翻译如下:
奏。奴才班第、纳木扎勒谨奏为将图财害命之贼犯正法以示警诫事由。
近日,噶伦公班第达等咨呈:其所辖贡布地方之番民齐罗特、旺结二人杀死一内地经商之民人,掠夺其财物。该处第巴头人闻讯即遣人寻其逃亡方向将其追拿之,搜出其所掠财物以看管。该当如何处置,呈请诸大臣裁夺等语。
闻报后,(奴才)遂就近遣拉里粮员焦通(jeo tung,音译)、熊兴(hiong hin,音译)查验尸伤。验得:查验得知系高士玉之尸,死者,素称高三。其伤情(如下):右耳根一石伤,后脑勺发际根处一石伤,肤俱损,骨亦破,颈一刀伤,喉已断,左肩一石伤,除此无他伤。未寻得所击杀之石,寻得凶刀,将凶刀与伤口比对相符。又查得知,高士玉祖籍陕西固原州,身亡前于民商郭登云家中存放马一匹、锅二口。既已掩埋高士玉尸骨,将贼犯齐罗特、旺结及其所掠红白褐衣二十九件、银六两,及衣物等一并提解来藏。即送至,奴才遂召集公班第达等人会同逐一亲提审讯。
齐罗特供曰:小的系贡布之第巴属人,二十岁,贫不聊生。今年四月二十九日,民商高士玉拟将自珠拉(jukla)地方所购衣物携至胡查朗多(hūrcak langdo)地方换取黄连药,租用我等背负(褐衣),议定为我等给付脚钱三钱。五月初一,至硕卡(xok’a)地方,伊又雇用唐古特(番)人旺结,令其与我共同为其背负褐衣,当日至丁当(dingdang)地方宿住。次日,日夜兼程,高士玉行于前,我与旺结一同负褐衣随其后。即时,我与旺结商议:我等俱为贫苦即将饿死之人,此汉商处衣物甚多,我等将之分取以糊口也。旺结言:我等若将之分有,必先杀死此人方可行之矣。小的我即从其言,同行至舒(šu)地方,小的我拾石一块,朝高士玉耳根处一击,高士玉即昏倒。我亦出刀割其喉,旺结拾石击其左肩,又击其脑后根,高士玉即死。旺结自高士玉身上搜出银六两,银指环四枚,银钱二文半等物之后,我等将其分有之。至砻布(lumbu)地方时,不料为官人罗布(norbu)等得讯,寻踪而来将我等捉拿,物件(赃物)亦被连同携至之,我等当死,无可奚辞。
旺结供曰:小的我二十二岁,硕卡地方第巴属人,因家贫无以聊生,五月初一,民商高士玉至我处,雇用我等为其负褐衣,商定给付脚钱三钱。我与齐罗特为其负褐衣,当日于丁当地方宿住。次日,天未亮即起身出发时,齐罗特见(高士玉)有褐衣甚多而先起心,于我言:我等将高士玉物件分有也。小的言:若分取其物,必先将其杀死后方可行,否则必会出事。齐罗特即从我言,至舒(šu)地方河岸,齐罗特遂拾石一块击倒高士玉,出刀割掉其颈。小的旋即拾石击其左肩,又击其脑根处,高士玉遂丧命。小的畏罪,恐为人所见,急投高士玉尸骨入河中,藏凶刀。我与齐罗特将其红褐衣十四、白褐衣十五、银六两、银指环四枚、二文半钱、绢绸一匹分有之,一同畏避至砻布地方时,官人策凌罗布率十余人将我等追踪捉拿之。此俱属实,无他同伙,此前亦无行盗之举。
此二人为杀死高士玉之举,供认不讳。伏查例载,图财害命而杀人者,不分首从,斩立决,拟将齐罗特、旺结依例正法,斩立决,以示警诫。此二人言无家业外,死者高士玉于此处全无同伴及亲属等,因其子于四川成都府,将其褐衣、衣物、马、锅等物交与粮员通判滕炯齐(teng joo ki)以示公平买卖,乘便送至四川总督大臣衙门,继而交付所属大臣。查出高士玉之子,将之点交其子。得旨后,谨遵奉行,为此谨奏请旨。乾隆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七月十四日朱批:知道了,钦此。
值得注意的是,奏折中“伏查例载,图财害命而杀人者,不分首从,斩立决”之“例”,当指《大清律例》。与该案件时间最接近的是乾隆五年颁布的《大清律例》,其中“刑律·人命·谋杀人”规定:“凡谋(或谋诸心,或谋诸人)杀人,造意者,斩(监候)……若因而得财者,同强盗不分首从论,皆斩。”其所附条例进一步解释说:“一、凡谋财害命,照律拟斩立决外……若杀人后掠取家财,并知藏蓄而取去者,审得实情,仍同强盗论罪。二、凡图财害命应分别曾否得财定拟,其得财而杀死人命者,首犯与从而加功者,俱拟斩立决。”为齐罗特、旺结二人定罪,用的正是这一条。上引《大清律例》还强调,因而得财者,同强盗论罪。对于强盗罪,《大清律例》规定:“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但得(事主)财者,不分首从,皆斩。”为了解释“强盗”概念,乾隆五年的律例附了27项条例,但还是未能界定清楚,而早在唐代的《唐律疏议》对“强盗”则有较清晰的界定:“谓以威若力而取其财,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又补充说:“假有以威胁人,不加凶刃,或有直用凶刃,不作威胁,而劫掠取财者。”齐罗特、旺结二人持凶器且有计划有预谋地杀死汉商,案情并不复杂,犯罪事实清楚,是典型的杀人越货、图财害命案,二嫌疑犯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这一切对法官来说依法量刑定罪甚易,然清代在边疆地区施行因俗而治政策,在民族地区还颁布了众多地方法,而且遵循属地法原则,故处理汉藏二族间在藏发生刑事案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干扰因素较多。在此复杂背景下,驻藏大臣第一时间做出的反应不是将此事委托给达赖喇嘛和诸噶伦,而是想到需以《大清律例》来定罪,并上奏皇帝。
乾隆皇帝接到奏报后于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字寄谕:
驻藏管旗都统班第等奏称:将杀害商民高士玉、图财害命之齐罗特、旺结二人提审,拟依律定斩杀罪斩立决,以示警诫。得旨后遵旨办理等语。藏地地处边陲,道路遥远,无法与内地相比,此二贼因杀人当偿命,应即时正法。照今内地依法定罪矣。然称候旨定夺,未免拘泥。嗣后藏地若有此类应行正法之案,有罪大恶极者,不必候旨后方处理,汝一面办理,遇奏事之便奏闻即可。就拿获二贼之人,亦应量予奖赏,将此传谕班第、纳木扎勒知之。
乾隆皇帝于七月十四日命将此谕旨日五百里驰递至藏。驻藏大臣班第等人于八月二十一日接旨,表示嗣后若再出现此类案件将遵照皇帝训令行事,即刻办理。
看来乾隆皇帝是坚决支持此类普通命案照国家法《大清律例》来处理,而且要求此后发生类似命案无须奏请,可当即斩立决,先斩后奏,说明朝廷将死刑权下放给了驻藏大臣。按清朝规定,死刑案件需层层审批,决定权最后掌握在皇帝手中,在非特别时期直接授权地方官员处死罪犯的情况,在清初中期极其罕见。还需注意的是,“嗣后藏地若有此类应行正法之案,有罪大恶极者,不必候旨后方处理,汝一面办理,遇奏事之便奏闻即可”之语,可进一步说明此类事件系首次发生,故乾隆皇帝特发指示。
在中国古代,敕令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乾隆皇帝的该项指示成为之后驻藏大臣处理汉商在藏被害案典型案例来援引。
第二年,巴塘地方3名藏族人流浪到浪荡沟,因生计无继,共同密谋杀死汉商劫掠财物。3人谎称卖羊,将一汉商诱骗至无人之所后杀死,瓜分了汉商随身携带的银钱。就此,驻藏大臣上奏说:“奴才窃查律书载:图财害命者,不分首从,皆斩。”鉴于主犯扎克巴扎西于狱中畏罪自杀不论外,扎木巴吹扎克、阿旺楚勒因与扎克巴扎西一同合谋图财共同杀害苏十斤(su ši gin),罪大恶极,将二人即依律应立斩决示众。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5名藏族人合伙于凌晨潜入他人房屋,杀死熟睡中的汉商掠夺财产事件。驻藏大臣强调将依律处治。由此可知,上述乾隆十六年的案件不断被援引,成为一个不成文的法令为后世所遵循。
以上讨论的诸案件都发生在藏汉两族间,对此,西藏地方既未遵守属地原则,亦未遵循属人原则,而是直接以国家法处治。这有力地说明,但凡在西藏发生汉藏间刑事案件,均以国家法处理。
关于藏族人之间发生的刑事案件,亦有参照《大清律例》处治的例子。嘉庆十六年(1811)九月,驻藏大臣奏报了一起民间命案:江孜20余里之白勒地方河内,有一番民被人杀死,旋被放牛小娃子巴桑雀瓜看见,呼叫附近蛮寨居民郭巴等寻踪追赶,当将凶犯洛尔结拿获,并据番民罗加查认系伊子弥玛尸身。凶犯洛尔结途遇番民弥玛,见其身背兜内装口袋数个,该犯闻知弥玛欲赴江孜做小生意,遂起杀机,跟随弥玛至河边,共同饮酒,假借剃头,连扎毙命,抢走随身财物。此事被报到官府。驻藏大臣认为:“以此图财谋害,实属凶残已极。伏查例载,图财害命其得财而杀死人命者,拟斩立决。此案洛尔结应照例拟斩立决,但西藏为极边要地,番夷凶犷性成,年来屡有恃强行凶杀死人命之事。该犯洛尔结如此凶残,若不即依正典刑,无以儆凶番而彰国宪,是以奴才等不敢拘讯成例,于审明后当即恭请王命,委粮员贡布、游击萧太和会同噶布伦等将凶犯洛尔结绑赴市曹即行处斩示众。”
这起案件充分说明,《大清律例》不仅在判决藏汉刑事案件时有效,即使在藏族人之间发生刑事案件时也同样有效。此案件属于西藏民间非常普通的命案,并不属于重大案件。即便如此,驻藏大臣还是按《大清律例》处治。我们目前所见驻藏大臣处理的刑事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汉藏两族间,而藏族人内部间案件处理记录极少,说明西藏民间大部分案件多以传统地方法内部解决。但从见到的文献看,凡被报到官府的案件,官方一般都会考虑按照《大清律例》来处治。
四、结语
以往研究讨论《大清律例》在西藏推行的情况时,前贤多从《清代藏事奏牍》《藏牍劫余》等资料集中寻找案例,但这些资料集主要收录了清末部分大臣的部分奏报,不系统、不完整,容易给人造成清代国家法至晚清方在西藏得到实施的错觉。也有一些人认为,驻藏大臣从晚清开始才被授予就地正法权。但本文所引案例清楚地表明,早在乾隆时期,驻藏大臣就已经拥有就地正法权了。
通过以上研究可证,作为清朝国法性质的《大清律例》在西藏得到实施是不争的事实。清朝自雍正年间始设驻藏大臣,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后废除郡王制,次年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提高了驻藏大臣权力,也为清朝的西藏法律建设提供了保障,驻藏大臣开始放手处理各种刑事案件,促进了西藏法律制度的发展进程。《大清律例》自乾隆十六年在西藏首次推行后,一方面从刚开始的重大政治性案件的审理过渡到了民间刑事案件;另一方面,不仅汉藏民族间人员在西藏发生的命案需遵照国家法来处治,而且藏族人之间发生的命案,凡告到官府,也可以用国家法来处理。清代满、汉、藏多语种档案文献的相关记载,反映了清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西藏地区推广中央王朝法律思想和加强法律依循国家上位法的强烈意志和现实实践。
作者简介:特尔巴衣尔,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5期 为便于阅读,脚注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