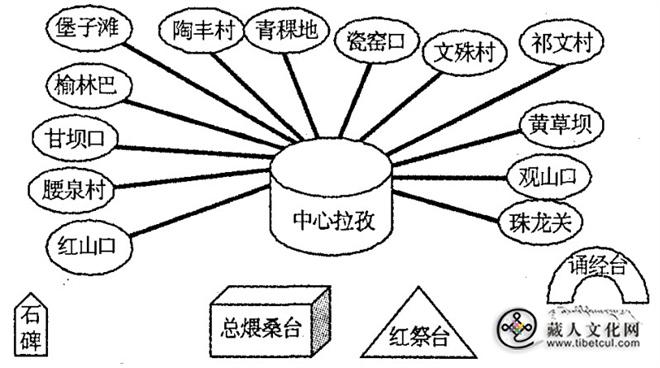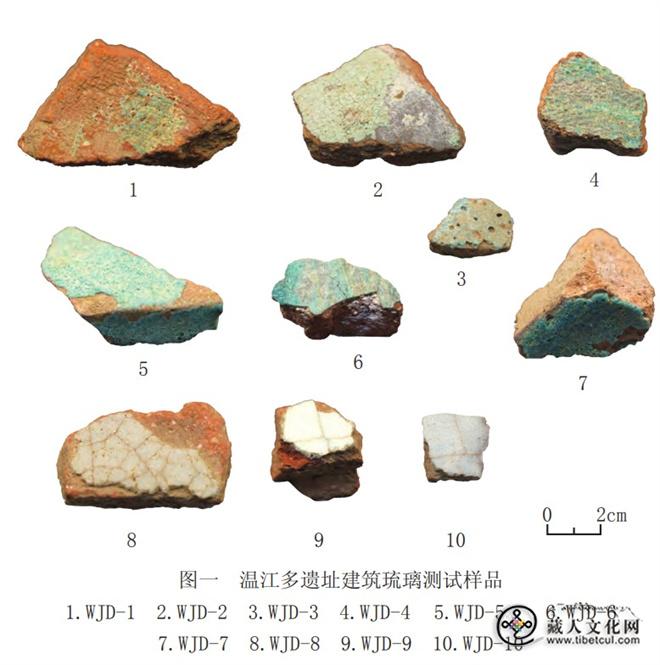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曾晓鸿
摄影:曾晓鸿
摘要: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是清宫存藏藏文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特定的藏文公文写作规范和档案属性。档案中所见藏文公文与汉文译本,以及汉文檄谕与藏文译本,构成可资比较、互证的对译文本,揭示出乾隆时期涉藏地区土司与清廷中枢、地方衙署之间沟通联系过程中不同语种公文传译释读的具体状态。藏汉文文本对译分析表明,汉文译本能够相对准确地译述藏文公文的主要信息,藏译檄谕大致符合藏文文法规则和行文表述习惯,但在称谓概念、信息择取和语气表达等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乾隆时期藏汉文公文传译的实践层次和翻译水准。由于两金川之役公文传译问题丛生,清廷不断调整和完善译写处理机制,将中央、四川地方传译系统整合起来,形成特定的互动关系。不同民族或社会身份的译员群体基于清代四川涉藏地区军政事务需要,共同参与、推动和影响着两金川之役公文传译的作业流程,塑造和展示了乾隆时期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体现出清代汉藏民族语言、文化深层次交流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公文传译;译员群体
多语种档案文献的参酌互证和综合运用,是近年以来清代边疆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趋向。不同语种档案文献的对译研究直接关系到清代行政公文的传译机制,揭示出清代多语文政治文化形塑和构筑大一统政治体系的实践过程。清代中前期藏文公文翻译的译员选任、机构设置、情报文书和基层公文传译等问题已有不少开拓性的讨论和探索。但是囿于译文文本的缺乏,相关研究大多偏重公文传译的制度设计和过程演变,而且对中央与地方传译系统的内在联系有所忽视。作为清宫存藏藏文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与汉文或满文译本、檄谕等构成一组组相对完整的对译文本和互证史实案例,成为进一步深入探讨清代公文传译问题的珍贵素材。本文以数十份藏文、汉文的对译文本为基础,透过文本观察人的历史活动,还原和检视乾隆时期两金川之役公文传译的作业流程,分析文本背后多民族共同参与、缔造清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历史进程。
一、两金川之役藏文、汉文公文文书的对译比较
两金川之役是乾隆时期边疆治理事务中的重要历史事件,遗留下数量可观的汉文或满文公文档案,以及少量藏文文书档案。特别是第二次金川之役(1771—1776)前后,涉事土司致函清军将臣、地方吏员的藏文函件,构成特定的官方文书档案类型。这些藏文文书在清代汉文档案中通常被称为“番禀”“夷禀”或“番字禀帖”,主要存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金川档、录副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军机处档折件、宫中档杂件中,共计50余件。时段涉及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四十二年(1777),尤其以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三十八年(1773)最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存藏的清代档案文献源于同脉,均属于以内阁大库档案为主的清宫档案,其中藏文档案的存藏数量不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藏数量相对较多,亦仅存300余件。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不见于事发地,即四川省档案馆、阿坝州档案馆等各级档案馆的清代档案中,应属清宫存藏的独有文书档案。
就文体种类而言,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大多属于奏书,包括上行文书的呈文(སྙན་ཞུ)、禀文(ཕུལ་ཡིག)等,兼有少量下行文书,如檄谕(བཀའ་ཡིག),及平行文书,如信函等。奏书的致函者以大金川(然旦,རབ་བརྟན)、小金川(赞拉,བཙན་ལྷ)两土司为主,另有邻近的绰斯甲、党坝、梭磨、卓克基、孔撒、德格、果洛等土司。藏文文书原件纸质,一般无固定尺寸,或为边长均等的方纸,或是长宽分明的长条纸。行文以手写无头体撰成。书写格式遵循一定的程式和规范,大致分为抬头尊称、敬禀者自称、正文、落款年月、印章等部分。文书的抬头尊称与正文之间、正文与落款之间均留有一至三指宽的空白,即敬空符。
抬头尊称顶格书写,前有起头符࿐(ཡིག་མགོ),结尾往往以དྲུང་དུ,或ཞབས,或ཞབས་དྲུང་དུ,即“尊前”作为提示词,引出敬禀者自称和正文。敬禀者自称通常与正文相接,文前留三至五指宽的空白,结尾以ཞུ་གསོལ作为提示词,有时写为ཞུ་ཡིག་འབུལ་འབྲལ,或ཞུ་ཡིག་ཕུལ་དོན,或ཞུ་བ,或བྱིན་ཐེ་ཕུལ་དོན等,即“呈禀如下”,引出正文。文中大皇帝(གོང་མ་ཆེན་པོ)、钦差大人(སྐུ་ཚབ་ཏྰ་ཞིན)、将军(གཙང་ཀྱུན)等称谓前均缀有敬重符༧(ཆེ་མགོ)。此类文书程式与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存藏的甘丹颇章政权时期藏文公文档案颇为近似。落款年月前同样顶格书写,前缀起头符,改书内地正朔,援用年号纪年、阴历纪日月。少数文书将年号、藏历两种纪年方式并列,如ཆེན་ལུང་དགོང་ལོ་སོ་བདུན་ཆུ་འབྲུག་ཟླ་༢་ཚེས་༢ལ་ཕུལ།(乾隆三十七年水龙年二月初二日),或仅沿用传统的藏历纪年方式。落款处加盖清廷颁授的朱红色土司官印。两金川之役藏文文书自成一体,具有特定的书写风格共性,包含趋近王朝官方表述的政治规范。
“投禀”屡见于档案文献记载当中,是现存两金川之役藏文文书的主要来源方式,也是清代土司与地方衙署,乃至清廷中枢政治沟通的主要渠道之一。清代涉藏地区土司无权,亦无途径直接将藏文奏书呈递皇帝或军机处。即使在两金川之役结束后,土司的禀帖仍须改投成都将军,若径投军机处则属僭越违例。由此,藏文文书以“原禀”形式,与译禀(或称“译出夷禀”)、供单等组成汉文或满文奏折的“夹单”附件,并不具有独立的公文档案属性。
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的独特属性与清代军机处的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乾隆时期是清代军机处正式形成和职能扩展的关键阶段。作为清代重要的内廷机构,军机处的迅速成长、职权日重得益于乾隆时期两金川之役等重要战事的推动。而奏折制度构建起的通信体系,则是军机处绕开外朝机构获取重要信息的主要渠道。藏文文书常被充作军政信息,附夹于奏折中。乾隆十三年(1748)张广泗案的导火索正是经略大学士傅恒遵旨接到参赞大臣傅尔丹的奏折报匣,“内有小金川土司泽旺番禀一件,系告张广泗家人、通事与汉奸王秋勒取泽旺财物”。所以事关重大的禀帖、供词等机要信息,由参与战事的文武职官径直呈送军机处,“今天这些有价值的资料通常只能在军机处的档案中找得到。”对于事涉两金川土司的藏文文书,乾隆帝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解决大金川与革布什咱两土司纷争案时曾颁谕:“各土司文书大概系用唐古忒文字,该处翻译恐不尽其详细,一并传谕该督等,嗣后接到各土司文书,除一面办理外,即将原文进呈。”自此,藏文文书随附于文武职官具奏的奏折中,一同进呈军机处,衍为惯例。这是为何多数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存藏于军机处奏折中的原因。由于缺乏汉文或满文的录副条件,藏文文书以原件形式保存下来,成为直观反映土司与清廷、清军将臣、地方衙署沟通交流的原始档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类原始档案在研究当时历史方面,具有格外的史料价值,值得学者注意。
现存多数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即“原禀”)能够在清代档案中寻找到对应的汉文译本(即“译禀”)。两者大多散存于不同档号档案中,极少数共存于同一份档案内。而且汉文“译禀”、檄谕等文本多达90余件,远多于藏文“原禀”。这就为藏文文书与汉文译本的对译比较,从文本分析层面深入认识乾隆时期公文传译与多语文政治文化的实践提供可能。
通过对证分析可知,藏文“原禀”与档案所见汉文“译禀”的主体内容大致相仿。汉文“译禀”能够相对准确地表述出藏文“原禀”的主要信息,并无严重的脱漏或讹误之处。但是藏文“原禀”的翻译在内容上仍然有所取舍,通常是漏译非实质性信息,而译写紧要的主干内容,或补充必要的解释性信息。例如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大金川土司致定边右副将军温福的藏文“原禀”正文起首写道:
དེང་། སྐུ་འཚོ་ལེགས་བྲིས་དབང་པོའི་མཛེས་སྡུག་འོད་དུ་འབར་ཞིང་མཛད་འཕྲིན། ༧གོང་མ་ཆེན་པོའི་བཀའ་ཁྲིམས་གསེར་གྱི་གཉའ་ཤིང་ལྷོ་གླིང་གི་སྐྱེ་དགུ་ཡོངས་ཀྱི་སྤྱི་བོར་བསྒྱུར་ཞིང་།མཐའ་ཡས་འགྲོ་བའི་དཔལ་དུ་བཞུགས་བཞིན་པ་ནས་བཀའ་ཤོག་ཕྱར་ཅིག་སྤྱི་བོར་ཕེབས་པའི་འབྲུ་དོན་ཞིབ་ཚོགས་གོ་བའི་དགའ་སྣང་ཉི་མ་ཤར་བ་ལྟར་སྤྲོ་བ་ཟད་མེད་དུ་ཆེ་ཆེ།
译文:如今,贵体安康如仙界之王光辉照耀。大皇帝之法令王法金轭已架于南瞻部洲所有众生之项,众生福德皇帝之御令一份已收悉,并详尽领悟其意,内心如阳光照耀般无比喜悦。
档案所见汉文“译禀”:我们见大人们的谕帖吩咐的话,我们都知道了。
又如,大金川土司在同年九月呈递的藏文“原禀”中将抬头尊称写作: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ནམ་སྐོས་གོང་མ་ཆེན་པོའི་ཁྲིམས་གཉིས་མངའ་བདག་གཙང་ཀྱིན་ཏཱ་ཞིན་རིན་པོ་ཆེ,即“文殊天授大皇帝之二法人主将军大人仁波切”。汉文“译禀”简写为“万岁爷的将军大人”。
可以看出,汉文“译禀”并未顾及藏文书写和表达习惯,将藏文“原禀”起首的赞颂词当作冗句删减掉,有意忽视藏语文生动、感性的传统表达方式及其宗教色彩。这是汉文“译禀”较为普遍存在的现象。译员往往偏重有效信息,迎合汉文文本的表述惯例,或省略、改译部分地名信息,如将小金川东达卡(དུང་ལྟར་ཁབ)意译为“官寨”,拉嘎卡(ལ་ཀར་མཁར)改译为“边界上”等。译员在删减、改动部分语句的同时,时常依据语境填补藏文“原禀”未曾说明的信息。比如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梭磨安抚司土司卓尔玛(སོ་མོ་ངན་ཧུ་སི་ཐུའུ་སི་སྒྲོལ་མ)藏文“原禀”追溯当地瘟疫流行的缘起时称:དེ་སྔ་འདས་པ་ནོར་བུ་གཤེགས་རྗེས,意为“之前讷尔和去世后”。汉文“译禀”补充译写为:“我男人梭木土司讷尔和早年死了。”信息的完整性应是译员基于对地方情况的熟稔,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和处理的问题。
藏文“原禀”与汉文“译禀”的书写语气、词意表达有所差别。乾隆三十七年初小金川土司致定边右副将军温福的“原禀”辩解称:
སྲོག་འཕྲོག་བྱེད་པ་པོ་ལ་གནོད་ལན་བྱེད་པ་འདི་ནི་འཇིག་རྟེན་གང་ལ་རུང་ཞིང་།
译文:对于夺命者予以还击,是符合世间常理的。
档案所见汉文“译禀”:沃日要害我性命,我才报仇。
又如,同年九月大金川土司致四川提督哈国兴的“原禀”正文起首称:
ཏཱ་ཞིན་རིན་པོ་ཆེ་སྐུ་ཁམས་མཆོག་ཏུ་དྭངས་ཤིང་མཛད་འཕྲིན་མངའ་རིས་ཞིང་ཁམས་ཡོངས་ལ་བདེ་སྐྱིད་སྤེལ་བའི་གཉེན་དུ་བཞུགས་པ་ནི་འགྲོ་བ་གང་གི་སྐྱོབ་པའི་དཔལ་ཡོན་བླ་ན་མེད་པ་ཆེ་ཆེ།
译文:大人仁波切贵体安康,为利益所有辖区内幸福之功绩,是一切众生的至上福德。
档案所见汉文“译禀”:大人万福金安!我们听见大人到我们地方上行好事,我们就沾恩了。
藏文“原禀”的语意表达更为迂回、婉转,符合藏语文的交涉技巧和表达艺术。汉文“译禀”的语气和表达较为生硬、直接,明显具有译员译意的痕迹,或将译员的情感、观念代入译写中,无法准确地传递藏文“原禀”字里行间的细节信息。这或许是乾隆皇帝、清军将臣一再声称“所投文禀,词意鸱张纵恣”“其词悖妄可恶”的重要缘由。温福等则依据汉文“译禀”来理解藏文“原禀”之意,抨击哈国兴的作为:“臣等详加体察哈国兴到营未久,该逆酋何以遽有听闻,且禀内有行好事之语,明系因哈国兴等许令退地,故藉此为词。”两者的对译差别可能对乾隆帝和清廷中枢的政治决断,判定大小金川土司政治姿态和清军将臣统驭边务应对能力,以及官场内部权力倾轧等产生潜在影响。
重要概念、称谓的译写最能体现藏文“原禀”与汉文“译禀”的文本异同之处,这类问题大体呈现两种不同的状态:一是各自表述的差异性。如藏文中的གོང་མ་ཆེན་པོ一律被译写为汉文语境中习称的“万岁爷”,前者时常作འཇམ་དབྱངས་གནམ་བསྐོས་གོང་མ་ཆེན་པོ,被赋予涉藏地区宗教的威权属性,而后者则更具世俗政治的特性。类似事例如སྲས་སྐལ་བཟང被译为“土舍僧格桑”,དཔོན和ཏ་རོ被统一译作“头人”,ངེད་རྒྱལ་རོང་ལུགས被改译为“我们土司家的规矩”等。二是译写表述中的借用和互鉴,如“大老爷”(ཏ་ལོའུ་ཡེ)、“父母官”(ཧུ་མུ་ཀོན)、“将军”(གཙང་ཀྱུན)、“禀帖”(བྱིན་ཐེ)等。藏文རྒྱལ་པོ常对应汉文“土司”,内涵各异。但是藏文文书将“土司”的藏文音译ཐུའུ་བསི与རྒྱལ་པོ并行混用。涉藏地区土司在一定程度上理解ཐུའུ་བསི的政治内涵,并将之借用和内化于涉藏地区本土政治文化表述中。རྒྱལ་པོ的另一种写法རྒྱལ་བདག被译写为满文中的“扎勒达克”,并与汉文“译禀”中的“土司”联系起来。但是敬禀者自称如ཏ་གྱིན་ཆྭན་ཐུའུ་བསི་སློབ་དཔོན་དང་རྒྱལ་བདག་རྣམས,在不同汉文“译禀”中存在“金川应袭土司索诺奔们”“大金川色勒奔土司们”“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掌印土司”或“大金川土司色勒奔连做土司弟兄们”等不同译法。这表明译员能够理解ཐུའུ་བསི与རྒྱལ་པོ共同的“土司”含义,却似乎无法辨识涉藏地区土司政治文化中སློབ་དཔོན和རྒྱལ་བདག两词的关系,从而引发乾隆帝对大金川土司署名问题的疑惑和不解。因此,文本对译的多义性和歧异性暗示译员应当普遍对涉藏地区土司区域的地方性知识缺乏深入认知;藏文文书专有称谓的译写存在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统一规范,细节偏于模糊,倾向尽量趋近汉文的表述语境。
与翻译藏文文书相比,汉文檄谕的藏译更能作为检验、展示乾隆时期公文传译状态和水准的依据。目前笔者所见唯一一份两金川之役汉文檄谕藏译文书,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四川重庆镇总兵董天弼名义拟给小金川土司泽旺的藏文檄稿。汉文檄稿由乾隆帝谕令军机处代拟,藏译檄稿以藏文手写无头体撰写。除少数语句脱漏外,藏译檄稿基本上是逐句翻译,大致符合藏文文法规则和行文表述习惯,且在皇帝尊称前缀有敬重符,对应汉文檄稿中的抬格。语句表达为符合藏文行文语境有所增减和改译。例句如下:
汉文檄稿:尔泽旺久系内地土司,向极恭顺,屡受大皇帝厚恩,理应竭诚感戴,乃尔子僧格桑敢与索诺木狼狈为奸,肆行叛逆,抗拒王师,其罪实不可逭。
藏译檄稿:ཁྱོད་ཚེ་དབང་སྔར་ངེད་ཀྱི་ཐུ་སི་ཡིན། གུས་འདུད་ལེགས་པར་བྱས། ༧བདག་པོ་ཆེན་པོའི་བཀའ་དྲིན་ཁུར་ཞིང་། ད་ཆ་ཡང་དྲིན་གཟོ་བྱེད་པར་རིགས། ཁྱོད་ཀྱི་བུ་སེང་གེ་བཟང་། རབ་བརྟན་གྱི་བསོད་ནམས་དང་སྡེབས་ནས་དམག་འཁྲུགས་སྣ་ཚོགས་བྱས་ཏེ་ངོ་ལོག ངེད་ཀྱི་དམག་དཔུང་དང་འཐབ་པས་ངེས་སར་ཡང་ཆ་གཏོང་ལུགས་མེད།(你泽旺过去就是我的土司,很恭顺。大主人施恩,现今理应报答。你儿子僧格桑却与然旦索诺木擅起兵衅,抗拒我大军,难饶你性命。)
汉文檄稿:今闻本镇统兵进剿尔境,尔尚不知及早悔罪,仍容两金川贼番与官兵打仗,是尔自寻死路,断难复冀一线之原。
藏译檄稿:ད་ཆ་ངེད་ཀྱི་དཔུང་ཁྱོད་ཀྱི་ས་ཆར་སླེབ་པས། ད་དུང་ཁྱོད་མྱུར་བར་མི་ཡོང་བར་རབ་བརྟན་དང་བཙན་ལྷ་གཉིས་གྱི་གྲོགས་བྱས་ནས་དཔུང་ཆེན་དང་འཐབ་ན་ཁྱོད་ཀྱི་སྲོག་སྐྱབས་པ་ཤིན་ཤིན་ཏུ་དཀའ། ཁྱོད་འཆི་བ་ལས་འོས་མེད།(如今我大军到你地盘,你却仍未速来。如果然旦与赞拉两者互为奥援,抗拒大军,难饶你性命。)
可以看出,藏译檄稿最为突出的翻译问题仍集中在重要概念、称谓的译写上。如“大皇帝”被译为བདག་པོ་ཆེན་པོ,与གོང་མ་ཆེན་པོ的含义截然有别。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སྐལ་བཟང,意为“善缘”)依据汉文读音,被误译为སེང་གེ་བཟང(“善狮子”之意)。尽管受制于跨语际翻译的文化差异和历史条件,藏文檄稿难以完全复原汉文檄稿的词意表述和行文语境,但是能够灵活译写,相对准确地将汉文檄稿的主体意旨呈现出来。
二、公文传译的作业流程与译员群体的多元身份
两金川之役档案所见藏文文书与汉文译本、汉文檄谕共同构成可资比较、互证的不同语种文献集合体。文本对译的比较分析可以直观反映出乾隆时期官方译员群体应对藏汉文公文文书互译的实践层次和翻译能力。那么,乾隆时期官方译员群体如何构成?公文传译的作业流程具体怎样展开?藏文、汉文公文的互译转写通过何种文书处理机制得以实现?
两金川之役前,四川督抚提镇衙门专设译字房,由书办充任,负责译写藏文文书,不设职司翻译的专缺职官。兼管地方事务的州、县等地方衙署同样设有通事译字,部分藏文文书直接由州、县衙署的通事译字就近翻译。如乾隆八年(1743)六月,大金川安抚司世袭事以“投禀”方式呈递四川巡抚硕色。藏文禀帖由保县(治今汶川县威州镇)差役张谟携出后,当即由县署通事译出,乃至“因大金川土司既系生番,不谙汉文,自应照例饬取夷结,令保县翻译汉结,代造宗图”。但是藏文文书的译写状况频出,译本水平参差不齐,常有严重讹误之处,影响到清廷中枢掌握边地信息的准确程度。乾隆初年就曾出现过将“瓦寺”另译为“瓦斯”,令人错判为两处不同地名的现象。乾隆二十八年(1763)六七月间,乾隆帝鉴于四川涉藏地区事重繁杂,针对“唐古忒字译汉,自有一定音释”问题,特意谕令四川总督衙门,“向设笔帖式二员,嗣后著于理藩院熟谙翻译人员内拣选一员,前往补授。一应陈奏事件,如有喇嘛、番民等名字,俱著斟酌对音”,通过设置藏语文翻译笔帖式职缺,杜绝藏文文书译写的错讹问题。
理藩院选派笔帖式充任四川督府藏语文译员,依例为三年轮番差遣。这对于改善四川地方衙署的藏语文译写状况,保障四川地方事务实施和推行起到一定作用。乾隆三十年(1765)四川总督阿尔泰奏请,“留任笔帖式诺慕齐三年期满,请再留任三年,如能愈加奋勉,俟有边地相当缺出,奏请送部引见。”可见四川地方衙署面对复杂多变的涉藏地区政治环境,对此类“技术官僚”的需求和重视程度。四川地方衙署以书办、通事吏役为主,笔帖式译员为辅,构成一套相对独立的基层日常传译系统。至两金川之役,特别是第二次金川之役期间,清廷中枢为搜集、获取更多可靠和准确的战事信息,对藏语文译写的需求急剧膨胀。即使金川军营将臣也不得不承认,“查军营遇有呈报番禀及发给檄谕,所用翻译书写之人多系提镇衙门所带译字房书办,原俱不甚谙习……臣等又不能识认番字,其舛误必不能免”。地方衙署通事或笔帖式的译写工作已然无法满足战事进展的需要。
藏文文书的译写问题再度引起清廷中枢的关注,起因于金川舆图中地名音译的混乱现象。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战事信息的搜集、传递,谕令清军将臣定期以驰递奏报、绘制舆图、粘签说明等方式,翔实呈报边情战况及相应部署,且力求驰奏快捷、准确和细致。故而乾隆帝多次批评进呈的舆图地名颇多舛误,未足为据。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二月乾隆帝对清军将臣绘制舆图的详略失当颇为不满,特别是地名的音译问题,特地谕令:
此等番蛮地名,多系西番语音,如杂谷、刮耳崖等名,其本音并不如此,皆系绿营书识等信手妄书,遂至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方今一统同文,凡属旧部新藩地名,无不悉按本来音韵,即金元旧史之未协者,亦为厘订其讹,岂有边徼诸番,转听其名译紊淆之理!此等西番字音,必当以清字对之,方能悉耶。此后应将番语译出清字,再由清字译出汉字,始不至如前此之鄙陋可笑。
出于战事需要,清廷中枢开始一再申饬清军将臣规范藏文文书的译写:“嗣后遇有对音之字,宜详加斟酌”,并着手对地名、人名等关键译字进行统一厘定。作为乾隆帝推崇的“国语”,满文充当起汉文、藏文的传译媒介,“土音为西番字所不能通者,并著询明该处土人,用清字对音”,并很快从名称对音,扩展到文本的对照翻译。藏文文书的传译流程从“番语”→“汉字”,改为“番语”→“清字”→“汉字”。这与汉文檄谕从“汉字”→“番语”的直接藏译有所不同。因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主要集中存藏于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部分附带有满文译本。
藏文文书的译写规范工作吸纳格鲁派高僧三世章嘉呼图克图若必多杰(1717—1786)参与。章嘉呼图克图在乾隆十三年(1748)就曾受乾隆帝委托,接受过傅恒有关金川土司汉译名称问题的咨询。到第二次金川之役期间,章嘉呼图克图肩负起译写或审核藏文文书,校对和解释词汇、语义,以及将诏谕藏译的职责,俨然成为清廷中枢的藏语文翻译顾问。乾隆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773—1774)间,在章嘉呼图克图的协助下,清廷中枢随着战事推进,陆续针对已知的两金川地名、人名,缮写出藏、满、汉三种文字词汇对译的字样文本,并在乾隆帝的授意和督促下,对重要的藏文名称如拉布坦(即然旦,རབ་བརྟན)、莎罗奔(སློབ་དཔོན)、扎勒达克(རྒྱལ་བདག)、凯立叶(མཁར་རེ་ཡོ)等字词含义详加查询考证。对于夹附于奏折中的藏文文书,清军将臣谨遵乾隆帝谕令,“嗣后凡遇番禀,一面译出大概,仍将原禀恭呈御览,或令章嘉胡图克图详加音释,或交唐古忒学译出,发给臣等遵照。”部分藏文“译禀”往返传递于地方与清廷中枢之间,经过多次译写修订,最终存藏于军机处奏折档案中。
为有效治理西藏地方,清廷中枢对藏文文书的翻译,经历从依赖驻京喇嘛到培养译员、专设唐古忒学的转变历程。到乾隆中叶,清廷遣派以八旗蒙古生童为主的译员赴藏学习藏文。唐古忒学教习、考核、制度架构等渐成定制。马子木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档案和官书,认为清廷中枢在第二次金川之役期间译写藏文文书主要依靠唐古忒学译员译出,辅助章嘉呼图克图的译写校对。藏文文书的译写在清廷中枢形成相对固定的专职译员群体和规范的翻译流程。但是两金川之役藏文文书译写的规范,时常受制于藏语文的地域差异。清军将臣早就意识到准确翻译两金川藏文名称颇为困难:一是边地各处藏语文之间互存差异:“查瓦寺、鄂克什、三杂谷、丹坝、绰斯甲布、巴旺、布拉克底、两金川各处,均谓之甲垄。其番人言语,不惟与西藏之唐古忒迥殊,即与南路之明正各土司亦须通译”;二是边地地名众多、繁杂:“番地名字最多,或一坡而上下攸殊,或一岭而东西各别”,令人难以辨识。而且,有关藏文文书的战事信息沟通牵涉清廷中枢、清军将臣、土司之间的联动关系。由于乾隆帝一再申令整饬驿站递送事务,军务文报的驰递成为清廷中枢快速掌控军情和下达谕令的重要渠道,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传递最新的边务军情,并将决策、谕令反馈回金川军营。这大大推进和加速了藏文文书译写的程序进度,使之融入军情文报的驰奏驿递系统中。即便如此,从土司“投禀”、清军将臣呈递奏折到朱批反馈等一系列奏事流程完成,最快也需十天甚至半月时间,无法及时解决金川军营的译写需求,保障时效性信息搜集等问题。因而藏文文书的译写处理机制相比于西藏地方要复杂得多。
根据第二次金川之役期间清军将臣的奏折陈述,各土司“投禀”军营的藏文“原禀”一般最先由“随营通事”当即译出,译本即奏折“夹单”中所谓的“译禀”“译出禀词”或“译出番禀”。例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一月温福呈递的奏折,原本附有檄谕三件、“译出夷禀”一件和“夷字原禀”一件。“夷字原禀”为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小金川土司泽旺致维州协都司马诏蛟的藏文函件。经对译查找,“原禀”与“译出夷禀”散存于不同档号档案中。后者正文与温福呈递奏折中引述的“译禀”内容一致,大抵将藏文“原禀”完整译写,主旨内容并无太大区别。藏文“原禀”由温福“即令能译番字之瓦寺夷人将夷禀大概译出”。这进一步证实现存两金川之役藏文文书的部分汉文“译禀”,是由非专职的地方译员群体翻译而成,体制之外通晓本土藏语文者经常客串译写藏文文书的译员角色。
温福奏折中提到的“瓦寺夷人”是瓦寺土弁格登布(或译为格特布)。据乾隆三十七年三月温福等奏称:“各土司派出认识番字,并能书写之人,又不能通晓汉话。惟瓦寺土弁格登布虽不能书写,而通晓番话,并能汉话,凡有文禀,臣等皆令其通说”,“臣等查军营翻译,各通事有汉人,亦有番人,原系杂凑而成”,“嗣后凡遇番禀,如访有深通翻译者,令其译出附进,否则臣等仍令格登布等译出大概。”温福等的奏陈透露出金川军营藏语文译员群体驳杂的民族、社会身份。特别是土司或土屯遣派充任的临时译员始终承担着问询、译写等文书要务,颇受清军将臣的信任和依赖。如第二次金川之役后期参赞大臣海兰察军营以土练都司穆塔尔兼任通事。定西将军阿桂军营的藏文文书译写“向不用绿营字识”,而倚重老实本分的屯弁安布木:“凡有番禀,皆派出章京眼同阅看,令屯弁通事,逐句念出,即逐句写清。”藏文文书的译写工作常常是谙熟藏语文的土弁兵、汉藏随营通事、译字房书办、僧侣或章京等共同合作的集体行为。
由于译员构成复杂和水平参差,金川军营藏文文书译写时有讹误或误导之处,乃至引发清廷中枢对时局形势的误判。乾隆三十九年(1774)阿桂奏折附带的三杂谷(即梭磨、卓克基、松岗)呈递藏文禀帖,“原禀令曾习番字之中书济尔噶朗图译出清文,并无诞妄之语,与阿桂处原译之汉字不符。恐济尔噶朗图于番字文义不深,复令章嘉胡土克图另译,与济尔噶朗图译出之字大略相合。是三杂谷土司并无可恶情节。前此阿桂处所译之字,或系译字番人与杂谷土司不睦,故为增减,或绿营字识不习番语,妄为音译,皆不可知。”为此,部分重要藏文“原禀”呈送清廷中枢后,由军机处遵从乾隆帝谕旨,指派济尔噶朗图等唐古忒学译员或委托章嘉呼图克图另行再译。两金川之役档案中“奏遵旨译毕”“译呈”“军机处奏遵旨翻译”等字样的“译禀”,大抵属于此类再译的藏文文书译本。再译文书遵循“番语”→“清字”→“汉字”的传译流程,与金川军营可能继续沿用“番语”→“汉字”的译写方式有所不同。故而现存两金川之役档案中汉文“译禀”众多,而满文“译禀”仅有寥寥数份。
事实上,清廷中枢同样缺乏能够通晓两金川之役事发地藏语文的合格译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乾隆帝曾谕令,“军营屡次所译番禀,虽音字讹舛者多,而文义大概尚合,想该处绿营音译之人,于番字尚能谙习,著温福等即选派熟练音译番字者一人,由驿赴京备用。”“文义大概尚合”的评断大致与文本对译比较的结果吻合。选拔译员赴京备用说明唐古忒学亦无法完全满足战事的译写需求,转而寻求来自地方传译系统译员的协助。四月,温福等就选派译员赴京之事回奏道:
因军营所当番字之人,未甚谙习,不足备用,是以行令松潘镇维州协各衙门,于所设译字房书办内,详加甄选。兹据各该处派送五名前来。臣等复逐一考验,求其汉字、番字、汉语、番语并能通说译写者,竟不可得。内惟维州协战兵焦俞崇一名,能通番语、识汉字,但不识番字。又维协食守兵粮之屯练阿甲一名,番字、番语俱能书写通识,亦略通汉语,而不识汉字。合两人之长,可备翻译之用。
选派赴京的译员以汉、藏弁兵互补结合的方式得以解决。折中的选派方式与清代中央、四川地方传译系统的差异不无关系。清代前期唐古忒学纳入国家职官体系,构建起中央层级专职藏语文译员的培养机构,主要面向清廷中枢输送藏语文专职译员职官。而四川地方基层传译系统缺乏严密的培养、考核和选任机制,将通事、译字书办限定在吏役层面,译写水准反而不及民间自发形成的汉、藏语文传译者。前文所述汉文檄谕藏译文书即由金川军营选派赴京、熟习藏语文文义的通事兵丁译出,颇能展示其藏文文书的译写能力。因此,两金川之役将朝廷、四川地方传译系统联系起来,围绕文本译写、译员选用等形成特定的互动关系。清宫存藏的藏文文书译写是由汉、藏、满、蒙古等多民族职官、弁兵或僧侣群体共同完成的。
三、结语
清代是多民族共同参与、奠定和缔造中国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重要历史时期。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政治层面沟通联系的过程、机制和特点成为深入理解、认识清代大一统政治格局实现的关键问题。多语种官方档案文献即是探讨清代多语文政治文化如何进行深层次实践的主要依据。
与汉文、满文等档案文献有别,两金川之役藏文档案存量有限,却具有独特的公文档案属性和学术研究价值,是直观反映涉藏地区土司与地方衙署及清廷中枢互动交往的原始文本资料。各土司借助藏文文书与地方衙署、清军将臣、清廷中枢之间的沟通互动,也是不同语种文本传译释读的过程。作为奏折“夹单”附件,藏文“原禀”的主体内容能够在汉文“译禀”中得到较为准确的呈现,又在有效信息择取、行文语气表达和关键称谓概念等层面存在明显差别。档案所见数量更多的汉文译本的基本内容并无太大问题,可视为藏文“原禀”相对准确的对译文本。但是若要深入探讨汉文“译禀”的文本语境,需要以藏文“原禀”与汉文“译禀”文本对译互证的异同关系作为分析阐释基础,不能完全将汉文译本作为讨论、印证涉藏地区土司“主位”视角的直接证据。
两金川之役藏文文书译写是清代基于四川涉藏地区军政事务需要,推进不同民族语言文字之间深度交流、构建“一统同文”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现。边务军情的掌控和处理促使清廷亟需重视语言文字的互译沟通,不断改进公文译写机制,统合中央、地方的传译系统。多民族身份的译员由土屯兵练、随营通事、绿营弁兵、唐古忒学译员、僧侣、地方衙署译字房书办、笔帖式及从征的土司属弁等人员构成,成为乾隆时期沟通汉藏政治交往的中介群体。在清代大一统政治需求的背景下,不同民族、阶层或区域身份的群体扮演着寻求多语文政治文化“共性”的角色,共同推动了清代各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与文化互鉴。
作者简介:邹立波,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教授;红音,民族学博士,藏族历史文化学者。
原文载于《中国藏学》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