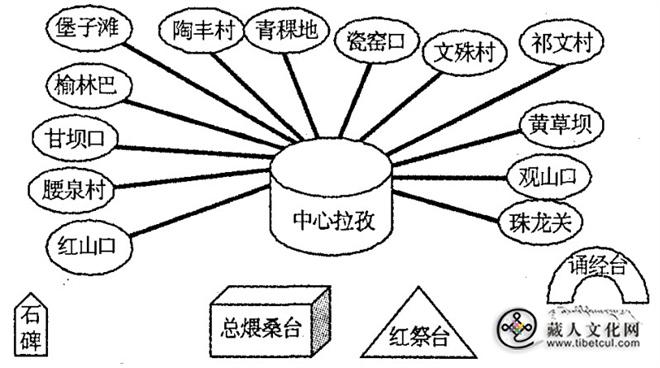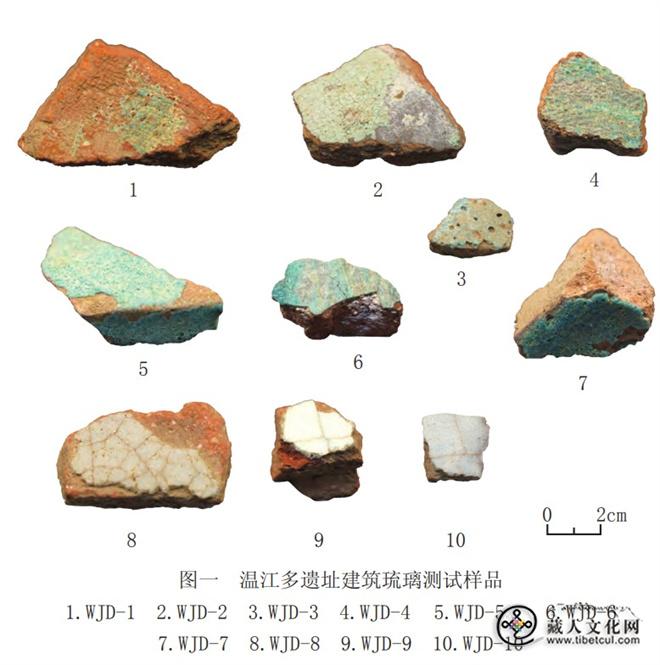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2008年至2012年间,笔者录音、搜集昂仁艺人讲唱的12部《格萨尔》史诗,并进行文字记录、补充修订、整理和统稿。工作采取的方法和实施的原则,除了遵照我国民间文学研究界提出的“忠实记录、科学整理”等基本原则外,还主要借鉴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大学、西藏社会科学院和青海《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录音、记录、整理和出版当代著名《格萨尔》讲唱艺人扎巴、桑珠及才让旺堆等的经验与教训,同时也汲取了国内外相关史诗理论的成果。在此基础上,通过实际工作还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方法。整理过程须坚持三项基本原则:严格遵守不轻易改动“原始文本”的原则;尊重艺人个性创作的风格特点;尊重史诗大传统与区域传承特点。
关键词:《格萨尔》;昂仁艺人;文本制作
小引
史诗艺人①昂仁(ngag dbang rig vdzin,1939—2012),音译为“昂旺仁增”,意为语自在持明,简称昂仁,也有人音译为“昂日”“俄合日”等,出生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柯曲乡德尔文村(部落)。德尔文部落因代代信仰格萨尔大王并盛传其“光辉业绩”(史诗),现已被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为“《格萨尔》史诗村”(2006)。1991年,昂仁被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格萨尔》说唱家”称号②。但按照传统《格萨尔》史诗艺人的分类方法,昂仁隶属于托梦神授艺人③。他自称能够讲唱94部或130部《格萨尔》史诗④,是当代伟大的创编《格萨尔》史诗艺人之一。
自2008年直至2012年昂仁艺人去世,笔者曾跟踪调查、录音和搜集了其讲唱的12部《格萨尔》史诗,即:(1)《董氏族根本预言》(ma cig rdo rje g.yu sgron gyis phab pavi ldong gi ma yig lung bstan,片段);(2)《噶岭之战》(vgag gling g.yul vgyed);(3)《英雄诞生》(vkhrungs gling me tog skyed tsal);(4)《羌岭之战》(spyi dpon rong tsa khra rgan gyis byang ri shivi thog thub rgyalpo phab pavi rnam thar ral grivi phreng ba);(5)《赛马称王》(rta rgyugs rgyal vjog);(6)《世界公祭》(vdzam gling spyi bsang);(7)《戎岭之战》(rong gling g. yul vgyed);(8)《霍岭大战》(hor gling g. yul vgyed stag movi rngam sgra);(9)《征服霍尔黑帐王》(stod hor gur nag rgyal po cham la phab pavi skor nyung ngu brjod pa,片段);(10)《辛丹内讧》(gling ge sar rgyal povi rnam thar las shan vdan nang vkhrug stag seng kha sprod);(11)《陀岭之战》(thog gling g. yul vgyed dgra lha dgyes pavi dgav ston);(12)《安定三界》(khams gsum bde bko)。随后6年间(2012—2018),笔者与其他几位学者对其讲唱的《格萨尔》史诗进行了文字记录、补充修订、整理、统稿和出版等工作。在此,笔者就其史诗文本“制作”过程中的记录和整理原则、方法等问题,谈一点看法,以求方家批评指正。
一、史诗文本成立的理论前提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部《格萨尔》史诗是怎样形成的呢?尤其是将一位艺人的讲唱录音记录成文字,再经过补充修订和整理,乃至统稿校订而成为“完整文本”出版发行,期间要经历怎样艰辛的工作过程?这当然是作为一名研究者面对材料的真实可靠性时,必须要深入探讨和了解的基础性工作。同时,这也是一般读者被远古史诗的语言和故事魅力所吸引,而对史诗形成过程及其讲唱艺人的神秘性充满神往、好奇之处。
那么,一部文字化的《格萨尔》史诗的真实制作过程是怎样的呢?笔者结合前人探索的经验和此次“昂仁本”的制作过程,就此问题尝试做出解释和说明。关于传统长条手抄本的制作程序,据说非常费时费力。据丹玛·江永慈诚先生告知:首先要有能“左腿缝纫、右腿写字”⑤的文字记录者,其次还要有深通文法的文字润色和修订者,再次是字体漂亮的缮写者,然后是技艺精湛的雕刻者和印刷者,等等。乃至最后阶段的印刷、装帧工作,据说也是十分考究。为防止书籍日后不被虫蛀,纸张方面除选用含有微毒的藏纸外,其边角涂抹材料的制作也特别讲究:需要专门设立干净的草场喂养特别颜色(赭色)的牛群,用它们清洁的粪便伴以朱砂等药物做成等。由于本文主要介绍当代艺人本的形成过程,这里就此问题不做赘述。
关于怎样记录、整理史诗以及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特别是其中的“忠实性、科学性”等原则问题,国内外民间文学研究界曾发生过激烈而持久的争论。其结果是:争论双方并没有达成最终均能接受的共识原则,而是依旧沿着各自的轨道前行(特别是国内的争论)⑥。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它成为民间文学研究界乃至一般读者的“共识”,即民间文学的记录与整理中存在“忠实性和科学性”等原则。就《格萨尔》史诗来讲,除20世纪以前制作出的传统长条手抄本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录音、笔录(文字记录)和整理艺人讲唱的工作中,关于“忠实记录和科学整理”等方面的问题,也经历了比较繁杂的实际操作和实践验证这一“特别的制作”过程。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西藏大学录音、笔录和整理出版的扎巴艺人本⑦,西藏社会科学院录音、笔录和整理出版的桑珠艺人本⑧,以及青海《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录音、笔录和整理出版的才让旺堆艺人本⑨中,可以充分见证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耗费的大量时日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并且从中也可见到非常丰富而宝贵的经验与教训。事实上,这项工作的结果甚至也影响到了当今《格萨尔》艺人们的“名气”。现在看来,过去原本并不看好的桑珠艺人,由于其著作出版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引起的社会反响,使得他已经成为当今《格萨尔》艺人中的翘楚。当然,这其中自然包括了其史诗的录音、笔录和整理者们所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即便如此,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准确地评估当今所有艺人们讲唱的成就。但是,这些众多艺人文本的出现,却为我们今后“精校”⑩《格萨尔》史诗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资料。
现在,我们搜集、录音、笔录和整理而成的昂仁艺人讲唱本《格萨尔》,也是当代诸多艺人讲唱本中的一种。我们也希望它能够丰富《格萨尔》史诗这座巨大宝库,为读者提供精美的艺术享受,为今后的“精校”工作添砖加瓦。看到希腊和印度拥有历经千年浓缩精华、精校而成的各自史诗经典文本,希望篇幅浩繁的《格萨尔》史诗系列⑪,通过浓缩精华、精校而成为一颗闪耀于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
在汲取前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制作文本的工作主要采用了以下步骤:(1)搜集与录音;(2)文字记录;(3)补充修订;(4)整理;(5)统稿。以上这些工作阶段,从西藏大学、西藏社会科学院和青海《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在记录艺人讲唱的工作中,同样可以见到例证。尤其是前两个单位,还总结出了各自的理论、方法,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与指导。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设定的以上步骤和采取的方法,完全吸收了他们的经验,特别是负责“桑珠本”记录和整理工作的西藏社会科学院金果·次仁平措研究员在其著作⑫中总结的关于制作“桑珠本”的经验与理论。他的总结可以转化为实际操作的行动指南,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同时,我们也积极汲取了国内外其他口头史诗相关理论的成果。
二、搜集与录音
关于搜集与录音,我们基本上采用了全面搜集和录音的原则,也即广泛搜集和尽可能全面录音其讲唱的全部《格萨尔》史诗资料与相关知识。从其60多年的讲唱生涯来看,昂仁录音和文字记录的《格萨尔》资料应该是比较可观的。但事实上,在我们开始正式录音其讲唱以前,能够搜集到的此前资料,除比较完整的文字记录稿《羌岭之战》和录音磁带《陀岭之战》外,几乎都是片段的录音、录像和文字记录,如《北方降魔》《孟岭大战》《征服霍尔黑帐王》等。据昂仁自己报告,《卡塔青白玛瑙宗》(khwa thavi mchong rdzong)、《赛马称王》等几部也有过文字记录稿,但笔者终究未能找到这些部本。除了委托他人搜集的相关资料外,昂仁新近讲唱的录音资料基本上是笔者完成的。从2008年至2012年间,笔者利用每年夏天近1个月的时间,与他同吃同住,一方面尽可能完整录音其讲唱的《格萨尔》史诗,另一方面也采用访谈乃至闲聊的方式,询问和求证其各个部本的情况乃至各位史诗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活动的地方”等相关知识,为我们接下来的补充修订和整理等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选择录音哪些部本,笔者也做了规划。除《霍岭大战》是个例外⑬,希望至少录音从史诗开头至4部降魔结束为止的完整故事。当笔者提出先从《天界篇》开始讲唱到《北方降魔》时,昂仁说没有《天界篇》这一部,只有《岭国长仲幼三部落形成史》《董氏族根本预言》《总管王祈求神子》等故事。其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还主动提出在录音《北方降魔》以前,想要讲唱一部发生在此部故事之前的《戎岭之战》。因此,《戎岭之战》是他拖着病体,比较完整讲唱的最后一部《格萨尔》史诗,这也使得我们未能录音其讲唱的《北方降魔》。由于笔者执著于昂仁介绍的其独特的《安定三界》,当昂仁已无法讲唱时,最终委托其子班玛诺布补充完成了这部故事。
三、文字记录(笔录)
秉承着处理口头文学资料的第一步“忠实记录”⑭的原则,我们对其讲唱录音的文字进行了记录(笔录)工作。首先,聘请青海《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的娘吾才让副研究员对昂仁讲唱史诗的新近录音做了全面的文字记录工作。娘吾才让曾对该中心的才让旺堆艺人讲唱《格萨尔》录音磁带做过多年的文字记录以及整理工作,他出生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安多牧区,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格萨尔》史诗吟诵艺人。同时,他也受过高等专业藏文教育,并且是一位《格萨尔》史诗的研究专家。因此,选择这样一位笔录者,笔者认为是比较理想的。本书中新近录音的《格萨尔》史诗,除《辛丹内讧》外,最初的文字记录工作均是由娘吾才让完成的。
《陀岭之战》是聘请西藏大学《格萨尔》专业研究生班的玛多杰记录完成的。他也是出生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安多牧区。从其反馈的文字记录稿可见,他也非常胜任此项工作。《辛丹内讧》是委托昂仁之子班玛诺布录音和文字记录的。他自幼出家,现为青海省果洛州甘德县龙恩寺的金刚上师(rdo rje slob dpon),从小对父亲昂仁讲唱的史诗耳濡目染,且受过深厚的寺院文化的熏陶。
此外,相关《格萨尔》史诗知识的访谈录音资料,委托青海省《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的旺姆措副研究员完成文字记录工作。她是《格萨尔》研究与翻译方面的专业人士,出身于青海省海东市循化县的安多半农半牧区,且受过高等藏文教育。
笔者对笔录者们提出的要求仅仅是:依据录音资料忠实记录文字与内容,不要增减和修改任何内容。正如钟敬文所言:“如果采录者所提供的资料,不是人民作品的原来面目,而是经过他人润色或改作过的,那么,它怎么能作为客观的科学资料呢?”⑮也即,忠实记录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础,来不得半点虚假。基于这样的理念,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最终完成了昂仁《格萨尔》录音转为文字的“原始文本”。
四、补充修订
新近的录音被记录成文字后,笔者将从果洛《格萨尔》研究中心诺尔德处搜集到的、由龙恩寺堪布宏格尔多杰活佛和喇嘛确吉两人于1987年记录的昂仁之《羌岭之战》,合并入这些资料,从而形成了昂仁讲唱《格萨尔》史诗的“全部的原始文本”。
笔者通读一遍后发现,这些文字记录资料,整体上的确具有震撼人心的故事情节结构与精巧优美乃至典雅的语言艺术魅力,从中确实透露出了一位优秀艺人倾其一生的艺术积淀与灵感源泉。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情节结构错乱、情节内容严重不足以及重复等,二是人物和部落关系颠倒错乱、前后不一致,三是字词、语句风格互不统一等情况。
这些不足,从过去扎巴艺人和桑珠艺人等记录者们的反馈来看,似乎并不仅仅是昂仁艺人所独有的,好像所有艺人全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但艺人们是绝对不会承认自己的这些“不足与错误”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美感差异”造成的。此外,也不排除与艺人在某一次讲唱中的表现与发挥水平的不理想有关。据西藏大学的丹真老师讲,他们也曾将扎巴艺人讲唱的录音磁带与记录稿对照,边放录音边念给扎巴老人听,扎巴艺人这才承认了自己的这些“不足和错误”⑯。
昂仁的“不足情况”怎么处理?其中最大的不足,当然是故事情节错乱与故事内容的严重不足。因此,笔者只好求助于昂仁之子班玛诺布。请他根据本部落中他人(包括家人)⑰聆听昂仁讲唱史诗的记忆和其他能够搜寻到的昂仁讲唱的录音、录像磁带做补充与修订。他遵循这条原则,保持着对父亲讲唱史诗的崇敬之情和对本部落《格萨尔》史诗的赤诚热情,走访了本部落聆听过并且熟记昂仁艺人讲唱《格萨尔》史诗的现代传承者,以及搜集了各种媒体单位保留的录音录像资料和本部落的录音资料,进行了补充和修订工作。笔者做出这样的补充决定,主要依据的是部落全体共享传承“同一文化”的原则与艺人一生积淀史诗知识的总和原则(或者说其“大脑文本”⑱)。我们必须承认,昂仁史诗中具有其个人特殊的天赋与积淀,但同时,他也只是其部落与时代的共同知识产物。
表1是增补与修订的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原稿中每页的计算方法是:以藏文22号字体及23行,作为划分一页的标准。其中诗行的编排方式依据笔者对《格萨尔》史诗“诗节”的理解,也即2行或3行为一诗节,并按现代诗行的排列方式做了编排(即每一诗节后空1行)。因此,这与“传统诗行”编排方法完全不同(即以双“།།”符号做诗行句尾,以单“།”符号做散句结尾)。
起初,笔者也曾听取他人的建议,试图标出补充内容的详细页码或字词片段。但对照“原始文本”与“修订文本”两版进行尝试的结果,发现这是绝不可能完成的工作。特别是《噶岭之战》《英雄诞生》《戎岭之战》补充篇幅较大的部本,除了保留故事框架和基本情节结构外,几乎做了逐字逐句的修订。此外,《安定三界》的内容,基本上可以说,是补充修订者根据昂仁讲唱、凭借记忆重述而独立完成的作品。那么,这是否还是昂仁的讲唱呢?笔者认为,不论前面篇幅较大的增补本还是重述的《安定三界》,都应该算作是昂仁的《格萨尔》史诗。原因在于:这些史诗的基本框架、情节结构和故事内容完全是昂仁讲唱的《格萨尔》史诗(即艺人“多次讲唱表演的总和”,也即是其“大脑文本”)。其中,早期的记录本《羌岭之战》,是昂仁讲唱的《格萨尔》史诗中非常难得的精品。因此,它也成为我们后来记录、补充修订和整理时所参照的样本。
五、整理
昂仁《格萨尔》整理工作的重点是调整错乱的情节结构、人物关系和字词语句。先前各地机构和个人在从事《格萨尔》史诗的整理工作过程中,曾采取过各种各样的技术与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总结前人经验,笔者认为在这项工作中,至今依然有效的是3条原则:(1)严格遵守不轻易改动“原始文本”的原则;(2)尊重艺人个性创作的风格特点;(3)尊重史诗大传统与区域传承特点。
首先,所谓“严格遵守不轻易改动‘原始文本’的原则”。这是过去笔录和整理史诗者总结出来的重要原则。尽管存在各种理解上的差异,但总体看法仍然趋于一致,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所谓的“原始文本”,是指艺人在独特场合的“一次表演”或“特指的歌”(the song)⑲的录音记录。而对其再做进一步整理、修订和统稿等工作时,不论从文字方面还是故事内容方面,必须严格遵照此原始录音以及记录而成的文字内容,不做轻易删改,因为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石。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于原始文本绝不能做点滴修改。事实上,作为在“一次高度压力和紧张状态下”的创编表演,其中同样存在各种错误。这就需要运用其他“原则”来做补充和校正。
其次,“尊重艺人个性创作的风格特点”。这是具体艺人所呈现的风格特色。他凭借记忆与灵感进行创编史诗,整理时不应该因为与传统内容完全不符而做删改。同时,这里也包含了艺人在不同场合的多次讲唱内容,以及从其最初开始“拙劣”讲唱到逐渐趋向成熟的“演述中的再创编”( recomposition-inperformance)⑳的综合内容。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照顾到该史诗的传统内容与风格,也要保留艺人的个人创编特色。艺人表现出的这些特殊风格,体现在其故事内容和语词特点等方面。但是,如果与“史诗的传统内容和风格”相去甚远,也就不得不做出修改和解释说明。不过,这种情况(即“背离”和“背叛”传统的情况),对于成长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特别注意“因袭传统”的昂仁来说,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最后,“尊重史诗大传统与区域传承特点”。史诗大传统是整个藏区经历千年传承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因此违背这些内容的方面,应该当作“错误”予以修改并做出修改说明。但与此同时,在某个区域内,共同遵守着一些“区域性的小传统”,这些小传统并不一定被其他区域所认同。同时,该区域内的民众也并不认同其他区域的史诗传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各自秉承的传承源头有所不同。因此,不应该将这些“区域传承特点”作为错误进行修改,而应该予以保留并加以说明。
依据这些基本原则,笔者委托娘吾才让这位熟悉《格萨尔》史诗的学者进行了具体的整理工作。从其反馈的“整理文本”来看,他的确依照这些原则做了整理。难能可贵的是,他严格遵守了第一条原则,即非常重视“不轻易改动‘原始文本’的原则”。这体现了他作为研究者所具有的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科学精神,坚持了保留“原来的真和美”的“科学性”㉑。
六、统稿
统稿工作是综合、整体地修订“整理文本”,包括情节结构、故事内容、人物关系和文字语句等方面的错乱颠倒,使其完整、统一和顺畅。这项工作由笔者本人承担。
首先,从《格萨尔》史诗的一般规律出发,协调昂仁《格萨尔》中前后不一致的矛盾。比如格萨尔兄弟三人之间的长幼关系,一般抄本与艺人讲唱中认为最长者是嘉擦,其次是戎擦玛莱,最幼者是觉如,但昂仁讲唱本中嘉擦与戎擦的长幼关系经常互换,并不确定。这里遵循一般说法,固定了下来(这种固定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按照昂仁讲法,一说戎擦死于《噶岭之战》,又说与嘉擦一道死于《霍岭大战》,后一种说法更接近于传统抄本中的观点。不过,也有不少抄本认为戎擦为最幼者,等等)。另外,一些特殊词汇,如ger mdzod(音为“格佐”,念神之主格佐)、yag la ser po(音为“雅拉赛布”,霍尔部落神山或霍岭两部落的分界山)、mkhar bzav chos sgron(音为“卡尔萨曲珍”,霍尔国铁匠部落名为曲珍之公主)、gdong vbum pa(音为“董本巴”,董氏族之本巴部落)、gdang ma(音为“党玛”,战功)、rma rgyal sbom ra(音为“玛杰邦热”,玛域或黄河流域神山之主)等,基本上按目前比较公认的写法修改成了ger vdzo,g.yag la ser po,mgar bzav chos sgron,ldong vbum pa,rdang ma,rma rgyal spom ra等。尤其是rma rgyal sbom ra一词,由于在传统的祭颂文中两种写法并存,而且近现代以来安多地区作家和学者的著作中也较多采用了此词,因此很难作出选择。但此次笔者征询多位学者,依据《藏汉大辞典》(1985)与《毛兰木大辞典》(2018)的拼写法,采用和修改为了rma rgyal spom ra这一比较通用的正字。
其次,保留古语、方言和尚不能确定的语词与说法。古语、方言是一种语言的活力表现所在,同时也是体现区域传承特点的表征。因此,有必要予以保留。比如表示动物粪便的ong ba(牛粪)、ril(马、驴、羊粪)等。有些方言使用的区域范围更小,比如昂仁史诗中的spu gri(毛锋)和mtshes spen(踵毛);把握和理解它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方面得到了当地《格萨尔》学者如措吉多杰先生等人的帮助解释。尽管如此,我们也予以保留。但是,过分执著于方言,就有碍于区域之间的沟通理解。比如安多方言中将主词之后缀pa、po二音,经常弱化变成ba、bo二音等问题,这里根据《新编藏文字典》(修订版,2015)、《藏汉大辞典》和《毛兰木大辞典》修改为了书面通用语pa和po,同时,动词时态的变化出现多种差异时,也主要依据后两部词典做了正字法处理。但有些表达如khyos(即khyod kyis的缩写)在诗行中出现时,虽然此词属于口语(尤其安多口语中较常见),但考虑到诗歌音节数量的限制,也未做修改。而且此词在《毛兰木大辞典》中也给出了上述含义的解释,因此估计大多读者能够明白其意。此外,有些故事情节虽在进行补充与整理工作时,依据不违背“史诗大传统”的原则,补充者和整理者将其做了修改。但考虑到尊重“原始文本”和“艺人个性创作的风格特征”原则,统稿时笔者依旧还原了这些内容。比如觉如(格萨尔幼名)名称的来历,“原始文本”中讲:觉如出生后,其兄长嘉擦前来道贺,看到其双手合十高昂着头颅的姿态,故取名为“觉如”(其意为头颅高昂者)。也即对于觉如这一重要名字的来历,昂仁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再次,《噶岭之战》中格萨尔母亲部落的姓氏vgag(音为“噶”)字,目前学界主张使用vgog(音为“果”)字。笔者请教果洛当地学者和艺人如格日尖参等,他们一律主张采用前者。按照格日尖参的说法,这两字没有差别,仅仅在于后者是前者的康区发音变化而导致的。也就是说,前者要早于后者,这种观点笔者本人也接受。从多种《格萨尔》艺人本与抄本来看,“噶部落”或“果部落”原本位于岭部落的上方(即西方或北方),且是岭部落的上级主管部落(如桑珠本中的说法),即岭部落在未发迹前也仅仅是噶部落所管辖的一个小小部落而已。这里依据录音记录的“原始文本”将“补充和整理本”做了还原修改。
最后,一些无法确定的说法,尽管存在矛盾或不统一,但都做了原样保留。比如格萨尔在天界的名称有3种说法:lha phrug dam pa tog dkar(神子丹巴多嘎)、lha phrug mon chung dkar po(神子孟琼嘎布)、lha phrug tos pa dga’(神子推巴嘎)。这3种说法,实际上是《格萨尔》史诗传承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时代和地区差异。另外,格萨尔的神马也有3种写法:lha rta rkyang rgod gyer ba(神马江果耶瓦)、lha rta rkyang rgod ‘pher po(神马江果派布)、lha rta rkyang rgod gyer po(神马江果耶布)。这3种写法,也存在方言变音的可能,还表现出安多地区与康区传承史诗的差异。此外,文中还存在dgra lha(战神)与dgrabla(战魂)、ga dar phying sngon(嘎达尔·秦恩)与ga dur phying sngon(嘎杜尔·秦恩)以及gling dkar lha ru tsho drug(岭六大部落)与gling dkar lha ru tsho brgyad(岭八大部落)等内容相近的几种写法并列的情况。这里有古词与新词、苯教与佛教文化、地名或部落名称以及部落联盟数量等方面的种种差异。尽管当下也逐渐趋向一致与固定,如dgra lha(战神)、ga dar phying sngon(嘎达尔·秦恩)和gling dkar lha ru tsho drug(岭六大部落)等。但笔者以为,目前尚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因此也做了原样保留。
小结
在录音、文字记录和整理昂仁史诗的过程中,令笔者感到惊异的是,他对《格萨尔》史诗所持有的“传统的”和“独特的”分类法和认识观念。比如,他对其讲唱的《格萨尔》史诗的故事系统有以下分类方法:(1)4部降魔、18大宗和47小宗(2008年);(2)4部降魔、18大宗和21小宗(2009年);(3)4部降魔、18大宗、25小宗和47外宗(2010年以来)。最终,可归结为94部,即:4(降魔)+18(大宗)+25(小宗)+47(外宗)=94部。事实上,其中除了“4部降魔”与“18大宗”两个部分的内容比较固定以外,其余的25小宗和47外宗,在他本人心里直至去世前,依旧是模糊的,甚至有时候能确定下来的也只有4部降魔。但有时说得兴起,他甚至告诉笔者,他能够讲唱130部史诗。这种计算方法实际上是将其“开篇部分”的《英雄诞生》《赛马称王》和“结尾部分”的《地狱救妻》《安定三界》等篇章,做了其“故事系统”外的单独处理。这也可从早期保存于果洛州《格萨尔》抢救办公室的记录中得到印证。
此外,他将史诗看作是格萨尔大王一生的“光辉业绩”,这也是其“传统和独特的”认识。他认为格萨尔大王从天界降临到人间的目的有3个:首先是驱除人间的黑暗,给岭国人民带来幸福吉祥,把全世界的财富、享用和福祉全部收归到岭国(王的角色);其次是征服愚昧无知或相信外道的人,引领其走上佛法正道、使全世界的民众过上幸福吉祥的生活(佛菩萨的角色);最后,昂仁的史诗系统中还含有未来世的观念,即在未来世格萨尔大王以第25代香巴拉勇武转轮王的名义再次出世,带领勇士们降伏外道,拯救黎民(佛王、法王的角色)㉒。因此,昂仁讲唱的《格萨尔》是格萨尔自天界降临到人间,在其人寿88年间,他与他的80位勇士所做出的英雄业绩,最后在88岁(一说为85岁)时返回天界,进入了六波罗蜜多(也有说进入炽燃火山)境界。由此可见,昂仁的《格萨尔》史诗可以归入“降魔除妖”(佛菩萨)与“来世救难”(香巴拉王)的故事范型。另外,他还将史诗中的“四魔王”理解为人类的“烦恼四毒”(愚痴、贪欲、嫉妒、我慢)的代表,以及他不承认《地狱救母》为史诗结尾,而只承认包括5个讲述佛法小宗的《安定三界》为史诗结束,等等,诸多观点是他对《格萨尔》史诗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里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总之,笔者调研昂仁艺人时发现,作为20世纪上半叶出生、成长起来的优秀史诗艺人,其史诗传承体系中不仅继承了安多本地区的史诗传统,同时也包括了整个藏区《格萨尔》史诗的内容,特别是经过色达、石渠传承而来的康区的史诗故事。当然,除了这些明显的特征,我们不能否认,其中也蕴含着昂仁自己创作的心血。比如其《安定三界》中提到的独特内容,至今尚没有在其他艺人的讲唱或文字记录中出现过。因此,笔者将其史诗传承体系列入了“上安多地区型”㉓。同时,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从其讲唱中呈现出的故事情节的过分“衰减、遗漏”和诗行的“过分简练”中,不得不承认其史诗讲唱已经呈现出遗忘和衰落的“特色”与趋势。
上述“制作文本”的过程是否合理,尚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令我们自信的一点是,秉持着对其认真负责的态度,尝试完成了昂仁本的制作工作。在此,真诚地期待广大《格萨尔》史诗研究者与爱好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的修改建议和意见。
注释:
①史诗艺人,藏文为为sgrung ba/sgrung mkhan(讲唱历史传说或故事的人),此词与法语Barde(游吟诗人)比较接近。本文中我们采用此含义,有时简称为“艺人”。
②赵秉理.格萨尔学集成:第四卷[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2340.
③关于《格萨尔》史诗讲唱艺人的类型,依据艺人们自己的传统观念,过去学者们(如东嘎·罗桑赤列、杨恩洪、降边嘉措等)总结为“神授(babs sgrun,巴仲)、掘藏[sgrung gter or gter sgrung,仲德尔(艺人自称)或德尔仲(学者称呼)]、圆光(pra sgrung,扎仲)、闻知和吟诵(thos sgrung and vdon sgrung,退仲和顿仲)”等几大类。近年又新增加一类,称作“多巴念夏(rtogs pa nyams shar,此词借自佛教术语)”,属于“神授”类别,有人译为“顿悟艺人”。实际上,相对于同样隶属于“神授”类别之一的“降神(神附身)艺人(babs sgrung,巴仲)”具有的现场降神特点来看,此类艺人更加强调通过梦境获得史诗故事的显著特点。因此,笔者认为译为“托梦神授”较妥。总之,从一般学理角度来讲,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史诗艺人,实际上只有两类:创编能力较强型艺人和创编能力较弱型艺人。藏族《格萨尔》史诗传统艺人分类中,除了称为“吟诵”类型的艺人的创编能力较弱以外(但著名吟诵艺人尕藏智华虽然依照抄本讲唱,却也表现出了较强的创编能力,比对手抄本和他讲唱的《大食财宗》就会发现,他刻意追求将书面语和古词修改为方言口语等通俗化的特点。当然,此类艺人尚有其独特的功绩,比如纯熟的讲唱技巧、优美的嗓音和多样的曲调变化等),其他均属于前者。
④关于昂仁讲唱《格萨尔》史诗的总目,参见:李连荣.祖先之歌—纪念《格萨尔》史诗著名说唱艺人昂仁[J].青海湖,2015(12):63-64.
⑤这种说法是指传统社会中对牧区“男人角色”的设定。
⑥国内就此问题的争论,从刘魁立先生的著作中可见一斑。(参见:刘魁立.民俗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57-183.)国外的讨论,更是由来已久,比如对格林兄弟记录民间文学方法的质疑,等等。(参见:朱泽佩·柯基雅拉.欧洲民俗学史[M].魏庆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91-193.)
⑦西藏大学自1979年开始了著名神授艺人扎巴(1906—1986)讲唱《格萨尔》史诗的录音、文字记录和整理工作,共计录音25部。参见:李连荣.格萨尔学刍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116,224-229;其美多吉.扎巴艺人及其《格萨尔》说唱本研究[M].藏文版.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20:44-51.
⑧西藏社会科学院抢救录音著名神授艺人桑珠(1922—2011)始于1984年,但作为专题项目,进行文字记录、重新录音、整理和出版等工作则开始于2000年,2016年完成,共编辑出版了45部(48册)。参见:金果·次仁平措.《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研究[M].藏文版.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3:10-15.
⑨青海《格萨尔》保护研究中心自1987年开始对神授艺人才让旺堆(1933—2014)讲唱的《格萨尔》史诗进行录音、文字记录、整理和出版工作。参见:恰噶·觉如.《格萨尔》艺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让旺堆逝世[EB/OL].(2014-05-30)[2023-01-16].http://news.tibetcul.com/wh/201405/33271.html.
⑩“精校”或者“精校本”史诗,正是我们目前所见印度两大史诗和希腊《荷马史诗》的形态。关于“精校”史诗的工作特点,通过苏克坦卡尔《关于〈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工作进展的报告》可见一斑。(参见:黄宝生.《摩诃婆罗多》导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49-156.)相比这些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史诗作品,尽管《格萨尔》史诗其中的某些篇章如《霍岭大战》等比较“成熟”以外,整体上还处于一种“反复创编与完善过程中的”“雏形形态”阶段,有待更进一步的“精校”工作。
⑪《格萨尔》史诗系列,这里指《格萨尔》史诗的各种篇章的总和。过去国外学者霍夫曼等称其为“thecycleoftheGe-sarepic”。(参见:HelmutHuffuman,StanleyFrye,ThubtenNorbu,Ho-chinYang.Tibet:AHandbook[C].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ublications,1975:195.)此词意等同于纳吉等学者对“荷马史诗系列”的称呼,即“cycle”(归属于荷马名下的所有“英雄诗系”)。参见: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M].巴莫曲布嫫,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9-50.
⑫金果·次仁平措.《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研究[M].藏文版.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3:22-65.
⑬笔者最初的动机仅仅是期望通过录音、笔录(文字记录)其《霍岭大战》,进行与其他文本之间的比较研究。因据昂仁介绍,其《霍岭大战》不同于现有抄本,最具特色。(参见:杨恩洪.人在旅途—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说唱艺人寻访散记[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125.)因此,该文本是最先录音完成的。随后几年,考虑到其史诗的独特性及重要性,笔者才决定抢救录音其主要部本。
⑭关于“忠实记录”原则的理解,各家自有不同的解释,这里采用钟敬文先生的观点:“必须是按照民众的口头讲述忠实地录下来,并且不加改变地提供出去(当然,它也必须经过一定的科学方法的整理过程)。即使原讲述中有形式残缺或含有显然错误的内容等,也不要随便加以删除或改动。”参见:钟敬文.新的驿程[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14.
⑮钟敬文.新的驿程[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13.
⑯李连荣.格萨尔学刍论[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140.
⑰昂仁子女中有两位优秀艺人:儿子昂青扎西(dbang chen bkra shes,1970-2016)是托梦神授艺人,普通牧民,不识字,可惜英年早逝,只留下了一部史诗《征北大战之铁神剑》(甘肃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幼女才忠(tses gron)是闻知艺人,普通牧民,不识字,因其嗓音甜美、曲调悠扬深受民众喜爱。除此,在德尔文部落,昂仁同辈中出现了众多艺人,如其弟弟喇嘛乌洛(bla ma bu lo)和堂表兄弟德华(bde dpal)、巴才(pad tse)、喇嘛南卡(bla ma nam mkha)、东宝(do po)、班桑(padma bzang po)等;其晚辈中出现了全国闻名的掘藏艺人格日尖参(gu ru rgyal mtsan,1967—2019),撰写出版有近30部《格萨尔》史诗。此外,尚有洛桑沃赛(blo bzang vod zer,1963-2018)、东尼曲珍(stong nyid chos sgron,女艺人)、嘉央喜饶(vjam dbyangs shes rab)等众多艺人也均出版有《格萨尔》史诗。
⑱劳里·航柯,刘先福,尹虎彬.作为表演的卡勒瓦拉[J].民族文学研究,2015(1):45-55.
⑲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M].尹虎彬,译.北京:中华书局,2004:145.
⑳格雷戈里·纳吉.荷马诸问题[M].巴莫曲布嫫,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2.
㉑尽管这个观点是钟敬文先生在讨论记录民间文学的“科学性”时提出的,笔者意为这同样适合于史诗的“补充修订和整理”工作。参见:钟敬文.新的驿程[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22.
㉒佛王或法王角色以及重返人间的观念,估计来自11世纪后传入藏区的“香巴拉”思想。后来由于受到六世班禅(1738—1780)等人的主张与弘扬,《格萨尔》史诗中的这一观念在藏区具有广泛影响。早在20世纪30年代,调查该史诗的达维-妮尔(A.David-neer)也从雍和宫的蒙古僧人中听到了这种说法。由此也可见到该观念传播之广泛。参见:A.大卫·尼尔.岭超人格萨尔王传[Z].内部资料.陈宗祥,译.杨元芳,校.成都:西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1984:22-23.
㉓李连荣.安多地区《格萨尔》史诗传承的类型特点[J].西藏研究,2015(5):95-102.
作者简介:李连荣,藏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民间文学。
原刊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3 年第 3 期(责编:蒲宏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