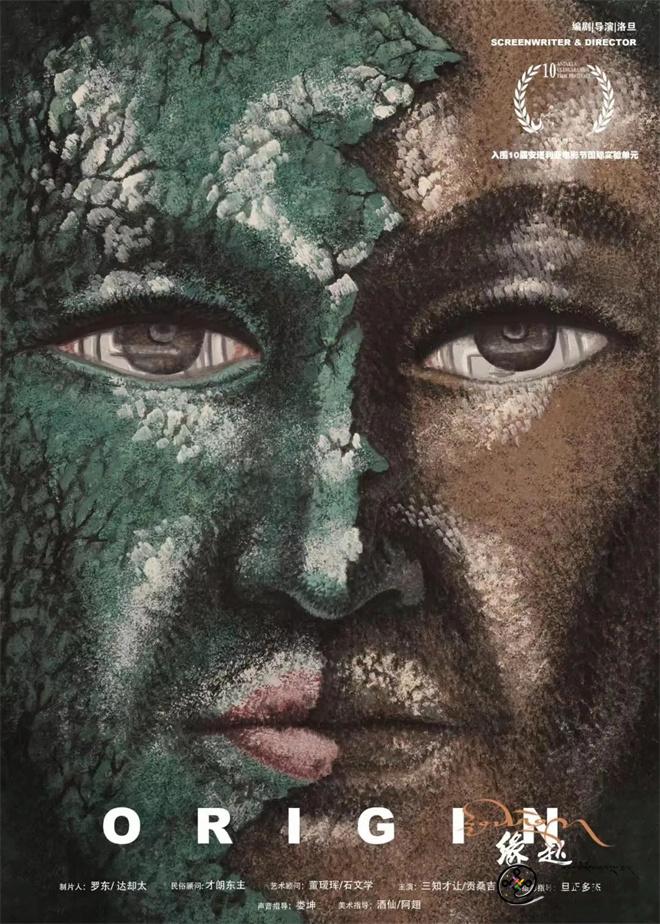小说与电影
崔:你在拍电影之前写过多年的小说。在那本体现藏族作家成就的文集《智者的沉默》里,我看了你的三篇小说《人与狗》、《流浪歌手的梦》、《诱惑》,这三篇东西中有一些贯穿始终的精神。关于狗的那篇,表达了狗深深的孤独,不被理解反而被误会;关于歌手的那篇,眼看歌手就要与他朝思暮想的女孩子牵手,但是瞬息之间这一切都不复存在;关于经书的那篇,经书始终没有到手,仿佛到手的东西都要跌碎似的,其中有一种对于尽善尽美的东西的不可触及的忧伤,感到有一些东西是难以企及的。这些反复出现的某种情绪,是你现实生活中挫伤的反应呢,还是更加接近一种精神生活? 万玛:我觉得还是跟我的经历有关吧。这个电影可能跟我的生活经历有关,刚才您说的那几个小说可能跟我的内心经历有关,我觉得是这样的。
崔:你倒是分得很清楚,外部的生活经历与内心的体验!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或者心情算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吗? 万玛:从内心的角度讲,应该是这样吧。我觉得我的心底有一种莫名的悲观,一种非常悲观的情绪。当时写作的时候不是很自觉,回头看,有一种很悲观的情绪在贯穿始终吧。无论是藏文的作品还是汉文的,而且我发现我的作品中的时间和背景都比较统一。一般故事都会发生在冬天,环境比较悲凉。有一次见到对史铁生的一段采访,那里面一句话我觉得可能比较接近我的这种心态,这句话是:人注定的孤独和理想的最终不可实现。
崔:你比较喜欢哪些文学家? 万玛:呵呵……很多,比如卡夫卡、陀斯妥耶夫斯基、马尔克斯、海明威、福克纳等等。
崔: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内在冲突很强的一个…… 万玛:对,比较喜欢他。
崔:诗歌方面喜欢谁呢? 万玛:中国诗坛代表性的几个诗人都比较喜欢吧。海子啊什么的,青海那边有一个诗人叫昌耀,我也很喜欢。
崔:你也用藏语写作?写小说? 万玛:对。藏区有一些藏文的文学期刊,我给他们写,除了写小说,还要做很多的文学翻译工作,有时候把藏文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文的,有时候把汉文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藏文的。
崔:你的藏语小说和你的汉语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万玛:主要是题材上不一样,针对不同的读者群吧。比如有一些藏语的小说吧,它可能对藏语读者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可能那种意义在汉语读者那里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类小说我一般不会同时用双语写。但比如《诱惑》啊,《人与狗》啊,我觉得任何读者都可以看吧。
崔:你是说你的藏语小说可能更加接近现实? 万玛:对,可能更现实一些,对现实的思考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对藏语言文字现状的一些思考,这可能是每一个藏族学者经常会想到的很实际的问题。但是你把这类小说翻译出来,其他读者可能就不会有强烈的感受。它们是那种时代性比较强的东西,过了那个时期可能就不会有价值了。
崔:一般所说的“介入性”,是吗? 万玛:对,对现实现状的一种介入。藏文的一些文学期刊它会要求你写一些比较关注现实的东西。
崔:哦,我们无缘拜读你的这些藏语小说了。那你说你拍的这部电影,是接近你的藏语小说还是汉语小说呢? 万玛:应该是接近藏语小说吧,因为涉及到的是藏区当下的一些现实。 崔:这样说就能说通了,因为看你的汉语小说与看你的电影觉得相差挺大的。小说写得激情、浪漫,而电影写实、克制。你认为你的电影与小说这两种手段运用起来有什么不同?万玛:骨子里有一种东西应该是一致的,但在呈现方式上可能就有些不一样了。写小说显得比较自由,比较方便,但电影可能会受到很多物质条件的限制。我很希望像写小说那样来拍一部自己喜欢的电影。
崔:习惯了文学自由的表达,转入电影会感到受限制比较大? 万玛:我觉得电影不是一个特别自由的表达方式,但是它有它的优势,而文学给了我们特别丰富、特别自由的表达空间。
崔:藏族文学的传统是属于那种想象力特别丰富的? 万玛:对,它里面包含着非常奇特的、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对那种非写实的东西的描绘非常精彩,反之一些写实的描写往往就显得比较苍白。
崔:那你感到做电影较少得到藏族文化传统的支持? 万玛:做电影也吸收了许多藏文化的养分,但写小说可能会更接近一些吧,藏文化中较少写实主义的传统。
崔:电影可能是不是也是另外的一种想象力? 万玛:电影与文学一样,想象力很重要。但电影往往将想象力具体化,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想象力。文学你怎么努力地描写也不可能把描写对象复原成为一个实物吧,这样对读者就有了一个想象的空间,想象的余地。
崔:对你来说,两种媒体是不是各有分工呢?就像藏语写作与汉语写作的分工那样? 万玛:不能说是分工吧,小说更个人化一些,而电影里面肯定也有个人化的东西,但在呈现上可能会更现实一些。
崔:那么是否可以说,你拍电影,首先想要过藏族这一关,得到他们的认可?是吧? 万玛:呵呵,这是我的一个底线,如果自己民族的人都不认可,就有违于我的初衷。
崔:那些电影导演对你影响比较大呢?或者你喜欢谁呢? 万玛:有很多导演,但是对我做电影直接有影响的是伊朗电影。没到电影学院之前我基本上没有接触过任何伊朗电影。看了几部伊朗电影之后,改变了我原先对伊斯兰世界的一些看法,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充满了一种令人心生感激的东西,这些是和我的家乡很相似的,另外在很多地方给了我很多的启示。
剧本、演员与摄影
崔:你小说的功底在你完成这部电影上面,立下了大功劳,首先是有真情实感,有话要说,而不是胡编乱造。但是在看到差不多一半时,心里也会有疑虑:全都是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好像互相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似的,直到小喇嘛要带电视机与VCD进寺庙,才出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叙事冲突。你是怎么考虑的? 万玛:这个片子里面我刻意地淡化了那种表面的冲突,但它还是有那种内部的张力和内部的冲突的。每个情节点看起来比较散漫,但是经过了精心的构思的。在那些日常的、琐碎的描述底下,蕴涵了藏文化的许多本质的东西,比如藏族人对生命、对死亡的基本的看法。比如里面有一句台词:“生命像风中的残烛,财富如草尖的露珠。”就是藏人对于生命无常的一个基本的表述。比如山上刻石老人的去世和村里一个小孩的出世,这其中就有一种轮回的观念在里面,虽然在影片的叙事时间上是倒着的,但在实际时间上却是顺着的。所以,从整体上看,我觉得有一种贯穿始终的东西在里面。
崔:呵呵,这个我们还真不敏感,看不出来,也许你的藏族同胞一望即知。当然,能够感受到的是,在那种表面上的单纯背后,有一种来自传统文化精神的深沉律动,每一个人物即使从外部形态上看上去,也都挺沉,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从内部拽住他们的感觉,尽管外部世界已经开始触动这块未经触动的土地。 万玛:其实他们都是在很自然的状态下生活着,那种挺沉的感觉可能更多地来自于自身之外的一些东西。
崔:令人感兴趣的是,你的剧中人物基本上都是真实身份,小喇嘛便是小喇嘛、老喇嘛便是老喇嘛、小活佛便是小活佛。寺庙允许他们来拍电影吗? 万玛:寺庙在这方面的管理是挺严的,一般是不让拍电影什么的,我们是认识那个寺院的活佛,跟他讲了这部电影的重要性啊等等,呵呵!
崔:你们怎么说的?怎么讲这部电影的重要性? 万玛:就说这是一部纯藏语的电影等等,这是别人去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最后他同意了。
崔:你的演员看过你的剧本没有? 万玛:没有。因为剧本是汉文写的嘛,他们好多人看不懂。
崔:那你有没有把这个电影的故事从头到尾给他们讲? 万玛:也没有,但是对白被翻译成了非常口语化的藏语,把每个人的用红笔标出来,发给了他们。
崔:比较我们看到的汉语字幕,再翻译成藏语有没有大的改动啊?因为你说过,在短片《草原》里,两个村长之间说的许多藏话都没有翻出来,汉语字幕比较简单。而在将汉语剧本回过去弄成藏语时,是不是做了一些修改? 万玛:《静静的嘛呢石》的对白在汉语和藏语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出入,而《草原》的对白可能就是一种简单的表意的翻译,因为它里面用到的谚语特别多,直接翻出来可能在表达方式上有一些问题,所以就用了意译的方法。
崔:那你的演员有没有改动你写的台词啊? 万玛:有,每个藏区,小到每个村庄之间说话的方式都会不一样。比如一句台词不太适合我所描述的那个地区的表述方式,我就会听取当地演员的建议做一些调整,但是表达的意思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