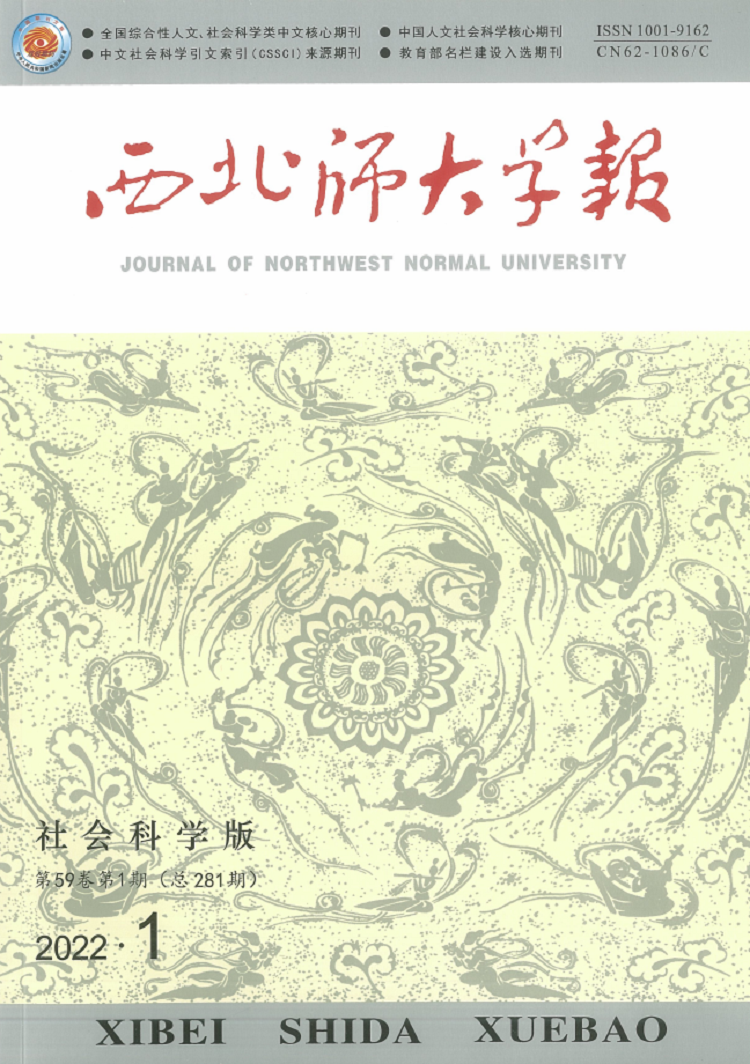
【摘 要】卍字符是一个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中广泛存在的图像符号,也是佛教的瑞相符号,表吉祥、光明之意。以卍字符历史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即远古时期的象征符号,佛教融合发展期的宗教符号,以及泛世俗化时期的装饰符号为节点,探讨其在不同时期美学意蕴的发展流变,分析其世界性、本土性特征中的人类情感和生命形式,从而揭示蕴含其中的朴素之美、光明之美和世俗之美。
【关键词】卍字符;美学意蕴;朴素之美;光明之美;世俗之美
自人类诞生以来,卍字符这个神秘且被广泛应用的符号便一直伴随着各种文明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卍作为一种纹饰、一种象征符号、一个字符,广泛见于西起希腊爱琴海诸岛、埃及、小亚细亚,东到中国,北自北欧、北亚,南抵印度次大陆等地”[1],它是世界众多民族所共同拥有的符号。几千年来,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对其形式和意义的理解与阐释,表现着人类共性的思维、价值和集体意识,在中国则更彰显着华夏民族海纳百川的文化自信,研究它对人类文化史和艺术史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 、远古象征时期:神秘、朴素之美

图一 河姆渡四鸟卍字符
学界历来对卍字符的生成时间及蕴含之意观点不一,然据现有诸多溯源考证的资料来看,王克林先生对卍字符的考证较为全面和严谨,其《“卍”图像符号源流考》一文以考古学为视角,从时空分布、形式演变、渊源取象、寓意功能和族属谱系五个方面认定卍字符是来自中亚两河流域的萨玛拉文化和中亚、东亚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彩绘符号,“是距今六、七千年前,亚洲北部地区一些民族或部族所崇尚的一种宗教信仰,‘灵魂不灭’、祖先崇拜的精神文化,是人类自身‘美化’了的符号艺术图像。” [2]在我国,卍字符分布的地域很广,南方和北方地区均有出现;年代也很早,陶器时代和各民族原始文化中均有显现。据可考史料来看,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中便出现过将类似四只鸟的喙由颈部相互交织后出现的左旋卐字符,图中(图一)鸟喙两两一致呈对称分布,似尖刀一般伸向外围,表现出一种动态、神秘之感。可以说,绘制该图的原始先民在当时已经表现出了纯粹的“工匠精神”,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意识和朴素的审美观。此后,卍字符在马家窑文化(甘肃、青海,距今约5000年)、小河沿文化(内蒙,距今约4500年)、后红山文化(辽宁、内蒙,距今约5000年)、石峡文化(广东,距今约4000年)和大汶口文化(山东,距今约6500年—4500年)中均有出现,呈现出高频率、分布广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后红山文化出土的彩陶中我们可以看到,“卍”居于罐体醒目部位,反映出该符号在当时先民心中的重要地位;而在西部地区马家窑文化中出土的有卍字符的马厂型彩陶,不仅数量多,而且罐体色彩清晰,各类变形的“卍”更是显现出先民们对其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尊崇,例如,有四个前端似蛙足的“蛙足卍”、有四个前端弧形弯曲延伸旋转的“风轮卍”及四个前端似小旗子的“旗形卍”,等等。然而,无论如何,所有图案均表现出“十”字基本造型不变和对称分布的特点,有的甚至可以觉出其运动之感。
那么,这些出现在原始陶器上的卍字符之于人类究竟是何种意义的存在,它传递着原始先民怎样的思想?通过现有资料考证来看,学者们认为“卍”字符是以“十”字为基本母型,通过对“十”字的粗化、空心化、网格化及倾斜化后不断延伸并变换四个前端而组成新的图案,“少见单线十字,有空心十字,网格十字,米字十字,卍字也是由十字变化而成的”[3],这种变化充分说明了“十”与“卍”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有的学者还通过考古专家对甲骨文中“十”字与“巫”字的蕴含之意比较后发现,“巫”字所蕴含的“太阳的使者”之意与“卍”的光明之意相通,象征某种特殊的宗教力量和文化信仰。由此,笔者认为“卍”字符中蕴含着朴素的原始巫术思想,其在形式上一方面表现出对原始图腾的简化,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原始先民从内心对自然、自我的抽象化表达。
除了这些原始陶器上所绘制的卍字符,远古时期的卍字符还出现在诸如萨满教原始宗教信仰文化中,并成为其代表性符号。根据现有的考证资料来看,佛教寺院和佛身上所著或装饰的卍字符,其根源“是古代近东和我国北部地区,游牧民族所奉行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相关的精神文化在佛教文化中的一种表现……是经文化交流而产生的一种标志原始宗教的精神文化的艺术符号”[4]。这表明卍字符来源于原始宗教萨满教,它是世界各民族之间文化涵化影响的一种表现,早早便具有了“人类文化共同体”的意味。从萨满教诸多的卍字符图案结构来看,虽然“十字四面末端外卷或内折部分有变化,但却不脱离其中十字形的主体。由于符号的对称规则,这就暴露和显现了它的来源和取象,不难看出是与人体有着密切关系的图像。”[5] 王克林将萨满教岩画中骷髅崇拜“灵魂不灭”的现象与《周易•系辞》中讲述原始人在观察自然万物时“近取诸身,远取万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表述进行了对比分析,证明卍字符是史前人类对各类舞蹈人形进行综合加工抽象后的一种艺术表现,是人类自身“美化”了的艺术图像。
在藏族文化中,卍字符被称为雍仲,分卍、卐两种类型,其出现的年代久远,从空间上广泛分布于藏民族生活的高原区域之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从目前已知资料来看,藏族文化中的卍字符最早出现于史前时期的“铜石并用时代”或“早期金属时期(一般认为这一时期始于距今 3000 年前到吐蕃王朝的建立结束)”。在这之后,卍字符主要出现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和北部那曲一地的高海拔岩画当中,“高原岩画中出现较多的符号有雍仲符号‘卐’和‘卍’、树木图像、日月符号、塔图像等,这些符号单独出现于岩画,固然有其意义。”[6]“藏西岩画中的 47 个雍仲符号里,‘卐’有 34 个,‘卍’有 13 个。藏西地区的凿刻类岩画绝大部分属于前佛教文化时期的遗存,因此,这里出现的‘卍’类在雍仲符号可以说与佛教文化没有关系。”[7]据此,我们可以判断从阿里地区岩画早、中期的分期和新石器晚期彩陶纹饰的“卍”是先民们在未受到佛教文化影响之前的自发创造。
卍字符在藏族文化中的突出位置还表现在其在藏传佛教出现以前已经成为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最高标志,苯教提前认识并运用该符号,并赋予其极高的象征意义。在与苯教相关的藏文文献中,描绘“卍”时经常会出现“雍仲九叠”的某某宫殿、某某山;“雍仲禅定”;“雍仲宝座”或“雍仲台座”等词汇[8]。这些由“雍仲”词汇所表示的意境来看,主要表达“永生”“坚不可摧”和“恒常不变”等宗教涵义。旅居法国专门研究苯教的藏族学者卡尔梅·桑木旦博士认为,苯教以俄木隆仁为宇宙中心,而象征永恒的“雍仲九叠”(卍)是俄木隆仁的标志性存在,故“卍”便成为苯教的最高象征。“卍”所具有的这种“永恒”“永生”宗教意义,伴随藏族文化留传千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藏族人民的思想观念。
卍字符在远古先民心中具有绝对崇高的地位,它既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界的认知,又彰显着人类认识自我的艺术特征,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意蕴。“由于原始人在漫长的劳动过程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的秩序、规律,如节奏、秩序、韵律等熟悉、掌握、运用,使外界的合规律性和主观的合目的性达到统一,从而才产生了最早的美的形式和审美感受。”[9]原始社会时期,线条是创造一切图形的基础,先民们正是依据线条的不断组合和变化,来表达对神与自然的敬畏、对光明和美好的向往、对自然界生存法则的适应。因此,在原始人淳朴的原始思维下通过简单的行为而创作出来的这个艺术符号便具有了一种朴素、原始和神秘的美学特征。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卍字符其实就是原始人对周遭生存环境进行心理认知后的一种情感的符号表达。
因卍字符出现的地域广泛、年代久远,各民族对其赋予了不同的含义,故学者们对卍字符蕴含之意的研究也就呈现出多样的推测和理解,但主要集中于太阳崇拜、生殖崇拜和鸟类崇拜等。前文所述,卍有光明之意,而就现有的卍的各类演变图案来看,我国许多地区岩画当中所绘的象征太阳的图案因其光明和光芒四射之意从而与卍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广西花山岩画的太阳图像虽仅仅以轮廓示之,但却形成了“剪影”般的艺术效果,图像粗犷且动感活跃,有着极强的艺术感染力;内蒙阴山岩画中大量的日月星辰符号,记录了人类童年对于自然的朴素认知,反映出朴实健康的美学观和惊人的艺术才华,从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观、审美观和思维方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曾被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天书”,其上的太阳图案画风原始、线条粗率,反映着我国农业部落社会对于天体的最早的崇拜意识;云南沧源岩画中的太阳图案绘制技法简单粗率,造型稚拙古朴,是云南古代民族对于太阳光明象征的崇拜。在这众多象征太阳的图案中,考古学家发现有些圆形太阳图案中绘有“卍”字符,联系前文所述,应与太阳同表光明之意。原始先民所处的时代生产力低下,当疾病及自然灾难来临时,族群的繁衍与兴盛便成为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卍字纹是先民生殖崇拜的象征符号[10]。我们知道,世界上至今仍有一部分地区和国家有着一妻多夫的传统,美国学者O.A魏勒和国内学者刘志群先生认为该符号象征着“一妻多夫”,具有明显的生殖崇拜,卍字符的“永生”“永恒”之意和图形的运动模式传达着人类对于族群发展生生不息的希冀。
据考古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原始部族都有过动物崇拜,他们以动物或幻想中的动物为崇拜对象,来反映狩猎时期原始人群的社会意识,这种崇拜在人类长期的发展中逐渐渗透于各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例如中国的龙和凤、俄罗斯的马和熊以及印度的牛和猴等。我们通过对藏族苯教著作《黑头矮子的起源》、藏族创世歌谣《斯巴形成歌》中的大鹏金翅鸟、藏族天葬中的秃鹫、迎鸟节习俗以及阿里、林芝、巴塘等地诸多孔雀舞的研究发现,藏族对鸟有着深深的喜爱和崇敬,“鸟崇拜”是藏族独特的民族标记,塑造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增添了绚丽的民族色彩。“根据藏族古代鸟类图腾,把卍字符的竖线作为鸟身,两端朝向相反的横线作为鸟头和鸟尾,把与竖线相交的横向看做翅膀,能组合出一个鸟的简单轮廓这一现象推断,卍字符的动物原型很有可能是鸟。” [11]我们通过前述得知藏族文化中称“卍”为“雍仲”,其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简化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卍字符,大量地出现在藏族婚丧嫁娶、民居装饰及宗教仪式当中,成为民间和宗教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图案和符号。
作为一种具有原始魅力的可视图形,卍字符被人们赋予了太多的象征意义,其中太阳、生殖器、鸟类等占据主流。然而,更进一步来说,无论推测该字符为巫术思想的代表性符号或者猜测其为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文字,其都彰显着上古时期朴素、浑厚的美学风韵。英国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在其《秩序感》中认为卍字符是一种“正在运动的形式”,线条流动且不呆板,给观赏者以无穷变化之感。卍字符所具有的这种粗拙生动的图像形象,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早期人类先民对生命的赞美,对美好意愿的描述与向往,从而一种神秘稚拙、朴素的美学特征跃然眼前。
二、佛教融合发展时期:神圣、光明之美
苏珊•朗格曾提出,“符号化的需要”是人类一直进行着的一种基本需要。她说:“我相信在人身上,有一个基本的需要。这一需要很可能是其他动物所不具有的。它将激发所有明显非动物性的特性:他的富有智慧的想象力,他的关于价值的意识,他的完全非实践的热情,他的那种充满着神圣的‘来世’意识。这个基本需要——肯定只有人才有的需要——正是‘符号化的需要’。如同吃、看、运动,创造符号的活动是人的基本活动之一。这是心灵的最根本的过程,它将一直持续下去。” [12]卍字符作为一个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中广泛存在的图像符号,作为一个在佛教艺术中具有光明之意的宗教符号、艺术符号,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对其的理解和阐释,既体现了人类思维和集体意识,更体现着华夏民族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与文化自信。
两千多年前,中国与印度便开始了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而佛教的传播则居于最显著的位置。东汉初年,佛教经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中国而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成为亚洲乃至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佛教文化逐渐成为重要的思想文化之一,与其有关的佛教艺术也受到了皇家和民间的喜爱。
卍字符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隋朝及唐朝时期都是佛教重要的代表符号,广为风行。两汉之际,佛教经南方和西域两条不同的途径以自己的传播方式将佛的信息传递到了中原。东汉后期,政治腐败、战乱频仍,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渴望摆脱战争与贫困,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宁,而佛教则从心理抚慰和精神需求方面对处于战乱中的民众给予了一丝慰籍。因而,这一时期的装饰纹样,包括兽类动物纹样、人物图案及建筑装饰等都能反映出佛教的传播痕迹,如西汉用于檐头遮雨的瓦当上亦出现了卍字符,显示出其对本土文化的渗透。正是佛教对卍字符的吸纳和使用,使该符号具有了光明神圣、庄严吉祥的宗教意义,从而成为佛教的吉祥标志之一。

图二 龙门石窟北魏开凿的古阳洞北壁第234龛造像
卍字符很早便出现在佛教造像艺术中。佛经中认为,佛胸前有卍字相,有时是三十二相之一,是指佛陀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殊胜容貌、庄严德相,由长劫修习善行而得;有时是八十种好之一,是指佛陀善相的八十种细微特征,如无见顶相、眉如初月、耳轮垂埵等。考古发现,龙门石窟古阳洞北壁的魏灵藏等造像龛坐像和南壁的丘法生造像龛坐像(图二)胸前均发现有“卍”字纹。“其中,在龙门石窟北魏开凿的古阳洞北壁第 234 龛陆浑县功曹魏灵藏等造像上出现了最早的‘卍’字纹”[13]。此像为太和末至景明年间(即北魏孝文帝和世宗宣武帝期间)所造,禅定佛像双手作定禅印,袒右肩大衣,结跏趺坐,胸前有火焰宝珠纹,宝珠中心有一卍字;而南壁第66龛的比丘法生造像胸前同样也有卍字,此二尊佛像均为北魏所雕刻,是目前颇为少见的最早的卍字纹;单尊石佛像上目前较早出现佛胸卍字的例子可见北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石造三尊佛立像(现收藏于美国森特路易斯美术馆),该造像面相清瘦,体形修长,主尊胸前有一阴刻卍字;山东青州曾出土北齐时期一尊石造倚坐佛像,该像高64厘米,袒右肩,露肤处施金彩,胸前清晰可见一黑色卍字;河南安阳大留圣窟开凿于东魏武定二年(公元 554 年),窟内三尊石佛坐像胸前都有浮雕卐字相,从其饱满的躯体和U型阴刻衣纹分析应属北齐所造,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三尊佛像原是北齐时代单尊雕凿,而后移入洞内的。”[14]此外,我们在麦积山石窟西魏第44窟主尊胸前、炳灵寺石窟第8窟西壁隋代泥塑坐佛胸前及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年)的甘肃张掖大佛寺(西夏护国寺)卧佛胸前均可见清晰卍字。另据穆宏燕教授研究,景教的十字莲花图案与卍字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景教即唐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也就是东方亚述教会。“景教饰牌以十字为骨干而变化出多种样式,外缘呈六角或八角,又喜作展翅鹰形”[15],反映太阳的光芒照耀,成为“人们祈望灵魂进入光明天国的象征。”[16]
我们在谈论佛教艺术中卍字符的发展历程时,有一处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这便是敦煌佛教艺术。开凿于北凉时期的第275窟堪称“敦煌第一窟”。该窟雕塑和壁画带有浓厚的西域色彩,“铁线描”和西域式的凹凸晕染法,使整个洞窟的壁画呈现出既古朴又豪放的艺术特色和风格。从北凉到南北朝时代,我们可称之为是莫高窟的幼年、童年时期。此时的洞窟明显带有一种舶来气息,一种西域气息,身处其中彷佛能听到遥远的袅袅梵音,清润着人们的一颗尘心。“一般来说,凡是佛都胸有卍字相,有时也称德字相、德卍字印相,‘卍’是符号,‘德’是含义” ……“虽然佛经记载诸佛都胸有卍字,但佛教造像中的佛像多数没有画、刻、塑出卍字相”[17],莫高窟的佛教造像中亦存在此种情况。根据敦煌研究院雷蕾与王惠民的考证来看,北魏第251窟、第254窟和第263窟3个洞窟中有8个主尊胸前有卍字相。这一时期洞窟壁画的人物形象造型朴拙,线描苍劲,色彩淳厚;主尊面相丰圆,神情庄重,胸前卍字相按照佛教义理光明彻照无量世界,衣冠服饰上尚保留有西域、印度和波斯之风,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氛围。西魏是莫高窟内中原的神与域外的佛开始相融相映、交叉并存的时期,敦煌佛教艺术的中国化在此时期肇始。这一时期的主尊们面容清瘦,眉目疏朗,“秀骨清像”如春风一般感染了处在勃发期的佛教艺术,第248窟、第249窟、第285窟、第288窟4个洞窟的5个主尊胸前有卍字相(图三),在宝花(佛胸前椭圆形或圆形的类似花盘的图像)的映衬下传递着佛的无量功德。北周第297窟西壁龛内主尊胸前有卍字相。莫高窟隋唐时期的洞窟中目前发现有卍字相的有隋第420窟主室三龛主尊袈裟及初唐贞观年间第220窟主尊胸前。
众所周知,卍字相在梵文中叫做 srivatsa,表“吉祥之所集”之意。“佛教认为它是解释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作‘万德吉祥’的标志。”[18]佛经《大藏经》《观佛三昧海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等佛经中均记载佛胸前卍字相的功用是发出的光可以照亮世界,庄严胜妙,从而化度众生,如金刚一般坚固真实,不可破坏。

图三 莫高窟第288窟南壁人字披下说法图主尊胸前卍字相 雷蕾临摹
佛教为何会崇拜光明,以光明为美呢?祁志祥教授这样解释:“《探玄记》卷三道破其中奥秘:‘光明亦二义:一是照暗义,二是现法义。’光明一能照亮黑暗,二能显现佛法真理。”[19]佛教从其因缘聚散的角度对事物虚妄不实的本质进行阐释和理解,但同时佛教又指出,事物从现象上看又是存在的。这样,佛教就从对现实美的否定走向了再否定,也就是从另外一个维度对美又进行了变相的肯定。这样一来,佛教就表现为在否定一切世俗之美的同时又借助世俗的美去描绘天国和佛祖。因此,光明之美便成为佛教变相肯定现实世界的美中较为突出的一种形态。在现实生活中,光明使人心情舒畅,黑暗则使人心情压抑。因此,佛教便以具有无上般若智慧和洞悉万物本体之明的成佛境界为“光明”境界,佛胸前的卍字相放出百万亿光明,化度众生,表达快乐、幸福和美的境界,佛教对此是称赞的;而那些背离妙明真智,执空幻物色的世俗认识则被认为是“无明”(即没有光明、没有方向之意,泛指无智、愚昧、浑沌等,特指不懂佛教道理的世俗认识)的,人的一切生老病死之苦都是由“无明”所造成的,它执假为真,是丑的、恶的,佛教对此是批判的。因此,在这种赞美与批判、肯定与否定中,佛教以光明为美的思想就得到了充分展示,佛胸前的卍字便承载着越来越重要的光明职能,如《楞严经》中描述说释迦世尊说法时,卍字首先大放光明,此字加持力可以周遍十方微尘普佛世界。
即时如来,从胸卍字涌出宝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尘普佛世界,一时周遍,遍灌十方所有宝刹诸如来顶,旋至阿难及诸大众,告阿难言:吾今为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众生,获妙微密性净明心,得清净眼。
又如《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描述卍字印之光可化度众生、消除十二万亿劫生死重罪。
如是百万佛皆同一字名栴檀海。是诸世尊。以胸德字卍字印光化度众生。时彼童子亲侍诸佛间无空缺。礼拜供养合掌观佛。观佛功德因缘力故。复得值遇百万阿僧祇佛。彼诸世尊亦以身色化度众生从是已后即得百千亿念佛三昧。得百万阿僧祇旋陀罗尼。既得此已诸佛现前说无相法。须臾之间得首楞严三昧。
佛告阿难。佛灭度后佛诸弟子。见佛胸相光者。除却十二万亿劫生死之罪。若不能见胸相分明者入塔观之。如是观者名为正观。若异观者名为邪观。
再如《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描述诸佛胸前卍字放出百千光明,光明可以为众生演说无量六波罗蜜法(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诸佛胸中有百千光。从万字生。——光中歌百千偈。演说檀波罗蜜。如是众光演说。六波罗蜜其偈无量。行者正坐闻无量佛皆说是法。
以上种种,我们可以推断出佛教是非常推崇卍字的光明、化度及坚不可摧的力量的。黑格尔说过:“宗教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者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况之下,艺术确实在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虽然佛教从其哲学本体论来看是否定一切美的,但是我们通过佛经及相关资料又会经常见到一些诸如对理想国犍陀越城精美装饰的描写、对菩萨极致美丽的刻画,对自然风物、山川大河之美的描写与领悟,说明佛教是注重客观美的现象的,它通过观照自然这样一种审美实践活动来启觉佛性或者证悟空理,在某种程度上也提升了人的审美能力。同时,佛教在中国本土化发展过程中亦顺应世俗的审美趣味,“批判昏暗之丑,赞美光明之美,并吸取这种外光明之美为营造佛、菩萨的身光明服务,借用这种外光明来比喻、形容领悟佛法的心光明、法光明之美,进而将光明之美的根本、根源置于心光明之上,从而完成了对‘光明之美’思想取向的建构”[20],使卍字照亮化度万千众生,将神圣美满遍撒人间。
三、泛世俗化时期:吉祥、世俗之美
朗格认为真正的艺术其实都是在表现一种生命的形式,艺术的结构形式就是生命形式的投射。也就是说,一件成功的艺术品、艺术符号看起来都应该“像一个高级的生命体一样,具有生命特有的情感、情绪、感受和意识。” [21]一方面,它能够通过情感、运动等因素来表现生命;另一方面,则通过表现性而非再现性呈现一种内部的高级连接。左旋的卍与右旋的卐在佛教看来是一种“轮回”,实则也是表现人类生命体生生不息的运动。它虽然是静态的,但它的内涵意蕴却是动态的,它以静态的形式展示与复现了人类情感千变万化、微妙莫测的动态形状。在卍字符不断世俗化发展的进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通过这一符号,为整个人类艺术表现活动和情感活动提供了多重交织的线索,艺术形式与人类情感在逻辑上达到了同构。

图四 唐代铜镜
中晚唐至五代宋元时期,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越来越紧密,卍字符从形制和美学意蕴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其逐渐开始脱离佛教,被广泛装饰于建筑、雕刻、服饰、器具及各种工艺品之中,其从佛教附属品的身份一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流行的吉祥图案之一。举例来说,唐代人们就偏爱将卍纹样大量用于铜镜的装饰,并将“长乐未央”“太平万岁”等祝福、吉祥式颂语铭于其上,以企盼将福善祥瑞、福寿绵长的美好寓意带给使用之人。图中(图四)所示铜镜卐居于铜镜背面正中位置,主纹以纽为中心作双线卐字形,工匠在卐字纹的转折空白处分别填入“永”“寿”“之”“镜”四字铭文,表达了人们渴望长寿的朴素愿望和对生活的美好祝福。铜镜中的卍字符不仅表现出这一时期人们对其的钟爱之情,还说明了卍字符从神圣庄严的宗教符号转向了仅供装饰的吉祥纹样上来,由此开启了卍字纹向世俗化发展的进程。宋元时期,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宋代,商品经济、文化教育及科学创新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儒学得到复兴,理学开始兴起,文人士大夫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充实,对性灵的自由抒发和清新淡雅的审美风格自然而然影响到了诸如瓷器制造、铜器制造等诸多方面。宋代作为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当时制造瓷器的官窑、民窑遍布全国,名瓷相继叠出,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异常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卍字符不再仅仅被民众认为是生和光明的寄托,其已经完成了从宗教符号向民间装饰符号的转变,其吉祥的寓意和表现出的富贵、清新、简约的审美情趣,使其成为世俗化的审美符号,大量、频繁地进入“寻常百姓家”,被当作喜闻乐见的装饰纹样广泛使用,宋代的瓷器、元代的粉盒等器物中均出现了简约清雅的卍字符图案。
明清之际,人们在“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观念的影响下,卍字符更是受到上至皇室下至平民的宠爱,人们通过在传统服饰、建筑及日常用品中融入卍的各种变体与组合来表达对其的热衷与喜爱,尤其是在服饰中融入卍的元素俨然成为当时的一种主流与时尚。皇家富贵、华丽的审美特征与平民清新、简约的审美情趣,最终使其完全达到了泛世俗化发展的状态,“其中正端庄、循序相生、对称均衡、不蔓不枝的形态和‘相生相伴’的宗教文化是世俗中精神寄托与品味彰显的体现”[22],如明朝的卍字纹大多以独立纹样或者以连缀的形式展现,在风格上注重清新、秀丽的表达,表现出一种平衡、稳定的艺术效果和视觉美感;清朝在前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继承和创新,通过将团寿纹与卍字符进行结合,象征富贵绵长,给人以连绵不断的艺术美感,艺术风格更趋向于奢华和富贵。在建筑及雕刻图案中,明清时期的设计师在镂刻木窗时非常巧妙地将卍字纹的传统所指与当时人们的审美诉求连接在了一起,形成了互益关系。卍字纹采用了方形架构,搭配线条的断续,在规整敦厚的基础上体现出一种连绵不断之感,线条的曲直变化搭配旋转对称的样式,给观者以庄重而不失灵活的视觉感受。卍字纹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虽是静态形象,却表现出一种动态的张力,复给人以一种质朴的秩序感与和谐感。同时,卍字还出现在了一些文学作品中,例如《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提到的“万儿”,便是她母亲在生她时做梦得了一匹卍字不断头花样的五色富贵锦后取名为“万儿”的,说明卍字符在当时已经深入到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了。
发展至近代,我们亦可从许多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手工艺术品中看见作为装饰图案的卍字符。山西平遥和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图案中均有以卍字符为基础的服饰和工艺品,这些图案整洁华美,表现出对称、均衡之美。在平遥一地,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年节风俗中通过广泛使用卍字符来祈求吉祥如意;青海互助土族在织毯过程中以红色为底、上织黄色卍字,象征对光明和神力的崇拜;贵州苗族在姑娘嫁衣上织卍,寓意生活如水车般旋转而滋润幸福;湘西苗族的挑花围腰上的卍寓意吉祥富贵;维吾尔族将卍在纺织品上连成锯齿状边框,象征吉祥如意,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四川凉山州、云南楚雄州、红河州的彝族妇女服饰上均有卍字符,意为大吉。彝族学者普珍从民族学视角出发,在其《彝族羊文化与吉符卍、卐》一书中对卍、卐字符从起源到发展、从具象到抽象、从巫术实践到哲学观念作出系统性概括后认为:“卍(卐)或十,在彝族文化中其实就是一对相交的羊角”;羌族认为卍象征人畜两旺,五谷丰登;藏区视卍为太阳,是一种护身符标志,“卍字符的变形符号在藏语中称为‘雍仲嘎奇’,寓意‘永恒不变’‘坚固不摧’‘吉祥万德’等”[23] ,在藏族的婚礼上、妇女的头饰、服饰及很多必需品上都有卍的变体,寓意吉祥美满,呈现出宗教情感和审美情感的交融。在几千年的绵延中,卍字符在世俗生活的瓷器、家具以及服饰中呈现出了基于线条组合的形式多样的诸多变体。它是美的,是富有表现性的,蕴含着一种华夏民族审美情感的抽象状态的表现。它被佛家借用并在中国民间取得认同地位后,深入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文化相融合,最终成为具有世俗化、本土化的审美符号。
众所周知,克莱夫•贝尔和朗格都强调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但朗格认为贝尔的“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的表述过于神秘,她认为具有人类情感的形式和表现性形式才是一切艺术所共同具有的本质。[24]卍字符生成于劳动实践,发展于宗教融合,回归于世俗生活,它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抽象与具象的统一,静态与动态的统一,表现着丰富的美学意味和内涵。卍字符自新石器时代出现至近代,其生成、发展、运动、变化都与中国人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审美精神紧紧交织在一起,从来不曾分离。在原始社会,它作为一种同原始人的思维和日常生活结合的非常紧密的符号来表达“灵魂不灭”的观念;自与佛教结合,它便蕴含了吉祥、光明、照亮化度万千众生之意;自与世俗生活融合,又双向地将吉祥美满寓意输入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对中华审美文化的认同和提升中,体现出生命力的无限张弛。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该符号一方面是对朗格“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这一命题的实践,另一方面更是对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再阐释,它从不同地缘和时空的推进中实现了向人类精神共同体的过度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靳玉兰.试谈卐字的渊源及其审美特征[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03).
[2][4][5]王克林.“卍”图像符号源流考[J].文博,1995,(03).
[3]王仁湘.中国史前考古论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434.
[6][7]张丽莎.西藏的岩画[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99.
[8]夏擦·扎西江才.本布论世 [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41-42.
[9]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512.
[10]杨甫旺.“卍”符号与生殖崇拜[J].四川文物,1998,(01).
[11]郭戎晶.论“卍”符号美学意蕴的发展与演变[D].武汉纺织大学,2012,12.
[12][美]苏珊•朗格.哲学新解[M].哈佛大学1957年英文版,40-41.
[13][14]金申.佛胸前的卐字·佛教美术丛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95-97.
[15]金申.景教的十字纹饰牌·佛教美术丛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207.
[16]穆宏燕.景教“十字莲花”图案再认识[J].世界宗教文化,2019,(06).
[17]雷蕾、王惠民.敦煌早起洞窟佛像的卍字相与如来心相[J].敦煌研究,2012,(04).
[18]辞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220.
[19][20]祁志祥.佛教“光明为美”思想的独特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3.(05).
[21]吴风.艺术符号美学[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16.
[22]梁惠娥、刘荣杰.中国传统服饰中“卐、卍”字纹的关联机理与现状研究[J].服装学报,2018,(05).
[23]夏格旺堆.“雍仲”符号文化现象散论[J].西藏研究,2002,(02).
[24]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8.
【该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敦煌艺术典型符号研究”(18XZW005)】
原刊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王金元(1979—),藏族,甘肃甘南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及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厅级项目1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