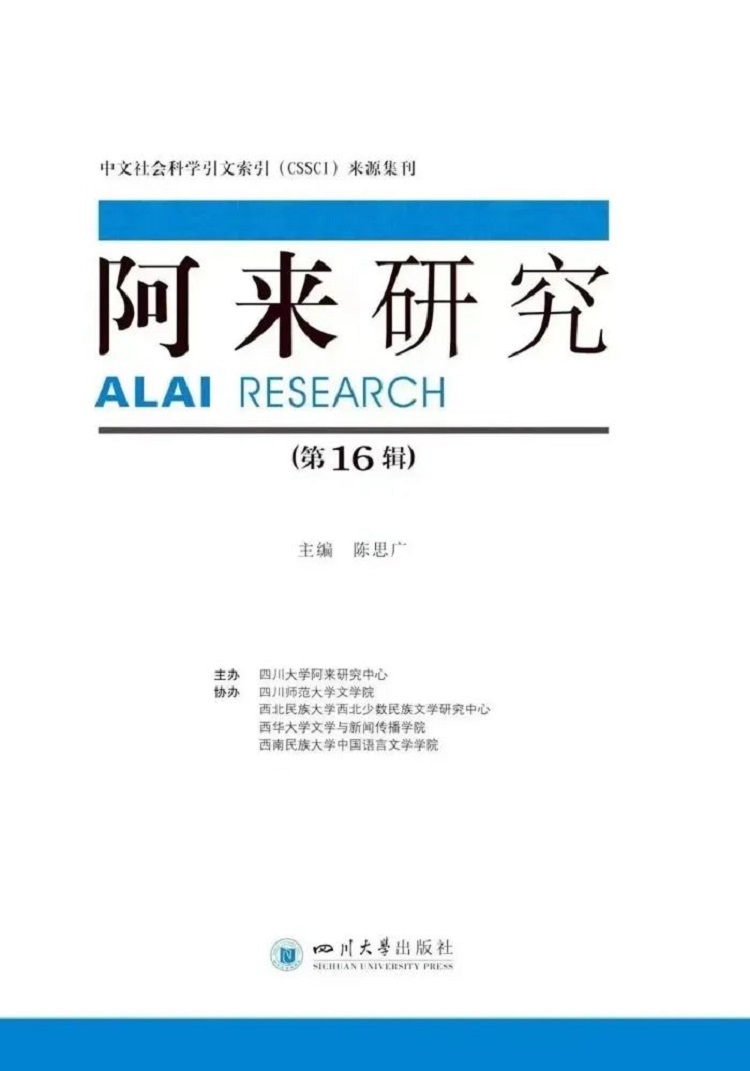
1.作为符号的“阿来”
2013年11月24日,四川大学阿来研究中心授牌仪式在望江校区成功举行。2014年5月24日,《阿来研究》学术集刊首发,阿来出席仪式并捐赠图书。这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的所指首次超过作家阿来本身,成为辐射藏地作家、四川作家及民族作家等研究领域学术刊物的前缀。其后,2019年3月9日,首届“阿来诗歌节”成功举办并于3月29日面向全国发出了《2019“马尔康首届阿来诗歌节”原创诗歌大赛征稿启事》;2020年10月20日,“阿来书屋”揭牌仪式在阿坝州马尔康市AAAA级景区松岗柯盘天街举行;2021年4月23日,“阿来书房”项目启动。作为阿来协同《四川日报》联合打造的“城市会客厅”,“阿来书房”是“阿来”文化品牌的线下实体空间,兼具图书、文创、展演、发布活动等多种文化功能。如此众多的“阿来”项目,如此丰富的学术与文化活动,显然已不是单指阿来本身,而是指涉“阿来”这个符号,而被符号化后的“阿来”承载的亦不单是个人的身份意义,转而成为藏地、四川甚或文学、文化的一种代言词。
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其著作《人论》中做出论断:人是符号的动物。他说:“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它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1]而“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2]。我们也可以说,从《阿来研究》到“阿来诗歌节”“阿来书屋”“阿来书房”,再到后续的“阿来”品牌,就是阿来作为当代著名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参与的符号构建活动,通过“阿来”符号的建构,借用阿来本身具有的文学号召力与吸引力,扩大符号的表意系统,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召唤结构。这一召唤结构,使得学术之网关联到多民族创作与区域文学,使得文学深度参与当代文化,影响当下文化产品,进而促进新文学、新文化的生产。可以说,“阿来”符号的逐步建构为我们进一步筑牢学术之网、文化之网创造了模板。这个结构丰富、扩大了“阿来”这一能指原有的所指意涵,涵盖了更多的文学意义与文化使命。《阿来研究》由“阿来创作研究”辐射到“藏地文学研究”“四川当代著名作家研究”“民族文学研究”,研究视域超越单向度的、单纯的阿来一人,辐射至藏地与四川,同时兼备海外视野。首届“阿来诗歌节”截稿时收到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稿件850余件,参与人数420余人。第一届一等奖得主是来自黑龙江的诗人杨文霞;;第二届得主是内蒙古诗人迟颜庆;第三届得主是陕西省诗人谢丽荣。“阿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引发的是全国各地多民族人民的文学热情与文学参与,其意义正如阿来所谈及的,“觉得最引以为豪的地方不在于说有一个诗歌节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而是把它作为对家乡的一个贡献”[3]。而已经落地的“阿来书屋”与正在发展的“阿来书房”,正进一步丰富着“阿来”符号的内涵。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项目、活动宣发时,大众媒体的报道大都提到了阿来作为“茅盾文学奖”得主的闪光头衔,这其中同样也体现了一个指称被符号化后所具有的号召力、权威性与附加值。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阿来可以说是高频次、深入地参与了“阿来”符号化的构建过程中,由之我们也看到,“阿来”符号意义指称广泛而非局限于单一视角,它指涉当代作家积极参与文化事务、组织文化活动,参与构建城市人文精神,扩大文学本身影响力,建设城市人文景观的文化担当等多重意涵。面对这一情形,我们不禁在想:在商业运作与名家效应背后,阿来何以被符号化?阿来与其创作具备何种特质?我们又应当如何认识“阿来”符号的深层意义?这些就是本文意欲探寻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2.普遍性追求
阿来曾在不同场合多次阐述自己的身份特征—“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4]。王一川就这一特点在1998年《尘埃落定》出版之初就将阿来的写作视为“跨族别写作”[5],并定义“跨族别写作是一种跨越民族之间界限而寻求某种普遍性的写作方式”[6];徐新建则认为“与其叫作‘跨族别写作’不如称为‘双族别文学’”,并指出“阿来通过小说所追求的‘普遍的意义’和‘普遍的历史感’其实是为了在消除别人眼中的‘异类感’之后,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对‘普遍性’的解释、建构和创造”[7]。我们暂且不论两种“正名”孰是孰非,两位学者通过对阿来文化身份的讨论,都并非意欲划定阿来的族别归属,而是指向阿来的文学理想,即对普遍性的追求。阿来文本中所追求并达到的人类普遍性表达成为其符号化的基础。
回溯阿来早期小说作品,我们可以梳理出一个敏感的文字工作者在进入写作之初笔尖流露出的身份焦虑和对民族、身份的早期思考。阿来的小说处女作《红苹果,金苹果……》一文,讲述了少女泽玛姬培育、种植良种苹果,带去市场售卖时所经历的对自己藏族服饰和装扮感到的不自在与别扭。其间又刻画了两个性格迥异的少年:一个是泽玛姬的同桌,藏族的干部子弟,“是藏族又要竭力装着不象藏族的样子”[8];一个是开朗、热情的买蘑菇的藏族小伙。人物设定虽略显生硬,但集中体现的却是阿来20世纪80年代数篇小说中人物对于自身民族身份的焦虑感和作者关于民族、身份焦虑的叙述与思考。《血脉》中“我”是汉族爷爷的藏族孙子,爷爷至死都向往着故乡,追寻着汉族的生活方式,为“我”取汉族名字,送“我”去上学。而爸爸和爷爷一样近乎固执地坚守着自己“藏族人”的身份,穿着厚实的紫红色氆氇,行走在人群中,城市“稠密的人流在他面前自动分开,就像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头野兽来到了人群中间”[9]。文末,面对三代人之间心灵的隔阂,“我”感叹道:“一生中间,爷爷、我、我的亲人都没有找到一个窗口进入彼此的心灵。我们也没有找到一所很好的心灵医院。”[10]
《猎鹿人的故事》中桑蒂因为交往两年的汉族女友与他分手,愤恨之际割下女友的鼻子;他出狱后回到家乡,上山后走过一条长长的坎坎坷坷的路找到“父亲”,找到“根”的所在。《槐花》写的是跟着儿子进城做了看守车场工作后无所适从的老头子在异乡的失语和对家乡的追寻。“老头已经很久不说家乡话了。再说除了家乡话,他只能讲几句和守车有关的几句不连贯的汉语。所以几乎失去了说话的机会。”[11]他把床拆了,躺在熊皮上听着松树油脂燃烧的声音才能安然入睡。《芙美,通向城市的道路》以娶了汉族妻子的“我”的视角记录了因擅长奔跑而进入城市的“混血儿”(汉藏混血)历经沉浮又回归乡村的故事。这些都是阿来早期对民族身份认同问题进行集中展现和讨论的作品,这些作品具备强烈的民族性特征。而后的中长篇小说文本逐渐远离民族身份讨论,走向普遍性追问。我们再回溯作者的早期表达,《红苹果,金苹果……》中的少女的局促难道不是中国贫困山区所有向往外界而又羞涩敏感的少女们的缩影吗?而《血脉》中,“那样的情绪不可能只属于一个藏人或汉人的感受。那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普遍感受。—那种被烙得生疼、格格不入的异类感觉”[12]。阿来带给我们的是异质经验之上的普遍感受。《槐花》与《芙美》则讨论了老一辈随子女进城后产生的无所适从、格格不入的孤独感与青年因一技之长进入城市后又复归乡村的普遍社会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最初关乎民族认同的问题,在阿来的文本中已经演变为在时代变幻下普通个体关于故乡与远方、城市与乡村的问题,而这恰是阿来能够被符号化,指称普遍现象而非特殊空间的基础。
2000年11月,阿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老房子》写于1985年,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在此之前我写诗。《老房子》写的是土司官制,后来我就离开了这个题材,没想到十年后《尘埃落定》又回到了这个起点。”[13]而事实上我们知道,阿来的第一篇小说是1984年《民族文学》第9期发表的《红苹果,金苹果……》。阿来对《老房子》作为小说写作“起点”的认定,意在强调的绝非是《老房子》一文的艺术成就,而是蕴含着对十年后重启土司主题的《尘埃落定》一书的高度认同。顺着这条线索,我们恰恰发现从普遍性追求出发后阿来文学创作的重要指向:从历史走向现代。
关于历史,阿来曾表示:“我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她的运行、她的变化”,“通过自己的观察与书写,建立一份个人色彩强烈的记忆”。[14]梳理阿来《尘埃落定》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可以复现一条以文学再现康藏历史变迁,记录其运行、变化的长廊:从追溯藏民族建立的重述神话作品《格萨尔王》[15],到记录雍正八年开始对瞻对的七次用兵直至1950年第十八军解放瞻化县城的非虚构文学《瞻对》[16],到写从民国至1949年后退出历史舞台的末代土司的故事《尘埃落定》[17];再到记录当代康巴乡村沧桑之变的《空山》[18];写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灾区如何重建移民村、抚慰亡灵的《云中记》[19]。从古至今,特别是近百年来康区的历史在阿来的笔下,在一个个主角、配角轮番上场的演绎中,留下了鲜活的印记。但阿来在这里—在这宏大历史叙述与个人命运的展示中,始终以一种现代的眼光穿透历史,烛照生活,从而使其作品以鲜明的现代性昭示于读者。
何谓现代性?我们可以采用这样的观点:“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理论抽象、基本框架;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具体实现、现实展示;现代性代表着与‘传统性’不同的理念和因素,现代化代表着与‘传统社会’不同的崭新时代和社会形态。”[20]也即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思维理念、信仰法则,现代化是物质层面的现代更新与进步。阿来重构历史的书写融入与继承了现代性反思的文学传统,从《尘埃落定》中鸦片、军火、商业贸易进入寨子直至最后土司家族的随风飘散,到《空山》里“文革”与改革开放两个大时代背景下的机村日常书写,阿来一直在用自己的文字记录着现代性进入康藏地区的宏大历史与琐碎日常,在叙事中贯穿着独特的历史意识和清醒的文化反思。《格萨尔王》创造出说唱人晋美这一形象,以现代性观念重构古老史诗。“山珍三部”较以往的文本则人物、事件、时间更为现代,从三个珍稀物产入手,更直接地把视线聚焦在现代社会的现代化问题上,“由于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这是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行为,其实都特别息息相关的时代—就造成了自然的不断破坏,环境的不断恶化”[21]。阿来借机村为载体展开的是康藏地区在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惨淡挽歌。在物的层面上乐观的历史叙事被消除,在人的层面上他者消失,现代人走向了孤立无援的境地,面对这些,我们该作何思考呢?阿来从现代性叙事中的裂缝与悖论之处走向的正是更深层的现代性反思。
阿来选用了相当具有现代意味的事物去书写现代化导致的生态与文化破坏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到《空山》中机村的人们开始使用电灯、电话、汽车等种种节省物力、人力,缩短距离、耗时的现代化工具;在现代性势如破竹的进攻下,旧事物不断沦陷,机村人走向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新生活。而新事物的到来在阿来的笔下并没有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随之而来的人性异化、物欲膨胀、生态破坏让淳朴、美好、和谐的古老村落迅速败落,古老的寄托如《尘埃落定》里的寨子一样最终随风飘散。在旧事物败落的同时,新的合理性也被摧毁,进化论式的历史进程被质疑,“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22]的逻辑被推翻。关于这样的文本特质,在阿来创作日益丰盛的时候,梁海就指出:“阿来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让我们回溯历史的轨迹,并用现代性来观照、反思人性的复杂。”[23]南帆同样认为,“同《尘埃落定》一样,阿来的《空山》再现历史的时候仍然表明了一种边缘的乃至另类的观点”,“《空山》将这个小村庄和几个藏民带入一个巨大的历史主题—现代性”。[24]
沿历史纵轴延伸,作者又表现出对当下的思考。面对现代性,阿来并非绝对否定、拒绝与排斥,相反阿来看到了现代化带给人类绝对性的处境变化和便利,他利用现代化物品作为载体展示居民切实的现代化需求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中篇《三只虫草》来说,桑吉为百科全书去县城里寻找调研员,一路上搭车、住宿,怀着对百科全书的向往,走出故乡走向城市,看到城里电视更多的频道,看到神奇虫草的普通归宿。这与《啊,香雪》中香雪为铅笔盒登上火车后意外离开台儿庄驶向向往已久的地方有着叙事上的同构性,都蕴含了稚嫩少年对广阔世界和现代性的向往。在驶离家乡的路上,他们看到了更广大的存在,也看到了现代城市的虚妄。喇嘛说:“那一路上要染上多少尘垢,经历多少曲折,情何以堪!情何以堪!”[25]可面对黑暗与挫折,桑吉还是选择了走向大海,在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展开他面前的百科全书,用电子邮件告诉老师说:“还有,我原谅校长了。”[26]可爱的桑吉最初为他的虫草做了各种安排,围绕的都是现代化带来的种种物品:姐姐的裙子、老师的洗发水、奶奶的膏药。“这是一株可以换钱的虫草。一株虫草可以换到三十块钱。”[27]三十块钱,可以买包骨痛贴膏给奶奶缓解疼痛,可以买件打折的漂亮衣服给姐姐,可以给表哥买副他向往已久的城里孩子戴的皮手套。现代化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扩大了人们的活动半径;现代化带给我们更丰富的食物,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更便捷的交通。面对前进中的尘垢与曲折,阿来选择的或许也是走向大海吧。然而支流如何汇入?我们所应持有的理性为何?个人所应负的责任为何?阿来没有停止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发言,面对尖利的现实和看似无解的悖论,阿来没有退却,他向我们展开的是面向个体与真实的现代性书写与现代性反思,用记录对抗失落,用思想反抗荒诞。
总之,阿来用普遍性书写统摄了民族性,而民族性书写又给予普遍性补充。在历史中融汇现代性理念,则是丰富阿来普遍性书写的一大法宝。正是阿来所秉持的文学观、所实现的独特文本与其文本的深层含义所具有的人类共识性、共享性,才使得其符号化成为可能,才打造了其符号的宽广意义。
3.知识分子担当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阿来曾不无自负地说道:“我自己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不然,以我对知识的兴趣与天资,此刻应该在西藏的某个寺院里研习佛教经典吧。”[28]在作品所蕴含的普遍性力量使得符号化成为可能之外,作者自身的文学理想与文化担当则使得其符号化成为必然事件。
首先,就作家自身成长经历来说,阿来成熟于一个充满文学热情的年代。1977年恢复高考,阿来考上马尔康师范学校,1980年毕业。阿来在新时期浓烈、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下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这当然为年轻的阿来提供了更为充沛的艺术想象空间。我们知道,“知识分子”有两个词源:一是来自俄语,代表俄国19世纪受过西方教育的不满于现状、批判主流社会的群体;二则来源于法国,出自因德雷富斯事件发表的《知识分子宣言》一文,同俄语中的“知识分子”一样,代表一种社会道德与批判意识,不过法语的“知识分子”包含在公共领域公开发言的意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兼具批判与公开发言的基本特质。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审视阿来的小说时,我们发现,阿来几乎所有的中长篇小说中,都有一个地方知识分子式的人物,通常是男性角色,他们具备成熟的理性思维与反思能力,无一例外地爱读书、好学习,具备良好的学识与道德并兼备一种文化责任感。在《尘埃落定》中是两次被割下舌头仍然秉笔直书的书记官翁波意西;在《空山》里是在动荡时期从学校背书回来建立树屋,历经村庄动荡,最终留下关于村庄记载的达瑟;在《格萨尔王》中是直接出现的叙述者晋美;在《山珍三部》里是充满求知精神,要看到虫草长大后的样子的桑吉,是固执地做着对村庄的记录和对柏树的考察的王泽周。这个男性自我在阿来小说中反复出现,却并不重复。这类人物坚实地存在于文本中,以其意识统摄全文,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作者的“第二自我”[29]。而正如文学理论家们所说,“隐含的作者的感情和判断,正是伟大作品构成的材料”[30],这些人物身上投射有作者自身的影子,也承载了作者的厚望。他们的选择与指向就是文本的选择与指向,而他们所蕴含的知识分子的清醒与担当则同样寄予了阿来的理想。
其次,具体到作品中,阿来塑造了一群具有相当反思能力、文学储备、文化担当感的“这一个”典型角色,这些角色无一不是知识的承载者、文化的反思者、时代的见证者,甚或是历史的记载者与言说者。《尘埃落定》中翁波意西两次失去舌头,第一次他预言土司们将要从这片领土上消失而落难,在狱中的他“想看书想得要命”[31],傻子少爷把麦其家早期还有书记官时记载的历史给了他;第二次,被割掉舌头的翁波意西请求成为麦其土司家的书记官,延续中断多年的传统。在傻子少爷大获全胜从边境归来,送给他一支钢笔时,面对天空般的蓝字,翁波意西发出了声音,恢复了说话能力,又因在继位的关键时刻为傻子少爷发声再次失去舌头。第一次失去舌头时,作者饶有意味地为19章取名为“书”[32],第二次失去舌头时,则发生了一段关于“历史”与“记录”的颇为耐人寻味的对话:
我说:“你不要再说了,就把看到的记下来,不也是历史吗?”
书记官涨红了脸,冲着我大叫:“你知道什么是历史?历史就要告诉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就是历史!”[33]
作者借傻子与书记官之口展开关于历史记录的讨论,阿来的文本中就是时刻穿插着对于宏大概念的追问与探寻。最终官寨倒塌,一切尘埃落定,而“后来的人会知道土司领地上都发生过些什么事情”[34],书记官“写下的东西都有一式两份,一份藏在山洞里,后来总会有人发现的。一份就在他身上,他写下:‘但愿找到我尸体的人是识字的人。’”[35]最终呈现再读者面前的末代土司故事由阿来写成,由我们共同阅读。“作为一个记载历史的人,在官寨里,他记载了麦其土司宣布逊位而并不逊位,记载兄弟之间关于土司位子的明争暗斗,记载土司继承人被仇家所杀,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历史的重复。现在,他却在边界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东西,一双眼睛灼灼发光。他会把这一切都详详细细地写下来。”[36]阿来如是描写书记官跟随少爷到达边境市场后的场景,仿佛描写自己一般。
《空山》里的达瑟骄傲地说:“我有好多书,我有一个图书馆。”[37]在书屋上,达瑟给叙述者“我”拿出一本百科全书,展示书中的彩色图片与植物名称;在别人质疑自己记载觉儿郎峡谷的古歌的功用时,平时木讷少言的达瑟“挺直了身子,一脸庄重:‘那就是以后的书。’”[38];在树屋被毁的时候达瑟的精神同步崩塌;机村拆迁时,人们发现达瑟留在墙壁中的皱皱巴巴的笔记本,这里面是“有关植物学的,只是一两行字”“也有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的想法”[39]。这章里作者设置了第一人称限制视角与全知视角交叉的叙述,“我”与写作者、“我”与达瑟,叙述者与被叙述者交织。看到“植物学”这三个字,再读读阿来的博客与《成都物候记》,我想我们很难说服自己不进行一种代入和阐释:达瑟和“我”,究竟谁才是阿来?这个问题不必解答,我们不必做一种强制解释,将作者对位于人物,这毫无意义。我们意图提炼的是作者灌注于这类人物身上的品格与理想。
“山珍三部”中阿来承接以往文本关于在历史中进行现代性反思的思考,在第三部《河上柏影》文末写道:
但从有人以来,就有人在做记录那些消失的人与物的工作,不为悲悼,而为正见。不然,人就会像从来没有在地球上出现过一样。
因为人,毕竟是在这个地球上出现了。[40]
从《一个村庄:石头和柏树的故事》到《从一个民间传说着手,对一个村庄关于宗教发源事实的考察》,《河上柏影》中“混血儿”王泽周固执地做着对村庄的记录和对柏树的考察,最终给出了柏树下花岗石的地质来源:这颗石头不是神僧施法用来镇压异端的飞来石,“虽然传说里是这么说的,后来,县里请来的地质专家也是这么说的”[41],石头下也没有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面对传说与后来的权威,他没有人云亦云,那个装满书籍的柏木箱子,养成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些系统的知识给了他清晰的思路。最终,王泽周计算出了三颗柏树的年龄,将准确的数据写进自己未完成的论文中。而这个伴随王泽周整个求学经历的箱子,这个曾经承载知识、为他甄别哪些书值得留下的箱子,依然散发着醇厚的植物香气,在父亲的手下变成了儿子的书柜,继续承载下一代的求知、求真精神。
阿来正在书写的也是作家与我们共享的时代记录。作家将自己注入作品,赋予作品骨骼与肌理、气韵与风格,这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而正是这样贯彻其人生经历与作品的一种知识分子担当意识,使得阿来积极参与“阿来”符号的构建,也正是由于作家的参与,“阿来”符号的构建呈现出繁荣之势。在作家的文化使命感下,“阿来”这一符号辅佐了多民族文学的发展壮大,促进了城市阅读空间的扩展,也助力了区域文学的研究。如果说是阿来作品中的普遍性追求为其符号化奠定了基础,那么作家本身的文化心理与文学定位则是其普遍性追求的根源,同时也是其符号化的最初源头。
从阿来的符号化之路与对其符号化的溯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丰富的阿来与其文化意涵的展开。阿来的作品并非执着于小道,而是追求大道,意在启蒙,志在记录,顺应时代潮流而有自己的作为与抱负。走出作品,回归作家,我们依旧能发现阿来的独特之处,阿来并不是一个文艺气息极其强烈的作家,相反可以说他具备相当的理论知识储备,在文化责任感之外具有一种知识分子公开发言的能力。阿来的作品中永远不乏关于历史、语言、人性、政策等的宏大概念,阿来的发言中也充斥着“消费主义”“东方主义”“文化多样性”这些学术语言,阿来的新作《以文记流年》更是以对杜甫精当而又深刻的解读体现了丰厚的学养。那么,面对“阿来书房”我们也就不必惊讶了,阿来的意义就在于他不是一个隐士,而是一个积极的文化参与者、制造者与发声者,他从不拘泥于地方,而是放眼世界,他深刻地进入历史,承接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反思与知识分子传统,跨越20世纪80年代,在21世纪做出自己的文化选择,承担属于著名作家的文化责任,为地方文化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如果说以前阿来是一个记录者,立志成为地方文化的书记官,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阿来也是一个文化的制造者,其符号意义的来源亦是其符号意义的内涵,这一文化符号的形成会赋予作家新的力量,也会赋予文学研究、城市文化以源源不断的活力。
注释:
[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2]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3]《四川作协举行第二届“阿来诗歌节”原创诗歌大赛颁奖典礼》,中国作家网,2020年10月27日,h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1027/c403994-31907656.html.
[4]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资料》,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5]王一川:《跨族别写作与现代性新景观—读阿来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中国文化报》1998年第26期。
[6]王一川:《旋风中的升降—<尘埃落定>发表15周年及其经典化》,《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
[7]徐新建:《权力、族别、时间:小说虚构中的历史与文化—阿来和他的<尘埃落定>》,《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8]阿来:《红苹果,金苹果……》,《民族文学》1984年第9期。
[9]阿来:《阿来文集》(中短篇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页。
[10]阿来:《阿来文集》(中短篇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5页。
[11]阿来:《阿来文集》(中短篇小说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6页。
[12]张莉:《阿来:异质经验与普遍感受—读阿来短篇小说<血脉>》,《名作欣赏》2013年第28期。
[13]尚晓岚:《阿来翻新旧年的血迹》,《北京青年报》2000年11月19日。
[14]阿来:《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文化》,《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09年第1期。
[15]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16]阿来:《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人民文学》2013年第8期。
[17]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阿来《空山》第一卷发表于《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4年第5期,至《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发表第六卷完稿。
[19]阿来《云中记》2018年5月12日动笔,2018年国庆节假期完稿,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出版。
[20]周穗明等:《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化批判》,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21]阿来:《我为什么要写“山珍三部”》,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第6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22]阿来:《蘑菇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23]梁海:《民族史诗最动人心魄的力量—阿来论》,《中国作家》2011年第3期。
[24]南帆:《美学意象与历史的幻象—读阿来的<空山>》,《当代文坛》2007年第3期。
[25]阿来:《三只虫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4页。
[26]阿来:《三只虫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27]阿来:《三只虫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28]阿来:《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民族文化》,《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2009年第1期。
[29]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30]W.C.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31]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32]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33]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页。
[34]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5]阿来:《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页。
[36]阿来:《空山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
[37]阿来:《空山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
[38]阿来:《空山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0页。
[39]阿来:《空山3》,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页。
[40]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18页。
[41]阿来:《河上柏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205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6辑

杨雪萍,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