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生存与发展”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如何保持平衡和谐地生存与发展,是目前人类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之际强调,加强边境地区建设,要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特别是在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就,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显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被提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要守护好这里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西藏建设要突出地域特点,引导激发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理念,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硬约束,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合理确定城市人口规模,科学配套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加强森林防火设施建设,提升城市现代化水平。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的生态环境,利在千秋、泽被天下。
要牢固树立生态理念与生态意识,西藏当代文学也发挥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化建构意义。以挖掘、阐释文学艺术和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为核心使命的生态批评理论的出现,就是人类追求生态和谐,保持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有力体现。生态批评理论以其深刻的文化反思和直面现实的勇气所洞察的人类内在需求与工业文明之间的某种潜在冲突,会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对现代人的生态启蒙,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人们已经习惯了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明取向等,从而为地区或整个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保障和智力支持。因而,本文将对西藏当代文学中的生态意识进行必要而深入的开掘与阐释。
一、西藏当代文学自然书写中的生态意识
(一)西藏当代文学中回归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态意识内涵
西藏当代文学具有强烈的自然书写倾向,且表现出回归自然、融入自然的鲜明主题。这种认同自然、亲近自然、讴歌自然、融入自然的审美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浓厚的生态意识。作家们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生态意识来自于大自然的熏陶。马丽华在游走西藏过程中,受到了大自然的熏陶:
我以为人生原本更简单——就为了这一片蓝天,一方草原,远天下孤独的野牦牛一个黑色的剪影,黄枯的山脊上一群滚动的羊子,就为了这一声鸟鸣、一丝微风……不是占有它们,就为了此生能亲眼看一看,亲耳听一听,这一辈子就很值得了。……人生对万物有情,万物才有情于人生呵!
她还描写了游历藏北文部时,完全融入纯自然空间的情景:
那是一个纯自然的空间,可以遥望明亮的日月之路,聆听太阳金链的金属声响,月亮处子的裙裾寒窣,大草原不胜其艰的叹息,小草们的喁喁细语。万物在交流,在合唱,人声以纯自然的方式加入了——在那个大地躁动之夜,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在远方凄凉地呼唤着,仿佛开天辟地,人的第一声嗥叫。
在这里,人类与大自然浑然一体,生命是这般的简单、质朴与快乐,这才是最理想的生命境界。马丽华不禁感叹:“牧人们与大自然耦合得如此之好,毫无优越感地自视为大自然的一份子,与几乎一切野生动物保持了友好睦邻关系,组成藏北共生共荣的生物圈,行猎只是偶尔为之。”在青藏高原,藏民族长期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平等地对待自然界的一切生命。
在很多藏族诗歌中,诗人们也极力展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状态。藏族诗人旺秀才丹说:“我是自然之子,是真理之子/是田野中守望生命的情人/不索取,也不拥有/这个夏天,我和所有火热的生灵一起成长/准备迎接烈日,暴风雨和黑暗/还要将心脏贴向大地/和田野、草原一起律动。”同样,藏族作家阿来也曾说:“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群树、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阿来长诗《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中充满了对大自然万事万物的盛情赞美与敬畏之情,特别是诗歌最后一节,更是表现了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一派其乐融融的和睦祥和之景。恰如李长中所言:“民族文学的生态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发性行为,也就是说,因为少数群体长期与自然为伍,与自然亲密接触,能够和自然水乳交融,和谐共处,这就形成了他们融入自然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是世代相传的,是指导自己行为处世的基本原则。”他们不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且拒绝对大自然的任何破坏与侵犯。
(二)西藏当代文学感悟自然的主体意识蕴含着一定的生态意识
西藏当代文学中的自然书写不是对自然景物的形态作简单的描绘,其中包含着创作主体感悟自然、体验生命存在的深刻意蕴,这种带有强烈的主体精神诉求的艺术行为,其实是对现代社会对人与自然和谐、平衡关系异化、扭曲的一种不满与拒斥,这同样包含着强烈的生态意识。譬如,扎西达娃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中有一段精彩描写:牧童达瓦次仁与老狼纳迪和一只灰斑麻雀争当贡帕拉山主人的故事。达瓦次仁九岁那年开始独自上山牧羊,他第一次到贡帕拉山顶,就看见一只老狼傲慢地盘踞在那象征大山主人宝座的莲花座形岩石上。有经验的牧羊人指点达瓦次仁,只要他能在七天之内牢牢占据山顶这块莲花座形岩石,不让别的飞禽走兽靠近,这座山就会和他神意相通,他就能从这看似荒凉的大山里获得牛羊所需的肥草、溪水,甚至财宝。很快,老狼纳迪向新来的牧童达瓦次仁挑起了一场权力争夺战。牧童达瓦次仁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气鼓鼓地捡起一块鹅卵石放在抛石器软鞭的石囊里,在空中挥舞几圈后,鹅卵石飞出去正好击中了纳迪的头颅,它翅趄几步从莲花座形岩石上跌落下来。当它挣扎着站起来时,达瓦次仁迅速摘下背上的小铜锅在它头上背上一阵乱敲乱砸,老狼因头部重创输给了弱小的对手。可是,达瓦次仁在莲花座形岩石上只当了两天主人,就被一只气势汹汹的麻雀赶了下去。灰斑麻雀成了这座大山的主人,人和狼都失去了自己的地位。
在扎西达娃讲述的故事中,牧童达瓦次仁、老狼纳迪和灰斑麻雀是大自然中平等的生命主体,他们都有自己的个性与尊严。虽然老狼纳迪与牧童达瓦次仁曾经是对手,但后来他们更像多年的老朋友。扎西达娃不仅赋予了老狼以"纳迪"这样与人类没有什么两样的名字,也极为细致地描写了老狼纳迪的心理活动。纳迪由于孤傲不羁小瞧了对手,从而彻底失去了反击能力,也失去了在人类面前的高贵尊严。及至生命的垂暮时刻,孤独浪荡了几十年的老狼纳迪向达瓦次仁投降了,它企望能够与人类友好和平地相处。可涉世未深的达瓦次仁未能理解老狼的深意,直到几天后,他在后山腰的沟壑里看见纳迪骨瘦如柴的尸体被几只秃鹫啄食成一堆白骨,达瓦次仁这才想起,“他们曾经用眼神互相交流过生命的语言,在一起互相憎恨和对峙、较量和盘旋了好几年,现在贡帕拉山上忽然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面对荒凉寂寞的大山,与其说死掉了一个敌人不如说失去了一个朋友,不由得升起一种茫然的失落感。”如果有一天,人类独自面对旷野,那将是何等的荒凉与孤独。扎西达娃通过牧童、老狼与灰斑麻雀的故事,表达了自然的主体性,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弱化了人类的主体性,表达了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生的期望。
不少藏族作家笔下都描写了人与动物的相互依存关系。次仁玉珍的散文《狗年说狗》描写了人与狗之间至为感人的深情,最终,猎狗为了保护主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扎西达娃在《古海蓝经幡》中说,他母亲有读报纸并经常对政府发表批评意见的习惯,有一次,政府发布了一条消息:“拉萨的野狗与城市居民的比例居世界之最”,政府发布此条消息显然有其用意,既然野狗太多,那就必须歼灭之。政府很快发起了一场灭狗运动,"她(扎西达娃的母亲——引者注)对此强烈反对,理由是这么多野狗只只都很壮实,正说明拉萨人生活很富裕,并且强调人不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霸道,应该同各种动物和睦相处。……她指出拉萨的窃贼比野狗更多。”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普通藏族民众对动物的态度,他们更强调人与动物和平共处。
藏北高原的牧民们还有这样一种生活习俗:家里的孩子刚能利索地跟着羊羔一起奔跑时,他们的父亲就会选出一只出生不久、非常洁白的羊羔,并在羊羔的耳朵上拴上红布条(意为放生羊),作为礼物郑重地送给孩子。这个习俗既可以培养孩子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感情,教给孩子藏北大地上最深的生存法则——人与动物的相互依存,又可以让孩子懂得,即使一只羊,人类也没有权利随意剥夺它的生命。西藏当代文学对自然主体性的感悟与描写比比皆是,其中蕴含着浓厚的生态意识,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二、西藏当代文学文化书写中的生态意识
无论是原始苯教,还是经过融合后形成的藏传佛教,都包含着万物有灵观念,这一观念的存在深刻影响了西藏民众的文化心理意识,他们因此而敬畏、崇尚自然万物。尽管西藏当代作家已经具有了现代理性意识,但在文学创作中,他们会把这种民族心理意识作为一种“审美因素”纳入进去,从而使作品蕴含一定的生态意识。央珍在《无性别的神》的再版后记中说:“大自然在西藏人眼里具有神性。西藏山山水水,都是众神所在,许多神山圣湖在自然崇拜里是有阴阳属性的。”的确,自然神性观念体现在不少藏族作家的作品中,格央在《西藏的女儿》中说:
在西藏人的世界里,神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天、地、水三界都有神,河流、树木、高山、泉水等等都是可能栖身的地方,在山口、路边、水中有看不见的精灵,甚至在家庭里也有家神,这些神与人们日常的生活、生产、祸福有密切的关系,会给人们带来帮助和祝福,但是如果触怒了他们,就会有灾难降临,因此,西藏的人从出生的第一天起直到生命的结束,都要和各种各样的神祇打交道。可以说人和神的世界是交叉在一起的。
格央的家乡小镇附近有一座不太大的山,据家乡人说,这座山是女神丹玛的仓库,所以平日里人们不常去那座山。直到有一天,附近一个人在这座山上打了猎,猎物是一只大大的獐子,可是,他还未及享受獐子带来的好处就急性病发作死去了。人们相信他杀死了丹玛女神的牲畜,触怒了丹玛女神,才遭到了报应。这件事发生后,人们再也不敢上山打猎了。正是这件事促使附近的人们彻底放下猎枪,从而保护了山上的野生动物。
同样,周艳炀的中篇小说《小猪倌和她的杰勒玛》也讲述了藏族人对“神山”的敬畏。月儿贡的拉丁村头人顿珠泽旺家的小猪倌巴姆和小羊倌旺姆去离村子比较远的果树林里放牧,偶遇黑熊和大花豹,动物之间一场凶恶的厮杀之后,花豹咬死了黑熊。管家误以为她们去“神山”放牧,一顿毒打之后她们被罚去山上的牧场放牧,不准下山,不准回村。这篇小说原本是要通过小猪倌和小羊倌的故事,揭露封建农奴制统治下底层劳动人民的勤劳、善良以及悲惨的生活遭遇,揭示农奴制社会的不平等以及改革的艰难,却无意中向我们展示了西藏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神山”的敬畏。农奴是不能以任何理由或借口到“神山”上去的,万一冲撞了山神,老天就会降冰雹砸倒青稞苗。即使是被花豹咬死的狗熊,鲁孜旺姆的两个爸爸也是没有权利剥熊皮、剜熊胆的。这恰恰体现了西藏古老的地方性生态智慧,在万物有灵观念引导下,人们敬畏自然的山川、河流、湖泊,即使忍饥挨饿,也要保护自己生存的家园,否则,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藏族人对圣湖也有着天然崇拜,圣湖的水是不能玷污的,圣湖中的一切生物都是不可侵犯的。不仅仅是神山圣湖,在藏族人心目中,神灵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在神山圣水崇拜的生态意识之下,发展出一系列规范人类行为的禁忌规则。可以说,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些禁忌规则,而非某一种宏观的叙事理念。”万物有灵观念作为一种深刻的民族心理意识,其中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意识,正是在万物有灵的神性自然观基础上,藏族先民赋予了万事万物以神性,这些不容侵犯的神性形成了一系列严格的禁忌,从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让西藏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珍贵的自然资源得到很好的保护,实现了可持续性发展。
三、西藏当代文学生态意识产生的传统渊源与现实动因
(一)西藏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对西藏当代文学生态意识的影响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人类生活离不开具体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西藏地处青藏高原,气候高寒恶劣,自然灾害频仍,如何在艰难的自然环境中生存,是藏族人面临的最大考验。远古时期的藏族人无法理解严酷多变的自然现象,他们相信大自然与人类一样,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繁复的神灵世界,也由此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西藏生态文化传统。自然界的“神灵之多有如恒河沙数。天地间神鬼攒动,层次分明,各司其职,不相统属,但为特定地域及特定人群互为所属”。这种独特的神性自然观,深深地渗透进了藏民族的血液与思维方式中,不仅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山川、河流、湖泊、树木、花草、石头等是有生命和灵魂的,动物也被赋予了灵性,是与人平等的生命主体,具有人的品格。正是这种对大自然原始朴素的认知,成了藏民族生态意识形成的根源。
藏族民间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藏族史诗、神话以及民间传说记录了藏族先民们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愿望。“他们从一落地起就生活在了神话和传说的世界里。他们生活在不断的提醒中,他们被有意无意地一再告知,每一株花草,每一个生灵都有其生存的独特意义。”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识,“史诗中体现出藏族先民崇拜自然的宗教观念,以及人与自然生态一体化关系的哲理认知,将自然融入到人类的道德关怀范畴之内,呈现出了藏族独特的生态平等观。”
藏民族朴素的生态意识及藏族民间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作为传统文化因子传递、延续到了西藏当代作家的文化审美意识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态意识。
(二)社会严峻的生态危机对西藏当代文学生态意识的激发
作为文学潮流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其产生、发展的主要动因,是当代社会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文学作品中的生态意识其实是作家的生态危机忧虑在创作中的必然反映。现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转型过程中,大自然被“祛魅”与客观化,不再有神性与灵性,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神秘互动亦不复存在,大自然成了人类征服与利用的对象。因而,人类可以对大自然无限度地扩张和索取,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与人文精神问题。相较于祖国内地,西藏的现代化起步比较晚。但正因为起步晚,发展速度快,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才更为剧烈。也由于有了国内其他地区的前车之鉴,青藏高原的自然生态问题与文化变迁才更为引人注目。
西藏社会在追求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也越来越面临着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的严峻现实。面对这一严峻现实,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传统的西藏当代文学必然会表现出浓厚的生态意识。阿来长篇小说《空山》以机村独特的藏族传统文化为背景,通过一个小村庄的生活史,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空山》所描写的是一个破除禁忌的、“祛魅”的时代。当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禁忌被破除,曾经不能砍伐的森林可以被砍伐,神圣的寺院可以被摧毁,森林的保护神色嫫措湖可以被炸毁,人们不再有珍爱与敬畏之心,也没有人愿意遵守古老的乡规民俗和禁忌,一切所谓的封建迷信都被破除了。正是无节制地狩猎导致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被打破,无节制地大规模乱砍滥伐森林,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危及生命,土地被埋,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本,动物失去了家园。人与自然的关系彻底失衡,进而导致人精神的失衡——人心险恶、贪婪。除了钱,人们的心中再也没有信仰,曾经那些美好的东西都失去了。阿来把机村人的伤痛——不仅仅是机村,而是普遍的中国基层老百姓的伤痛——揭示出来,引人深思。次仁罗布小说《长满虫草的心》也向读者揭示了消费社会所导致的人心变异。在一个以金钱为主导的社会中,世态炎凉、人心不古是必然结果。社会严峻的生态危机刺激了文学生态意识的迸发,也必然体现在西藏当代文学中。
四、西藏当代文学生态意识的文化建构意义
西藏当代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是西藏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和意识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它对民族文化优秀成分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传承作用,这是西藏当代文学生态书写的一个重要作用。同时,生态意识在西藏当代文学中的书写与开掘,对我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西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在西藏当代文学中得以承继,在客观上起到了环境保护的作用。千百年来,藏民族就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呵护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生灵。诚如海德格尔所说:“人不是存在的主人,人是存在的看护者。”“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人类与大自然都具有主体性,只有继续维护人与大自然的适当关系,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共同繁荣。
其次,西藏当代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有助于反拨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意识”。当代生态危机的发生、蔓延,根源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文化思想观念的长期存在。当代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产生、发展的现实目标就是反拨、纠正此种以“人为中心”,蔑视、占有自然万物的文化思想观念。人类社会的发展现实告诉我们,把人从大自然中剥离出来,造成人与大自然的对立,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已经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对此,诗人于坚曾感叹:
人类骄傲地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处置一切的生物,世界是人的,不是狮子、老虎、豹子、大象、鲸鱼和石蚌的,这种理念深深地植根在人类的意识中。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孤独得很,人类的暴力统治着整个自然界,人类经常以奥斯威辛的办法对付自然,这孩子接受的就是这种天经地义。我时常会感觉到自然界对人类的恐惧,它们惟一的反抗就是失踪、消失、绝种或者成为可怕的泥石流。
如何从源头上扭转当下的生态恶化趋势,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曾经在此’的诸神惟在‘适当时代’里才‘返回’;这就是说,惟当时代已经借助于人在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方式发生转变,诸神才可能‘返回’。”诸神返回的关键点在于人,“生态危机从根本上说乃是人性的危机,是人类生活方式选择上的危机。文艺的功能从来应是治‘本’的。只有作用于人性这个根本,塑造人格精神,环境问题以及其他自然生态问题才能真正解决。”从这一点上来说,西藏当代文学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恰恰是作用于人,促进人对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塑造人的精神品格。在此意义上,西藏当代文学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具有深刻的文化建构意义和价值。
最后,西藏当代文学中的生态意识不仅仅是一种审美因素,其现实功用也不只是为了纠正此前错误的思想观念,其最终目的是在改变人们观念意识的基础上,引导人们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藏族先民的生态意识与生态智慧在西藏当代文学中得以承继,对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化建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原刊于《西藏当代文学研究》(第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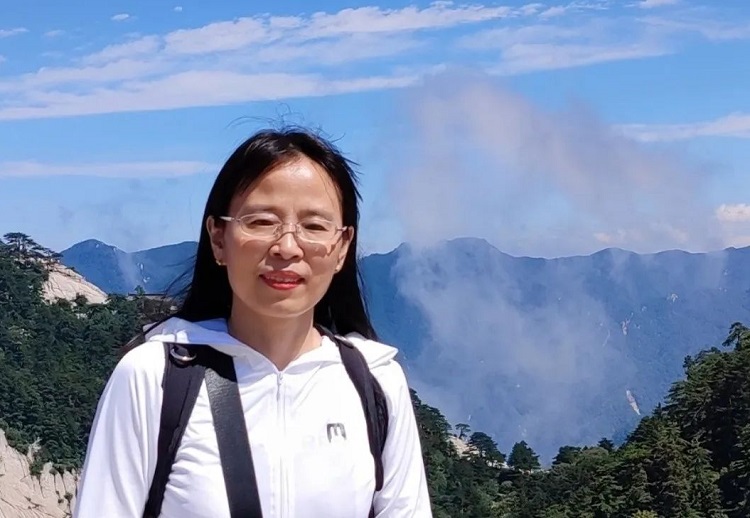
卢顽梅,女,陕西礼泉人。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当代藏族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