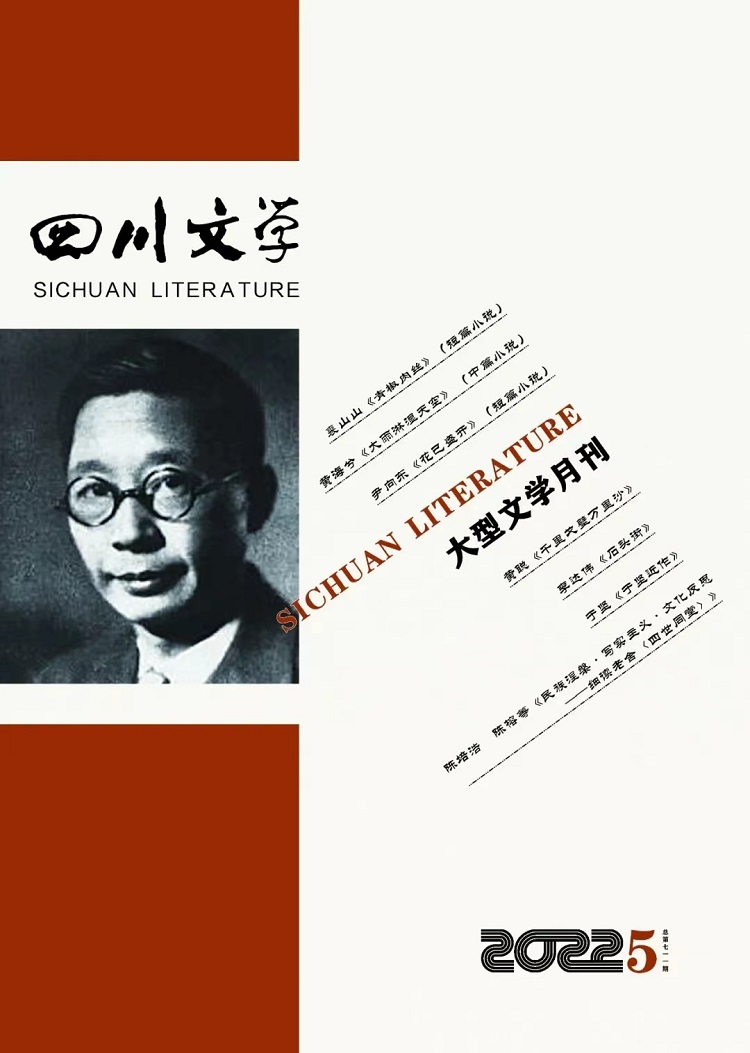
卓玛年轻时是康定的一枝花,她在舞台上用纤细姣好的形体展现出各种意想不到的美。这片土地的文化像窖藏千年的酒,不经意在她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间飘散出厚重甘醇的香味。她是歌舞团的台柱子,每个舞蹈只要她参演,便有灵魂。只是正值她舞蹈巅峰时,却结婚怀了孩子。歌舞团团长憋着一口闷气,寄希望于她生产后重回舞台,虽不比巅峰时期,也比别的演员多些风韵。但卓玛不这样想,为方便照顾孩子,她从歌舞团调到工作相对轻松的群众艺术馆,成为一个舞蹈编导。在送别她的晚宴上,歌舞团团长端着酒杯敬她,抑制不住心里的悲愤,直嚷着:“你这是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卓玛不语,只以微笑化解。她虽离开舞台,没想在编导这行,却又做出成绩来,她编导的节目先后获得省级和国家级奖项,她的事业再一次走向高峰。周边地区,乃至其他省也都慕名请她去当一些重要节目的总导演。谁也没想到在这顺风顺水的路上她再一次紧急刹车,办理了病退手续。这一次,连最好的朋友也不理解她的行为,不过卓玛只有淡淡一句话:“还不是为了孩子。”
卓玛病退没多久,李默也退下来。之前他已在农牧局担任副局长,下一步很可能就坐上局长的位置。这节骨眼他退了下来,熟悉他们夫妇的朋友都说:“这两口子的一生都只为孩子。”也难怪,他们只生了一个孩子,叫李小满。
他们病退,只因李小满上高中。小满是卓玛和李默夫妇的骄傲,初升高时,两口子咬咬牙,亲戚那东拼西凑,加上贷款,在成都买下一套二手房,目的就是让小满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小满在康定时,成绩一直好,刚到成都,学习环境和学习水平等因素,让小满在班上排名靠后,乃至卓玛和李默一度觉得到成都来是个错误。不过小满自觉,成绩在班上掉下来后,他没气馁,更加努力,父母请外教培训,无论学什么,他都不拒绝。到高二时,他的成绩已进入班上前十。临近高考这一学期,学校安排的模拟考试非常多,每一次成绩出来,小满都有进步,直至冲入前五。
卓玛和李默把房子买在武侯祠一个小胡同里。房是老房,小高层,他们在三楼。这房当初是单位的福利房,没环境,也没什么设施,从外表看,显得破破烂烂,与周边的高楼大厦相比,像一只被踩扁的蟑螂,暂时没被扫走。就这样一套房,花掉卓玛与李默的所有积蓄,还欠债。他们搬进房时,感叹成都就是成都,这样破烂的一套房,要价还那么高。不过他们买的是希望,望着那些巨人般的大楼,那些环境一流的小区,他们相信要不了多久,儿子小满从大学毕业,就能实现。因此他们在小胡同的破楼里住着,陪伴小满学习,十分幸福。
学校离住的地方不远,骑自行车也就十多分钟。学习紧张,小满也起得早,卓玛和李默总想把小满照顾周到,等他们醒来时,小满却已出门去学校。中午小满不会回家,食堂里吃完饭,就回教室复习,困了,趴在课桌上睡。晚上还有自习,通常将近十点,小满才会回家。两口子做好吃的,会等小满回来一块儿吃,他们的晚饭因此真的很晚。李默习惯喝二两泡酒,卓玛便陪他喝。再好吃的东西,小满三两口吃完,就回寝室,继续复习。两口子看着懂事的儿子,连劣质泡酒都变得像茅台一样香醇。只是整个白天,小满不回家,他们有些无聊,不过,也很快找到打发无聊的方式。这个小胡同,虽然隐藏在城市的角落里,但烟火气十分浓,想吃什么都有,消费比康定便宜许多。俩人不再自己做饭,早晨出门,随便吃点稀粥或豆浆,然后各奔东西。李默爱去的茶房,下棋的人多,能找到水平相当的对手。卓玛去的茶房,则全是麻将,都生活在小胡同里,麻将自然打得小,只以娱乐为重。到中午,俩人在街上随便吃点,抄手面条,什么都可以。吃完之后,回家小憩,再去茶房。一天的重中之重是夜晚,两口子上街买菜,估摸着时间把饭菜做好,然后等待小满回家,像这一天,所有的希望,才从夜晚刚刚升起。
卓玛和李默病退后的生活便是这样。病退那年,卓玛四十五岁,李默四十八岁,到小满高三,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都变了模样。身材姣好的卓玛,如今横向发展,肚子和腰上的肉像塞满棉花的小枕头;脸也圆了,只剩一双大眼睛还有些昔日的风采。过去一块儿跳舞的朋友来成都出差,约着吃饭,一见卓玛,没人敢认,直问:“你是不是肿了?”卓玛只笑,没半点后悔的表情。对方便说:“好在你儿子争气,是真正的祖国花朵,考个清华北大没什么问题。”这时候卓玛的笑里才流出幸福。
李默的肚子也鼓凸起来,头发不甚打理,这翘一绺那缺一角。朋友们见他,说他成了真正的油腻男。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在过去,和朋友一块儿,无论卓玛还是李默,都开朗豪爽,尤其是李默,酒必喝至酣处方得散场。现在,他总看时间,到晚上八点必走,酒则最多只喝二两,任谁也没办法多劝进去一点。渐渐地,朋友们来成都也不再找他们。
临近高考,李小满状态非常好,他保持全班前五的成绩,等待高考。学校也放了假,让学生在家自习。
自从小满放假,卓玛和李默很少出门,除开买菜,他们都待在家里。李默把每天三顿饭安排得既营养又好吃,小满只在吃饭或方便时走出他那间屋,其他时间都紧紧地关着房门。卓玛和李默无事可干,打开电视,怕声音吵着小满,便开成静音,俩人在无声的电视节目中消耗时间,他们甚至不敢大声交谈,有事要说时,也只是耳语。整个屋子内部都安静,但外面的声音没办法阻止,虽禁了喇叭,各种声音仍纷至沓来,胡同内是吆喝声,卖冰糖葫芦的、收旧家电的、清洗抽油烟机的,会在不同时段响起;胡同外的声音更大也更混杂,刹车声、轮胎摩擦路面的沙沙声,间或响起的警笛、救护车的呼叫以及救火车的长鸣。外面的声音混杂成一个庞大的固态,针刺不过。这事夫妻俩不能解决,只得面面相觑。好在这些无法影响小满,他从不抱怨,临近考试,他甚至连交谈都越来越少,除开必须交代的说两句,别的事他都不言语。
离考试只剩下三天时间,卓玛和李默感觉花已盛开,只待结果。等考完试、分数出来、填好志愿、录取通知书送达,李小满就是那颗高枝上的果子。卓玛和李默只负责把每顿饭做得更科学更有营养就行。
中午,有炖鸡、炒木耳、凉拌西芹、炝炒油菜。菜做好摆上桌,卓玛去小满寝室轻轻敲三下门。她不多敲,小满会听见。如果他还没做完模拟试题,就不会走出寝室,他们只好安静等待。今天尚好,卓玛刚敲了门,还没走到沙发边,小满就把门打开。卓玛高声说:“开饭,小满出来了。”
李默忙去厨房盛出三碗饭。小满接过饭,坐到餐桌边,只管埋头吃。卓玛和李默静静看着他,小满有一米八的身高,这点像李默。一双大眼睛和高挑的鼻梁,长出了藏族人的特点,只是皮肤有点苍白,明显缺乏日照。夫妇俩满意地看看小满,才端碗吃饭。小满不说话,他们也不出一点声音。小满吃饭快,桌上的菜也都吃,三两口吃完,扯张卫生纸抹抹嘴,便站起来,他没走回屋,直接走向大门。卓玛和李默相互看看,卓玛亲切地说:“儿子,晚上想吃点什么?”
通常,小满会说随便,这会儿他在门洞里回过头,看看父母,说:“红烧牛肉吧,我出去逛逛。”
卓玛和李默连连点头,李默说:“要考试了,绷太紧也不行,得放松,出去好好玩,需要钱不?”
小满摇摇头,拉上门出去。卓玛忙站到窗边,她看见小满穿着牛仔裤,还有一件橙红色印了一行英语的T恤,他清瘦高挑地走过胡同,向外面走去。
小满刚走,李默忙去冰箱里拿出牦牛肉解冻,小满喜欢牦牛肉,他们因此买了许多来冻着。
卓玛说:“儿子越长越帅气。”
李默说:“可不,也不看看他爹是谁。”
卓玛坐到李默旁边说:“你自己照照镜子吧,你是圆脸,小满的脸可不圆,你眼睛小成这样,还是单眼皮,小满的眼睛很大,眼皮也很双,再说鼻子,你的鼻子可不像他那么高挺。除了神态,偶尔的神态和你像,别的都不像。”
李默说:“我当时找你,就想到这点,混血的孩子很多都特别帅,有一种异域的气质,所以小满现在长成这样,他的眼睛和鼻子,特别有藏族人的味道。”
这话让卓玛高兴,她开心地笑起来,去收拾碗筷。
小满不在,两人便窝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边躺一个。看好一会儿剧,才发现声音依然关着,卓玛说:“我们都习惯看无声电视了。”
李默笑着把声音打开。平日里,看无声的电视,他们却睡不着,耳朵敏锐地捕捉小满房里的动静,这会儿电视声极响,又是一部抗战剧,爆炸声、枪声不时响起,俩人却睡得极沉,呼噜声一个赛一个。睡到下午,卓玛最先醒来,电视正播广告,看时间已到五点,忙摇醒李默说:“怎么睡到五点了?你说好下午做红烧牛肉的,快点做吧,不然牛肉烧不软,我看看小满回来没。”
李默揉着双眼,先把电视关成静音,然后半梦半醒地跑向厨房。
卓玛蹑手蹑脚来到小满寝室门边,先将耳朵贴门上听了听,又轻轻推开门,这才呼口气大声说:“小满还没回来。”
李默说:“快回来了。”
李默烧牛肉,卓玛去菜市买些新鲜蔬菜回来,为保证各种营养搭配,每顿的蔬菜都不同,而且都新鲜。卓玛把蔬菜准备好,等小满回来现炒,这时候已是六点多。卓玛看看天色,天气晴好,但更闷热。
“小满怎么还不回?”卓玛说。
“他难得出去玩一次,时间也还早,不用操心。”李默说。
红烧牦牛肉的香味弥漫在整间屋时,天已黄昏,卓玛站在窗边看了看说:“怎么还不见踪影?”
李默说:“估计遇见同学,耍开心了。”
卓玛说:“我打个电话问问。”
李默说:“算了,再等等,小满懂事,我们不用打电话催。”
俩人不再说话,见天一点点黑尽,城市的各色灯光占据了夜晚。
卓玛说:“我必须打电话了。”
李默没应声,他也焦急起来,见卓玛拿出手机拨通,铃声却在小满的寝室里响起。
俩人跑进去,看见书桌上有做了一半的英语试卷,手机就放在试卷边。
卓玛说:“他没带手机,怎么办?”
李默正想说什么时,他的手机响起来。李默接电话,没听两句就往厨房冲去,卓玛紧跟着他,见他关掉火,嚷着:“快走,去派出所,小满出事了。”
卓玛的心脏顿时狂跳起来,问:“出什么事了?”
李默边跑边说:“不知道,电话里没说。”
卓玛呼喊起来:“天啦,小满不会受伤了吧?”
他们跑出胡同,李默伸手拦出租,上了车,卓玛手捂着胸,不停催促司机开快点。
司机脾气好,只回应说:“超速了,我要被罚款。”
好不容易到派出所,李默还在付车费,卓玛已下车冲进去,见到警察就问:“小满呢?我儿子呢?”
警察见她神色紧张,问:“有什么事?”
李默赶来说:“是你们打电话叫我们来的。”
听见这话,几个警察都过来了,一个警察问:“你们是李小满的家属?”
另一个警察说:“这是我们所长。”
李默说:“所长好,我们是李小满的父母。”
卓玛说:“小满呢,他在哪里?”
所长说:“你们别着急,我们马上出发,小李,去开车。”
李默说:“去哪里?”
所长说:“到地方就知道了,请你们配合。”
年轻的警察开来一辆面包警车,所长坐前排,李默夫妇坐第二排,还有两个警察坐在他们后面。车鸣着警笛,向外面驶去。
卓玛说:“究竟去哪里?”
所长再次说:“请你们配合。”
一时,车里沉默下来,只有警笛刺耳地在头顶呼叫。有一瞬间,卓玛想到前几天,小满在寝室里复习时,她埋怨城市的声音,尤其是各种警笛,说不清什么时候就猛然响起,嘶鸣着穿越大街。那会儿她想,一座城市,哪有这样多的火灾、需要求助的病人和急需抓捕的罪犯?此刻,坐在警车上,她明白警笛就是这样响起的,一个电话,他们也不知道什么事,警笛就响起来了。这还是她和李默有生以来第一次坐上拉响警笛的警车。像电视剧通常演的那样,卓玛总觉得警车终将把他们拉到看守所,在那里,他们将看到穿着条纹狱服的小满,卓玛的心悬起来,掉不下去。
虽已是晚上八点多,大街上车仍多,好在有警笛,各种车辆纷纷避让,车穿越大半个成都后,向郊区驶去。卓玛不愿意再说话,有一会儿,她心里颤颤地希望警车就这样开下去,永不到目的。
车在郊区路上又开了半个小时,驶进一个大门,卓玛和李默满怀心事,没注意大门上的招牌。大门内很宽敞,环境也好,几幢房子错落有致地散在绿化树林间,一点也不像监狱。警车绕来绕去,转了好几个弯,才在一幢房门前停下来,警笛声终于喑哑。所长下了车,李默和其他警察都下了车。大厅门前,有工作人员听见警笛,已在那里等候。李默和卓玛顾不上看四周,只觉得这里的环境很熟悉,似曾来过。
所长对工作人员说:“这是家属,你带路辨认吧。”
卓玛紧张地问:“辨认什么?”
所长说:“请控制情绪,配合我们的工作。”
这话似有魔咒,卓玛再次不吭声。
工作人员很客气地比了个随他走的手势,一行人便紧紧跟在他后面。进门是个大厅,大厅内还有许多小门。工作人员打开其中一道门,他们都进去了。卓玛和李默感觉房间里很凉,看见房间墙壁全排列着铁匣子,每个铁匣子外都有巨大的把手,整齐划一。
李默颤着声说:“究竟要辨认什么?”
卓玛紧紧抓住李默的手臂。
所长这时才说:“下午接到一起报案,在向阳小区里,一个学生坠楼而亡,有学生辨认出是李小满,这才想法找到你们的联系方式。派出所里怕你们过于激动,所以直接到火葬场,请你们辨认一下。”
卓玛嚷着:“不可能。”
李默声音颤抖,问:“在哪里?”
工作人员走向一个铁匣子,正准备拉开时,卓玛尖声叫起来:“天啦,那不是小满的衣服吗?”
就在铁匣子下的地面上,放着一条带血的牛仔裤和橙色的体恤。浸血的体恤,橙红的颜色更深邃。卓玛就是这时候晕倒的,她倒在冰凉的地上,让警察们一阵忙碌。
等她醒来时,看见自己躺在医院里,打着吊瓶,李默伏在床边,像睡着了。
卓玛小声喊:“李默!”
李默抬起头来,他此刻的样子让卓玛吓一大跳,他的白头发忽然增加不少,面色黝黑,像熬过许多夜晚,双眼又红又肿。
卓玛说:“怎么会在这里?小满回来没?你还炖着他爱吃的红烧牛肉呢。”
李默抓住卓玛的手,轻轻摇了摇说:“卓玛。”他说不下去,眼泪不停地滴落。
卓玛像回忆梦境一般,脑袋里闪出一些画面,他们坐在一辆警车里,那辆警车不停地向前驶,警笛在头顶特别刺耳。她颤着声问:“你辨认了?”
李默的脑袋又伏到床上,他点点头,哭出声来,双肩不停抖动。卓玛沉默一会儿,她用力抓住李默的手,李默抬起头来,用袖口抹抹眼泪,惊异地看着卓玛,她脸上除了愤怒,没有任何表情,原本就大的眼睛此刻瞪得老圆,眼白已布满红色的血丝,她用通红的眼睛瞪着李默说:“李默,你必须查出是谁害了孩子,必须抓住凶手报仇。”
李默被卓玛的表情吓着,他虽然是汉族人,一直在康定生活,也很多次听说过康巴人复仇的故事。那些故事里世代仇杀,为了复仇不惜一切代价,每一个仇杀的故事既血腥又壮烈。听得多了,他不太相信,只觉得这些故事口口相传,经过无数人的加工和夸张。但此刻,他看见卓玛的表情,她还只是个女人,已让他相信康巴地区复仇的故事有多真实。如果揪住小满背后的人,卓玛会毫不犹豫复仇,哪怕手中没有利刃,她用头颅、用眼睛都会取对方性命。
李默身上的血性被点燃,他短暂地忘掉悲伤,轻轻拍拍卓玛的肩说:“你放心,我已给亲戚们打了电话,他们正连夜从康定赶出来,等他们来陪着你,我会去弄明白这背后的一切,哪怕靠自己的力量,我也要挖出真凶,亲自动手复仇。”
卓玛点点头,不再言语。
卓玛和李默一夜未眠,天刚蒙蒙亮时,卓玛的大哥扎西开车和妹妹青措赶到,青措哭成一团,扎西一句话也没有,红着一双眼睛,眼里都是复仇的火焰。
亲人到了,卓玛要立即出院,去火葬场陪小满。李默让再等等,说自己的弟弟李畅还没来。
卓玛说:“李畅就在双流,来这里不过二十分钟,我哥哥妹妹连夜从康定赶来,他为啥还不到?”
李默的表情很复杂,既抱怨又怀疑,说:“我再打电话问问。”
他拿出电话,拨通了,对卓玛说:“是我迷糊,以为给弟弟打了电话,结果还没打。”
打通电话,等了半小时,天彻底亮开,李畅终于到达,也红着一双眼睛,能看出他边开车边掉了一路的泪。他们办完出院手续,走到停车场,李默说:“去火葬场。”
李畅看着众人,红着眼说:“你们怕是没吃东西吧,火葬场那边没什么东西吃,我们在附近找个馆子,吃点早餐再过去,后面还有忙的,不吃东西可撑不住。”
李默说:“我们从昨晚就没吃。”
卓玛想着那锅满溢香味的红烧牛肉,眼圈红了红,但没掉泪,她说:“走吧,吃东西去。”
火化在第二天早晨进行,还有一整天的时间。他们到火葬场没多久,卓玛就催促李默,让他去调查真相。李默由弟弟陪着,前往派出所。扎西和青措则在火葬场一直照应她。他们租下一个小会客厅,好在火葬场都是一条龙服务,什么都有。按藏地规矩,这一夜得守着,虽然小满只是孩子,又是凶死,不便通知朋友,但兄妹之间,也不能怠慢。青措明白这个,与人联系,在小客厅里摆下酒菜。他们想与卓玛交流,除了说复仇的事,别的卓玛都不回应,见姐姐精神并不萎靡,反而有些亢奋,她不哭闹,甚至不掉一滴眼泪,青措也安了些心。
当夜,李默坐弟弟的车回到火葬场,一见李默,卓玛眼睛一亮,问:“找到凶手没有?”
李默摇摇头,颓然坐下,他比早晨更苍老,脸也更黑了些。
青措放好碗筷,斟上酒说:“姐夫,快吃一点,忙一天估计也没吃东西。”
李畅说:“就今天中午吃了点抄手,真是饿了,大哥,你先吃点。”
李默只喝酒,并不动筷子。
卓玛问:“这一天,你们都忙了些什么?”
李畅看看她,欲言又止。
李默说:“主要是配合警察查找线索。”
一条命案,不是说破获就能破获的,卓玛明白,说:“快吃点东西吧。”
扎西喝下一杯酒,红着眼说:“一个人不能说没有就没有了。”
当夜,是怎么睡着的,卓玛没一点记忆,她睡在漆黑一团里,连梦也没有。前一晚大家都没休息,这会儿,各自东倒西歪在椅子上,等工作人员叫醒他们时,天又亮开。
告别仪式在一个小房间里,小满经过整容,安安静静躺在玻璃棺里。临跨进门那一刻,卓玛退了出来,她不想看见小满此刻的样子。
青措说:“姐不想进去就不去吧。”
大家点点头。
她站在门外,看见巷道里是一溜告别厅,活到这一把岁数的人,卓玛也来过火葬场很多次,送别老人、亲戚和朋友。她奇怪乘警车到这里时,竟然不知来的是火葬场。早晨的火葬场特别忙碌,像此刻依次排列的告别厅,每个厅都有人在告别,有的厅人多点,有的人少点。成都就是成都,连火葬场都如此热闹。人们哭哭啼啼,此起彼伏,工作人员带着夸张和职业性的哭腔主持告别仪式,反倒让仪式不再庄严,有点滑稽。
等小满的告别仪式完成后,大家出来。
青措再一次把双眼哭红,她搀着卓玛的手臂问:“姐姐,你真不再见小满最后一面了?”
卓玛摇摇头,脸上现出异样的坚定,她们回到会客厅,男人们则前往火葬室等候。火葬时间不长,一个多小时,李默手捧骨灰匣,由扎西和李畅搀着回来。
“走吧。”李默说。
他们向停车场走去。
回到家里,李默刚安顿好骨灰匣,听卓玛说:“闻到没有?红烧牛肉的香味,这时候都还没有散,我们前天就是在炖牛肉等小满回来时,接到的电话。”
李默哭起来,像一头老牛,声音嘶哑沉闷。他一哭,青措也跟着哭。只扎西几拳砸在沙发上,像远方一串沉闷的滚雷。
卓玛说:“你们别哭了,我要自己去找到凶手。”
说着,她站起来准备出门。大家顾不上哭,都上前拉住她。
李默说:“等她去吧,她自己不看见,永远过不了。”
扎西说:“我和卓玛去。”
青措说:“我也去。”
李默说:“我们都去。”
李畅开车走前面,扎西的车紧跟着。这一次他们没去派出所,驶向了市公安局。李畅领着大家,乘电梯到五楼。
刑警队队长是个中年人,一见李默,说:“怎么又来了?还有疑问?”
李畅说:“孩子的妈妈要来看看。”
卓玛直接问:“找到凶手没有?”
刑警队长说:“孩子父亲没给你讲明情况?”
李畅说:“我哥不愿相信那是真事,也不敢给嫂子讲,帮帮忙。”
刑警队长说:“遇上这样的事,难免会不相信。”他带卓玛来到一台电脑前,“我们前天调取了各种监控,你自己看看吧。”
一个年轻的警察操作,卓玛看见小满出现在屏幕上,他穿着橙色的体恤和牛仔裤走出胡同,走上大街后,四处张望一会儿,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走过一条街,在一个广场边,他坐到椅上,看着面前人来人往,足足坐了两小时,然后他上了趟厕所,走出广场进入一条小街。那条街上有各种餐馆和小吃,在每个餐馆前,他都会驻足看一会儿,他双手背在身后,神情像一个爱看热闹的老年人。后来他到了向阳小区,小区大门装修得十分堂皇,小区内的绿化也似公园一般。小满在门前看了一小会儿,跟着向里走去,保安和过往行人都没有太注意他。他一直向小区里边走,走到小区角落的一幢高楼前,他又在楼侧的花坛边坐下来,抬头望着高楼,大概有四十分钟的时间,那幢楼有人出来,楼道的门开了。小满跳起来,在楼道门即将关闭时,一把拉住。小满进入楼道,按了向上的电梯,电梯里也有监控,小满乘电梯到达最高层,面无表情地走向通往屋顶的楼梯。屋顶及楼梯间都没有监控,年轻警察将监控转入地面,那时候已快到六点,卓玛出门买菜,李默则正烧牦牛肉。监控里很安静,没有人来往,大概十多分钟后,一个人影划过监控,跌到地上。
卓玛转过头,不愿再看。
刑警队长说:“你看见了,没人去屋顶,只有他一人上去,他是自杀的。”
卓玛没有说话,一时显得很虚弱,青措搀住她,向门外走去。回到家,青措和李畅去厨房做饭,说:“吃点东西,再好好休息。”
一直沉默的扎西陪李默和卓玛坐在沙发上,他看看李默,说:“这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说着,眼泪淌出来。
李默又跟着哭,卓玛头靠在沙发上,脸上没任何表情。
青措和李畅热好饭,卓玛说:“你们吃,我这会儿一点不饿,吃不下。”
李畅说:“嫂子,多少都得吃点。”
卓玛不再争论,机械地坐下。他们围在餐桌前吃饭,那锅红烧牛肉摆在桌上,青措替她夹肉时,她像躲老鼠一般避开了,只埋头扒饭。扒几口,她放下碗,看着众人问:“你们听见那声音没有?”
扎西问:“什么声音?”
卓玛说:“小满从楼顶掉下来的声音。”
李畅说:“没有声音,监控里没有声音。”
卓玛说:“我听到了,嘭的一声,肉体撞地面的声音很不一样,又大又沉闷。”
李默质疑地问:“真有声音?我怎么没听见?”
青措说:“我看监控时,也没听到声音。”
卓玛说:“我听到了,那声音就在耳边。”
一时都无话可说,大家担忧地看着卓玛,她坐在餐桌边,不再吃饭。沉默好一会儿,卓玛又说:“原来凶手是他自己。”她说这话时,声音低了许多,叹息一般。
大家吃饭,都不敢发出声音。吃完饭,青措正准备收拾碗筷,卓玛再次说:“李小满是怎样想的呢?我像不认识他了。”
李默说:“小满成绩好,面对高考也不应该有这样大的压力啊。”
李畅说:“现在的孩子,真是不懂他们。”
扎西小声说:“早知这样,从小就让他在牧区放牛,还不会出事。”
在大家讨论之时,卓玛站起来,也不和任何人招呼,直接向寝室走去。
李默去看了看,小声说:“她睡下了。”
李畅说:“这两天嫂子又累又伤心,好好睡一觉,一切都会好的。”
吃过饭,青措去小满的房间休息,三个男人在沙发上倒下,鼾声不一会就响起。所有人都睡得很沉,天都黑尽时,青措醒来,把三个男人叫醒。大家商议一会儿,明天一早,按传统习惯,把骨灰送回康定的寺院里超度,再去河口进行抛撒。
青措要去厨房做饭,李默说:“明天要回,懒得做饭,我们去外面吃,喝点酒解解乏。”
说着,他去寝室叫卓玛。卓玛跟在他后面出来,也不看大家,直接在沙发上坐下。
李默说:“兄弟姊妹们累了几天,我们出去好好吃顿火锅,喝点酒,明天回康定。”
卓玛仍不回答。大家穿衣准备出门,她也不动。
青措说:“姐看上去不太对头啊。”
众人回头看卓玛,只见她眼中没有焦点,眼神散乱。
李默走过去,蹲在她前面,用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她也没任何反应。
李畅说:“我之前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出事后,嫂子没掉一颗泪,那时候她一心想找凶手复仇,这会儿,支撑的弦断了。”
扎西说:“走,去医院。”
李畅在百度地图上搜到附近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初步诊断,确定患了精神病,详细情况还待后面观察。好在精神病专科医院不用家属陪伴,病人的护理全由医院安排。办好入院手续,护士接手照顾,众人才有时间去吃饭。
原本认为卓玛是气急攻心,治疗一阵,也就好了。那段时间忙小满的后事,直至将骨灰撒入大渡河中,李默才回成都。他去医院看卓玛,医生说她患了妄想症,虽然没有易怒、打人这些问题,但非常严重。她不认识人,没法交流,所以此刻探望她没任何意义。对她的一些行为举止,连医生也弄不明白。
透过隔离窗,李默看见一个大房间里,好些病人在里边活动,有病人坐着发呆,有病人与自己的左右手交谈,还有病人在一定距离内不停来回走动。李默看见卓玛,她穿着病服,坐在最角落的一张椅子上,紧张地看着眼前的人群,有人靠近时,她的手便做出阻挡的动作。平时,她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腿前,像抱着一个小圆球,又像捧着一束花。她要走动时,更为小心翼翼,一手前伸,制止别人靠近,另一手捧着虚无的圆球或花朵。李默觉得这些动作有点眼熟,但始终想不起卓玛比画的是什么。他叫她,她没反应,果如医生所说,看见李默时,她只当陌生人一般,眼光一扫而过,没任何表情。
回到小胡同的家里,李默才感觉孤独和难受。自从小满出事,到料理完后事,李默痛哭过,也把自己喝得烂醉,什么都不想。但他知道那时刻,作为一个男人,他必须硬撑。到卓玛生病,他更不能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哪怕是悲伤,也得深深藏着。这时候打开家门,家里安静得可怕,他坐在沙发上,感受到这个家已崩溃。他不开电视,什么也不想干,就那样坐在沙发上,直到天黑。天黑尽后,他才去开灯,想了想,走出门,去胡同里吃碗面条。回家后他躺到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也不知到凌晨几点,刚睡去,梦见小满在河水里喊冷,一时醒来,全身是汗。无法睡觉,他眼睁睁看见天一点点亮开,卖早餐的吆喝声从远处传来,他木讷地起床,口也不漱,只胡乱抹把脸,就出门,简单吃过早餐,他看着这条小胡同,监控里的画面就在脑中呈现。所有监控他看了不下十遍,小满出门后的每个动作他都铭记于心。他开始跟着小满的脚步走,走过大街,在广场边他也同样坐两小时,然后去厕所,哪怕没有尿意,也要进去。他重复小满的动作来到向阳小区,坐在小满曾经坐过的花台边。他没有进入电梯攀上顶楼,他怕一旦进去会控制不住自己,也从楼上跳下来。最初,他重复小满的路,是想知道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但他一无所获,他越来越不明白小满为什么要自杀。到后来,三顿饭李默都在外面将就吃,他习惯于重复一件事情,走小满最后走过的路,每次坐到花台边,他想走进电梯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每个夜晚,他几乎都失眠,一旦睡着,总有些噩梦让他一身大汗。
每个周末,他都会去精神病院看看卓玛,她没什么变化,除又增加一些新动作,动作的幅度更大,举手投足更像一个人安静地独舞。李默觉得这样也好,过去为小满,卓玛放弃舞蹈,现在虽然病着,她可以分分秒秒沉浸在独舞中。倒是医生每次看见李默,都会吓一跳,说:“你得照顾好自己,每一周时间,你的头发都看着白,精神也不好。”
又一个周末到来,李默看看时间,快到九点。每个周末,他都在九点准时出门。此刻,差五分钟才到九点,他为此竟然十分焦虑,他不愿意早一分或晚一分走出家门,他在家里看着手表来回徘徊。好不容易看见分针和秒针同时指向十二,他喘口气,也同时拉开了家门。第一次去看卓玛时,他打了的士。但后来,他已习惯坐公交,十二路公交车就在胡同口出去的大街上,坐五站,刚好到达精神病院前,下车步行不超过五分钟。李默手中拿着一元的硬币,站在公交站台边固定的位置。私家车、地铁和共享单车的普及,让等公交的人减了不少,只有一些执拗的老头、老太太仍习惯于公交。冬季到来,天空中厚重的乌云就压在高楼顶,成都的冬天潮湿阴冷,不过大街上的车辆依然繁忙。李默不怎么关注别的,只看着公交车驶来的方向。冷冷的微风吹来,李默满头的白发也懒散地飘了飘。等了十多分钟,贴满广告的公交车徐徐驶来。上车,投硬币,走到下车的门边。李默习惯站在这里,车到站后可以不慌不忙。他还习惯闭上眼睛,数着公交停车的次数,到第五次,睁开眼,医院就在前面。李默下车,他从兜里掏支烟点燃,不紧不慢地向医院走去。到医院门前,一支烟也刚好抽完,他将烟蒂扔进医院门边的垃圾桶,通过侧门进入医院大厅。这些都是他一成不变的习惯,他把时间掐得非常准确。
到住院部,主治医生看见李默,又吃了一惊,说:“李默啊,你头发基本全白了,人也越来越憔悴,我建议你立即看看病。”
李默摇摇头说:“我来这里不是看病的,我只看我老婆。”
说着,他向隔离区走去。医生跟在他身边,继续说:“你是不是长期失眠、焦虑,做事越来越程式化?”
李默转头看着医生,他双眼通红,眼里满是愤怒,他再次说:“我不看病。”
李默站在隔离玻璃墙外,按习惯,他将这样站着,站到十一点四十分,才准时离开。他看见卓玛也一成不变地坐在角落里,在医院这些日子,卓玛白了,也更胖了。
医生十分固执,李默发火他也没离开,他站在李默边上,等一会儿才说:“李默,你能不能把你亲戚的电话给我?”
李默想都没想,直接把手机递给他说:“找我弟弟,他叫李畅。”
医生刚把李畅的电话记下来,隔离室里就出现了混乱,卓玛忽然站起来,双手撑在后腰上,她呆呆盯着地面,像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流淌,然后大喊起来:“老公,你去哪里了?”她一叫,好些病人都跟着激动起来。护士、医生进去安抚她也无济于事。
随这呼喊,李默也激动起来,他对身边的医生说:“让我进去,我终于明白这些日子她在做什么了。”
医生质疑地看着李默,说:“你明白了?”
李默连连点头说:“你们都不知道,让我进去。”
医生打开隔离室的门,李默走进去,说:“老婆,我来了,你别慌。”
奇异的是,此刻卓玛仿佛突然清醒了,她紧紧抓住李默的手说:“你终于来了。”
在李默的指挥下,两个护士扶着卓玛来到房间,将她平放在床上,她双腿弯曲,脸上流露出幸福的神情。
医生问:“她这是在做什么?”
李默说:“还不明白?她要生孩子了,快准备啊。我前段时间没看出来,只觉得眼熟,她的动作总像抱着一个圆球,这圆球在不断长大,第一次怀孩子,她就爱这样捧着肚子,要生产时,也是羊水先破,她站着大声喊我,只是我没想到她又怀上孩子。”
护士们不知所措,只在边上默默观察他们。只有医生拿出手机,拨通李畅的电话。
卓玛平躺在床上,能看出她正努力生产,但情况不容乐观。李默焦急地站在一边,对护士和医生说:“你们出去,这么多人,怎么好生孩子?”
医生给大家使眼色,他们退出房间,只留下两个护士配合。也不知耽搁了多少时间,卓玛的表情看上去越来越痛苦,额头的汗珠开始密布。
这个虚拟的生产让医生和护士都束手无策,卓玛难产时的疼痛是真的,但他们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帮助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卓玛和李默,静观事态发展。这时李畅也赶来了,医生走出去,他们站在隔离室外,从这里,能看到房间里,李默站在床边,卓玛躺在床上,他们都在努力。医生简单地给李畅说了自己的判断,李默应该是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但这时候,没办法打扰他们。
卓玛越来越痛苦,如果任其妄想下去,可能造成新的伤害。医生们正准备介入,却见卓玛又平静下来,她看看平坦的肚子,双手像抱着一个大圆球,轻轻地抚摸,同时柔情地唱起一首家乡的山歌:
“孩子,不知经历多少轮回
你才来到我肚子里
这里是你温暖的巢穴
不冷也不热
你渴不了饿不了
一切都那样安适
只是孩子
此刻你将面对一个新世界
踏上一个新征程
你不要犹豫这世界冷漠
也不用害怕这世界多磨
因为你刚出去
就能看见两个活菩萨
那是你的爸爸和妈妈
他们将一直陪伴你长大”
她把这首歌唱完,李默和她同时欢呼起来:“生了,看,生了个儿子。”
李默手捧虚拟的孩子,不停地亲,说:“我们就叫他李小满吧。”
卓玛也站到一边,满脸慈祥,他们此刻的动作,像极了台上的双人舞蹈。
医生对李畅说:“你看见了,可以确定,你哥哥也患上精神病,我之前一直觉得他是抑郁,但从这会儿的表现来看,他和卓玛一样,是妄想症,这个我们得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检测才能最终确定。”
李畅看着幸福的哥哥和嫂嫂,脸上的表情轻松起来,他对医生说:“等他们一块儿住在这里吧,等他们在这里把孩子抚养成人。”
原刊于《四川文学》2022年第5期

尹向东,藏族,又名泽仁罗布,四川康定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在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一百多万字。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鱼的声音》、长篇小说《风马》。作品被选入《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多种选刊,收入《200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集》《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14短篇小说》《2001——2010新世纪小说大系生态卷》等选本。获过多种文学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