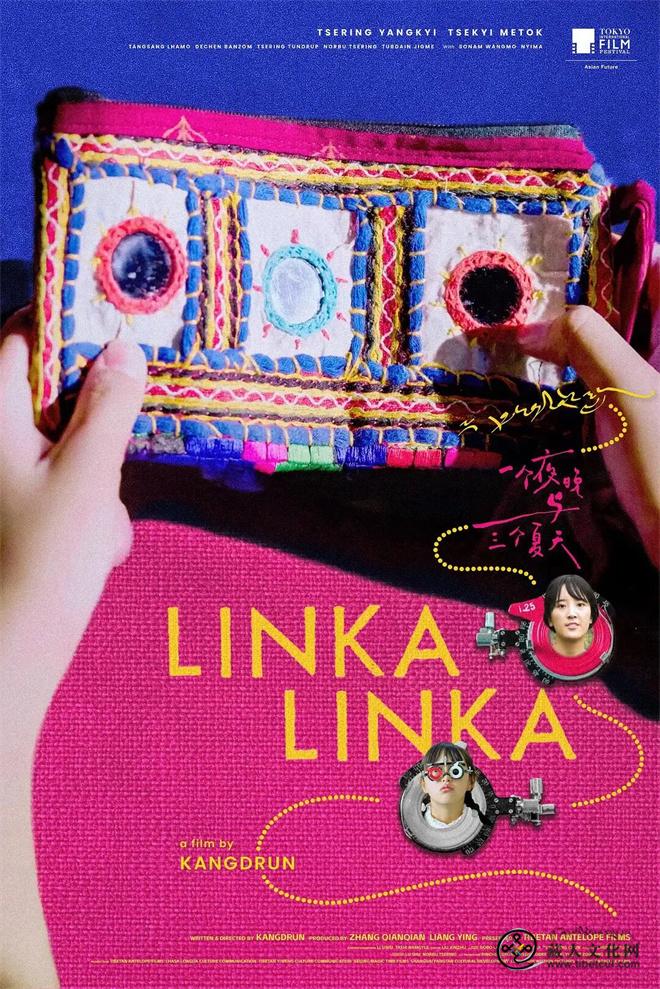万玛才旦导演
斩获台湾金马奖
「最佳改编剧本」

摄影/ 钟锐均
以及
以下
重磅采访长文
目前为止对「塔洛」
最棒、最有趣的解读
让你了解「塔洛」的一切

中国美术学院徐晓东副教授,在万玛才旦导演赴台湾金马奖征战之前,就《塔洛》的创作进行了一次电话访谈。
徐晓东:“塔洛”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
万玛才旦:“塔洛”大意为“逃离的人”。

徐晓东:塔洛在影片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背诵了毛泽东写于1944年的《为人民服务》,塔洛的腔调很特别,有诵经的感觉。您这样安排的用意是什么?
万玛才旦:是的,他背语录的腔调正是我们那边诵经的腔调。其实这种设置是有现实基础的。文革期间,很多藏人并不识汉字,要背语录,就习惯性地用平时诵经的腔调,完完全全地背下来。我觉得是那种腔调帮助他们记住要背的东西。我们小时候念书背语文课文的时候,也是用这种诵经的腔调。塔洛作为这部电影的主要人物,他身上有他那个年代的人的痕迹。主要体现在记忆上。他们的记忆里刻有一些终身难忘的东西。时间对他而言不是断裂的,他的生活一直处于一个相对封闭孤独的空间,所以说时间没让他发生太大变化。他的身上一直持续着那个年代的一些状态。

徐晓东:您主观上有没有将塔洛的经文上升为塔洛的信仰?
万玛才旦:不是我,是塔洛将“为人民服务”这语个录上升为了一种几乎跟信仰差不多的东西。那个东西对他来说印象太深了,在他的生活里就像信仰或者宗教一样。对他来说也许这是他核心的处世标准,自己所有的行为都以它来做衡量,在这点上跟宗教的作用实际上相差无几。就像佛教里的“十戒”一样,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都在约束着你,对人的行为方式起着一个规范的作用。塔洛做了好事,就觉得自己死后会重于泰山了,到最后,当他做出了一些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情时,就觉得自己死后会轻如鸿毛了。他始终有这样一个标准的处世观念。

徐晓东:第一场戏中,一开始,您把塔洛放在一个框子里,为什么做这样的构图安排?是否也起到引导观众视线的作用?他的走位有什么考虑?
万玛才旦:一方面,想要突出那个背景,和塔洛背诵的语录做个呼应;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调度上的考虑。
首先,他直接走过来,对着镜头背语录,其实就是对着观众背。背完之后,观众会发现他其实是对着所长背的。先把背景墙上那个“为人民服务”突出出来,再把他的状态啊、语调啊清晰地传递出来。构图上也是,希望引导观众视线,将他置于视觉的中心,这样基本上他的表情、情绪等一览无遗了。同时,也给后面的调度做一个基础。他背完之后,对所长说,我背得怎么样啊?然后所长走过来,两个人形成一个对应的关系。这个关系也是不断变化着的,一开始,他们是面对着面,走到那个炉子的左右,炉桶挡在他们中间。当一提到办身份证的时候,所长又回到了他自己的位置,搭起了官腔。这是他办公时所处的位置,他们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调度上讲,有这样一些设置在里面。

徐晓东:一开始出场的,除了塔洛,还有小羊羔。小羊羔戏份很足,您的角色设置中,小羊羔的作用和意义是什么?
万玛才旦:小羊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跟塔洛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一开始就把它带进来,让观众了解它跟塔洛那密切的关系。与此同时,也可以传递出塔洛的身份,第一个镜头观众就可以看出塔洛是一个牧羊人。而且,通过小羊羔,还可以反映出塔洛身上的一些性格特征,比如,他虽然高大,但也满怀爱和温情。另外,小羊羔与很多情节有呼应,起到铺垫的作用。剧情中,小羊羔的妈妈是被狼吃掉的,最终,小羊羔也被狼吃掉,这样就没有那么突兀。
一般我都不会安排一个很突然的巨大的转折,而会做些铺垫,比如用放鞭炮啊什么的说明狼的存在、威胁。在对话中也有所交待,塔洛说他们那个地方有很多狼啊,说狼很厉害啊什么的。还有塔洛说小羊羔的妈妈也是被狼吃掉了,说明狼很猖獗。包括塔洛那止不住的咳嗽,也是为这个人物专门设计的一个特点。比如他因抽烟犯咳嗽的毛病,只有喝白酒才能止咳。就这样一个细节也是为他后面喝醉了没有看管好羊群提供了足够的铺垫。
在电影里,小羊羔是不可或缺的,有这样一个角色和没有这样一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通过它,既可以传递很多的信息,也可以让整个故事充满细节,还可以打破、中断一些正在进行的事情,停下来喂奶什么的,有一种舒服的节奏感。所以,从每一个层面讲,小羊羔对整部片子都是有帮助的,用这样一个小的细节安排来贯穿始终,也可以起到一些隐喻的作用吧。

徐晓东:在某种程度上,小羊羔甚至是塔洛的一个化身吧?小羊羔被狼咬死之后,塔洛就有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做出违背他信仰核心的事情。就像小羊羔被狼吃掉了一样,塔洛这头羊也被一些不可控的外在力量像狼一样吞噬了。
万玛才旦:塔洛的命运的改变肯定需要一些其他的手段来辅助、推进,小羊羔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最后,塔洛能够下定决心出走,跟失去小羊羔、羊群被狼群袭击有很大的关系。有了这些细节,塔洛做出那么大的一个突破与转变,才有可信度。对塔洛这样一个人来说,是需要很多小的事情去撼动他的。
徐晓东:当悲剧性的事件将要发生时,羊群发出的声音不是写实的吧?
万玛才旦:对,稍微主观化处理了一点。塔洛给羊饮水的时候,他看着羊离去,然后起来一点音乐,但不是旋律性很强的音乐,对声音也稍微做了一个处理,从客观变成了主观。

徐晓东:片中出现的拉伊,是原来藏族就有的一些民间歌曲,还是您自己根据塔洛的情绪创作的?
万玛才旦:都是纯粹的民间歌曲,我先后听了很多拉伊,选择了一些对故事情节或者塔洛的情绪有帮助的,运用到片子里面。在原来的剧本中,塔洛想学唱拉伊,就请了个牧羊女教他,学一首,给她十块钱。后来还是把这个情节删掉了。因为我觉得,在山上时,塔洛一个人的状态比较好,不想让他遇见其他的人。这样更简洁一点,。有了牧羊女的存在,就对整体的气氛、塔洛的处境、他的孤独感都有所破坏。把这段删除后更符合塔洛的状态。
后来把他学拉伊的戏改了一下,变成通过听收音机来学。我们把原来录的声音做了处理,做成收音机的效果。塔洛通过收音机学拉伊,他记忆力强,学一遍就会了。

徐晓东:当塔洛把羊卖了去找杨措时,那个场景呈现的是镜子里的映像,观众看到塔洛与杨措被挤压在屏幕左面的三分之一处,将钱放在自己面前的桌上,一捆一捆拿出来,总共拿了16捆,这16捆钱将塔洛身体的映像几乎遮盖住了。这场戏的构图以及人物动作,您这样安排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万玛才旦:后面有一个调度,杨措走到屏幕的右面三分之一处,两人隔着一段空间,分处在两个边上。至于塔洛放钱的动作,我觉得就是他对爱情的表达,一种很直接的表达。对于他那样一个人来说,他所能够做到的最大的努力就是那样,除了那样他还能怎样呢?
关于钱放在哪个位置,我们肯定是做过很多测试的。既要表演起来自然,又要有力度。这个场景其实是省略了很多过程,把卖羊啊、拿钱啊这些省掉了,只是呈现了塔洛拿了钱一下子出现在杨措的面前,这样会有一个冲击感,无论是视觉上还是情感上,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对杨措是这样,对观众也是这样。我觉得杨措与塔洛之间要说有什么爱情的话,塔洛默默地将钱一捆一捆地放在那里的时候,杨措应该是有所感动的。所以她会说,你把小辫子剪掉吧,这样就没有人能认出你来了。我觉得在那一刻,作为一个女人,杨措对塔洛的行为是有所感动的,除此之外她怎么想就不好说了。当她剪掉塔洛的小辫子时,可能又变回原来那个杨措了。

徐晓东:您所塑造的杨措基本上是一个邪恶的象征或者化身,因为她的出现和推动,塔洛才向自己并不认可的那个方向转变。她是否就是一种反作用力,是一种与塔洛的存在截然相反的力量的化身?
万玛才旦:杨措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她处在那样的环境之中,被那样的环境改变,就像她以前会唱拉伊,后来她说不会唱了。我觉得这个人物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很难将之归于邪恶。将杨措看成是某种邪恶的象征或化身,我觉得不妥,我不想将人物概念化。她也是现实处境里的一个真实人物,她也是一个受害者。

徐晓东:当塔洛的辫子被剪后,那些剪下来的头发也放在他刚才放钱的位置上,堆了一堆,感觉像个祭奠物。
万玛才旦:对啊,剪辫子对于塔洛而言,就是一个仪式。从某个方面讲,辫子就是他的身份的象征,他的身份在辫子被剪掉的那一刻就没有了。从此他也就失去了身份,真正的、他自己或者别人都认可的身份。对他而言,别人不记得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有一个小辫子。他自己甚至也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他听人叫“小辫子“比听人叫自己的真名“塔洛”还更亲切一些,听人叫“塔洛”,他反而觉得怪怪的。

徐晓东:影片自始至终没有离开对“身份”问题的探讨,比如看守所做身份证啊,去拍照片啊,或者与杨措的交往啊,塔洛遇到的人和与这些人的对话,都不断地在强化这一点:身份。在您写这些台词时,是不是有意地将这些台词双关化,比如说,他与杨措的对话,杨措说剪了辫子就谁也认不出你了之类……她说“认不出”时,可能只是指外表上不被辨认,但您显然有更多的指涉,指向了塔洛自身弥足珍贵的东西的失去,他不再是他了。再比如,那个警察局的所长看到他剪了辫子,也说了一句“太可惜了”,对于观众来说,这显然是双关的,不仅仅是“小辫子”可惜了,还有一种忧伤。
万玛才旦:很多时候我只是下意识地写了这些东西。当然,最终呈现的台词肯定要经过设计。比如,塔洛说,“我自己知道自己是谁不就行了嘛”。然后所长说,“你只有办了身份证,别人才知道你是谁”。这种对话的确有关于身份的暗示,是双关化的。故事本身也是一个关于身份的寻找然后失落的过程。

徐晓东:塔洛为做身份证去照相馆拍照时,有看似闲笔的表现,就是对那对拍照的新婚夫妇的描述。
万玛才旦:也不算闲笔。塔洛去照相馆时看到的这一切,其实对后面的叙述是有帮助的,与故事有密切关系。对于塔洛而言,这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后面,塔洛的出走,也受这些印象的影响,那些拍照的布景是个诱惑,不管是布达拉宫,或者天安门、纽约什么的,都是一个“远方”嘛。对他们而言充满诱惑,想要走出去看看的那个“远方”。后来,塔洛到理发馆,杨措问,要是让你选的话你会选择什么?塔洛马上说,布达拉宫。然后呢,然后是北京天安门啊。再然后呢?再然后就是纽约了。所以,照相馆所见所闻其实也是后面情节发展的一个必要铺垫。观众知道塔洛这些信息来自哪里,他为什么这么回答杨措,但杨措不知道。这种观众的全知视角,也是对观众观影心理的也一种满足吧。

徐晓东:那对夫妇穿上洋装之后,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于是将塔洛的小羊抱在了怀里,才感到舒服一点,为什么这样安排?
万玛才旦:这是一个剧作法的问题。塔洛的小羊羔肯定要跟周围的环境啊、人物啊发生一些关系吧。他带着一个很重要的道具,这个线不能断了。所以,让小羊叫了几声,引起他们的注意,说,我们抱着它可不可以呀?然后那对夫妇抱着小羊羔照相,感觉很舒服,我们也觉得很自然。另外,这样也可以增加情节的趣味性。还可以让塔洛与周围的一些人形成互动。

徐晓东:当塔洛带了钱去找杨措时,他很想将自己新学的拉伊唱给杨措听,想去卡拉OK,但杨措却想参加一个歌手的演唱会,说只有今晚会有,其他时候再去卡拉OK。这是个很忧伤的段落,观众由此知道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提前暗示了塔洛的悲剧。
万玛才旦:当杨措说不去卡拉OK时,塔洛是在心里唱着拉伊的。从镜子里看到,当杨措走过去时,塔洛在心里唱起了自己学会的拉伊。这里用了一个主观的声音。很清楚,就是一个情绪的东西。他们俩不会有什么结果。杨措虽然受情绪感染,有点感动,但其实对于自己是否将会去做那样大的牺牲,她是不确定的。只有她看到钱的那一刻是感动的,但很快,杨措就变回了原来的杨措。在演唱会的广告车开走后,杨措坐过去坐在了一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而不是与塔洛站在一起。作为杨措,她也是很累的吧。

徐晓东:塔洛抽的烟区别于别人,是旱烟,别人抱怨说,这个味道把大家熏死了。他也不肯喝啤酒,而是喝很烈的白酒。在您的观念里,是不是原来藏族一些很强烈的东西被外来的文化给冲淡了,被一些温和的东西给取代了?
万玛才旦:有一些,但这样说有点大了。其实是为了塑造塔洛这个人物。他习惯那样的烟酒,他是那样一个简单的人。他有一些坚持,比如在那个演唱会上,他只抽自己的烟,而且很坚决。至于酒,更多的是因为他会犯咳嗽的病嘛,需要喝烈酒来平息,同时这也是一个设计。

徐晓东:塔洛与演唱会上的那个男人在争夺杨措,是否有些隐喻,比如,资本的力量与原始情感的力量在较量,最后,还是前者占了上风?
万玛才旦:演唱会上出现的男人是杨措较复杂背景的一个暗示吧,不全是隐喻。一切都是情节发展到那个程度自然而然发生的,塔洛的情感对于杨措而言,不算什么。藏区的现实中的确有杨措这样的人,这也是对这样一种当下现状的描述吧。

徐晓东:影片临近结尾时,塔洛又在背“为人民服务”,但他已经无法流畅地背出来,与开头形成对照。您为什么这样设置?
万玛才旦:塔洛不再能够流畅地背诵出“为人民服务”,有信仰原因,他背叛了自己的信仰,背叛了自己所恪守的准则,同时也失掉了作为他身份标识的小辫子,他的生活和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那惊人的记忆能力也就消失了,离开了他。
就像某些格萨尔说唱艺人一样,有很多艺人能够滔滔不绝、几天几夜地说唱几部、甚至几十部,但是,因为国家为了抢救这些文化遗产,把这些艺人请到城市里面,给他们发工资,然后让他们每天对着机器说,慢慢地,他们就说不出来了。塔洛神奇记忆能力的消失,跟这种现象有点相似性吧。
徐晓东:另外,所长招呼了大家来听,一堆人将塔洛围住,有点审判他的意味,您主观上是想营造这样的感觉吗?
万玛才旦:也不是审判吧,只是围观。有时候我们看见很多人在街道上围观某个特殊的人时,就像是围观一个怪物一样。
徐晓东:结尾处,塔洛回到山上,走到铁丝网的那边,很大的景,很小的人,这个构图有很强烈的孤独感和绝望感。下一个镜头里,塔洛就自杀了,这个结尾比起《静静的嘛呢石》而言很激烈,《老狗》也不过是杀死了狗而已,塔洛却自杀了……
万玛才旦:没有没有,那不是自杀,顶多是自残吧。他只是点了个鞭炮炸伤了自己的手,又不是引爆了手榴弹,你也太天真了吧。塔洛炸伤自己的手,把惩罚施向了自身。像塔洛这样一个人,也不可能将惩罚施向别人,只能施向自身。
徐晓东:为什么用黑白色调?
万玛才旦:黑白是为了突出塔洛的状态,他的精神世界其实是很简单的,他的价值观更简单,是非黑即白的,要么,他放好羊,死了就像张思德一样,重于泰山;要么,他把羊卖掉,说,这下我成了一个坏人了,死后就像法西斯一样轻如鸿毛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人。而且,我觉得他所处的山上那个环境,更适合用黑白来表现。有美学和氛围上的考量。
徐晓东:您更认可像塔洛这样简单地活着吧。
万玛才旦:我想我比他复杂多了。我创作了很多的人物,每一个人物都没法完全代表我。
徐晓东:您所有的影片,都弥漫着忧伤的情绪,甚至会有点绝望,您似乎很怀念一些价值,对一些改变有发自心底的不适与难过。您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暂时的呢?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
万玛才旦:都是短暂的表象,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为那些短暂的、变化的、不确定的东西忧伤,甚至绝望,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徐晓东:有没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
万玛才旦:尤其是价值,不太可能是永恒的。价值永远在变,一百年时间,一些“真理”往往就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几年、十几年就变了。往往令你深信不已的一些价值,也许两三年之后就什么也不是了。但也谈不上怀念吧。可能跟年龄、阅历有关系,都在变。你人生一开始就接触到一些价值观,可能对你影响比较大,就像饮食一样,一开始吃过的东西会对你一辈子的口味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