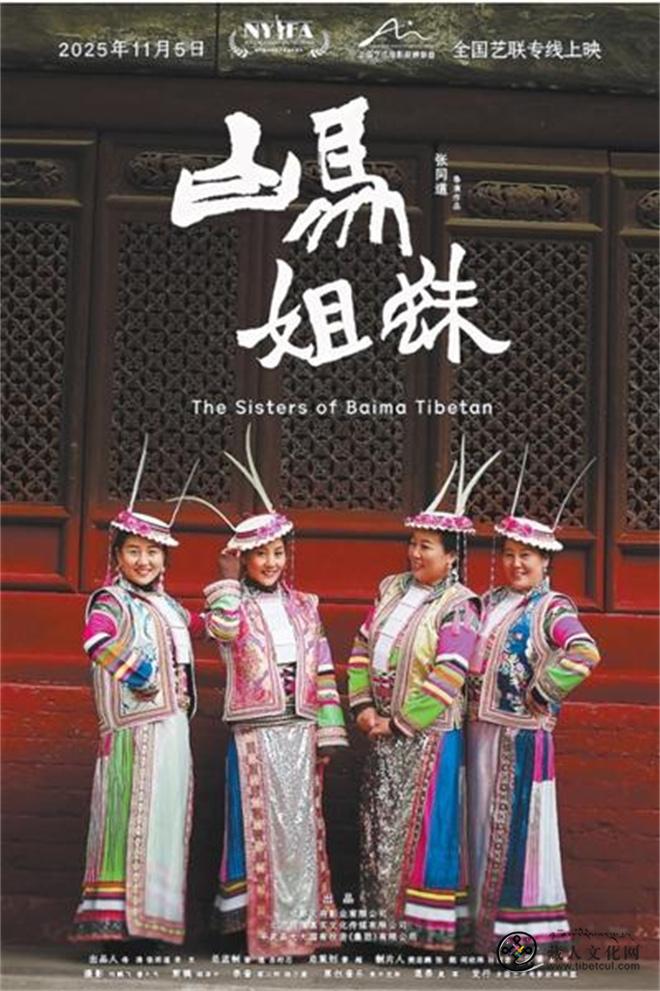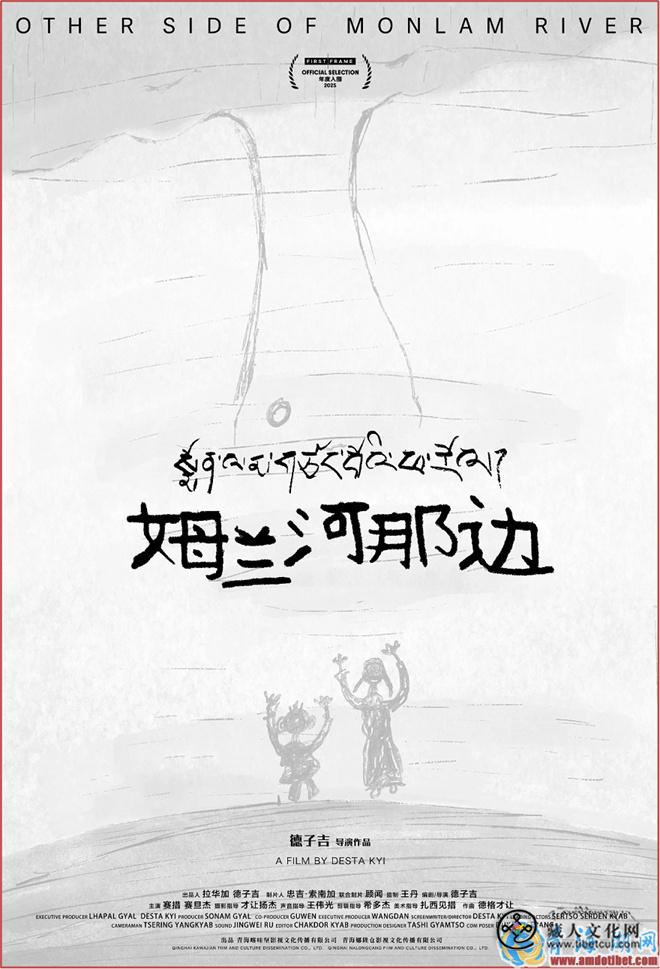一、缘起
《喜马拉雅天梯》的原初想法来自于制片人雷建军。2009年时他作为摄影师参与了一个纪录片剧组,对中国登山界的前辈进行访谈。也就是在那一次,他跟随摄制组来到西藏,从拉萨前往珠峰大本营拍摄一些空镜头。意外的是,西藏登山学校的一名年轻队员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一沓印刷质量一般的藏传佛教经文交给他,托付他把这些经文带给他的父亲。这名队员的父亲是绒布德寺唯一的喇嘛,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寺庙。回到北京之后,雷建军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起这个故事,他觉得,在这对父子关系之间,在西藏年青一代和他们的父辈之间,蕴含着这个民族的未来。

宁金抗沙康布寺的白塔,下方远处是登山大本营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难得的题材,我们决定跳出之前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创作方式,采取商业制作的模式,同时探索延续之前的民族志的工作方法来保障内容和主题的表达。2011年,就在我们上一个纪录片项目《一张宣纸》进入后期的时候,我们通过朋友结识了《天梯》的出品人和联合导演萧寒,找到了影片原始投资最重要的来源。2014年,我们还把一部五年前的学生作品《飞鱼秀》送进了院线,彻底摸清了纪录电影发行的各个环节。
二、核心挑战
当听说一部关于西藏的纪录片的时候,大多数观众一定会想到广阔的风景,神秘的宗教,可能还会有各种的高海拔动植物。最早,这些视觉意象同样也是我们在创作之前的仅有想象。但是同时,我们也确信,这对于我们的创作来说是不够的,我们希望这部影片不仅仅是一部剧情紧凑、戏剧性强、视觉华丽的纯粹的商业电影,不仅仅是去讲述可以发生在任何年代和地域的英雄人物的爱恨情仇。我们希望它能够传递更多的社会和文化洞见,并且不仅仅是呼应和加固我们对于异文化的传统认知。 因此,对于这样一部纪录片,我们虽然有了基本的拍摄对象和故事链条,即登山学校的青年藏族人学习登山、冲顶珠峰,我们也有了影片的核心关切,即西藏的现代化如何与自身传统发生关联。但是我们仍然缺乏方法,那种可以让我们通往人物内心,从内部人的视角理解他们的文化、行动和精神世界。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才能够在讲述精彩故事的同时有深度地展示地域文化。在影视人类学的方法论指导下,以及更重要的、来自于藏族创作团队的贡献,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定日县城
定日县城
和剧情电影不同,观察式的纪录片的创意和实施更多来自于整个团队的力量;而优秀的纪录片摄影师在拍摄现场则承担了更多的创作角色。我们的摄影团队由著名藏族摄影师扎西旺加担任摄影指导,两名核心摄影师分别是汉族的张华和藏族的德嘎。此外,团队中的藏族创作者还包括了副导演史达、高山摄影师巴桑塔曲和旺堆,以及花絮摄影师兼司机次多。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他们不仅通过和拍摄对象的积极互动和对现场的主动捕捉体现了专业的影像工作水平,而且对影片的主题思想形成了核心贡献。他们自身就处在西藏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剧变的社会语境中,对于本民族的当下和未来有长期的思考。他们成为了影片能够抵达拍摄对象内心深处的坚实保障,提供了文化深描的可能性。
三、影视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问。人类学的思想和哲学准备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完成。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传教士和殖民官员们带回来各种关于这个世界的地理和文化信息,欧洲的人文学者发现,在他们的文明社会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社会形态和文化样式。伴随着近代社会科学的逐渐生成,这些欧洲之外的社会进入到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之中。就像一个简单的并且不太科学的分类法所说,社会学起源于对我们自己社会的研究,而人类学则是对他者社会的研究。如何有效地解释和理解异文化和社会,也成为了人类学家们的核心问题。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的方法论由英国的人类学家们确立下来,马凌诺夫斯基和布朗通过他们长期的田野工作撰写出令人信服的人类学著作,后来的人类学者在这两位功能学派的先驱的启发下丰富和完善了当代人类学的方法论,即田野工作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这种工作方法强调和研究对象的长时间相处,通过学习他们的语言、过他们的文化生活,将研究者自己作为一个研究工具,在从外部人转变为内部人的过程中,达成对他们文化的深刻理解。

航拍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摄影师张华(汉族),摄影指导扎西旺加(藏族),副导演史达(藏族),副导演郭布勒·希荣(达斡尔族) 起初,大多数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方式以文字记录为主,辅以绘图和实物收集等手段。随着影视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普及,一些田野工作者发现了影像代替文字进行文化记录的独特优势,影像素材成为他们从田野回到书斋后进行研究和写作的重要助手,同时也在学术报告和论文专著等学术成品中起到辅助说明的作用。在美国女人类学家米德的卓越工作下,人类学家开始思考将影像代替文字、作为呈现田野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主流方式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影片拍摄、剪辑和类型形成了我们所谓的影视人类学这门人类学和视觉传播之间的交叉学科。 回到《天梯》所遭遇的拍摄挑战,我们尝试从影视人类学中汲取养料,通过调研、摄影和剪辑的过程去发现、建构和生成人物-行动的因果链条,确保叙事学意义上的完整性;同时,避免将西藏的景观和藏人的行为呈现为简单的宗教符号和地域特色,而是通过参与式观察产生文化洞见,最终通过视听语言完成一个“厚叙述”的西藏。最终,在影视人类学的指导下,对于《天梯》这个选题,我们发展出一个指导性的问题,确保我们在制作过程中足够集中:山是什么?登山对于不同的人群有什么特殊含义?保持对这样问题的不断探寻,我们就有可能找到文化、社会和故事的相交点。
四、山地
我们的正式拍摄从2013年9月底开始,这个时候恰逢秋季登山,登山学校的学员们跟随登山公司组织的队伍到不同的地点承担服务。我们跟随攀登宁金抗沙峰的队伍来到这座山峰的登山大本营,呆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虽然时间很短,但作为第一次参加登山活动的我来说,仍然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这些印象在后来的拍摄阶段不断重现,形成了我们对于山脉和登山的整体感觉。 宁金抗沙的大本营,这块海拔4800的山地,在登山期间,成为了一个微型的社会生态系统。这里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登山客户,有为这些客户搭建帐篷、搬运行李和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的登山向导和协作,还有其他人。我们的摄像机跟随着登山学校的六批学员,次仁多布杰,来到距离大本营不远的康布尼姑寺,寺庙里有5位修行的尼姑,寺庙外还有两三个年迈的修行者。寺庙为登山者们提供宗教的庇护和心灵的寄托,这里传说曾经是阿底峡尊者到过的地方。我们注意到次仁多布杰,是在头一天第一次往上运输之前他在工作空闲诵读经文的时候,对于登山学校的大多数学员而言,登山之前的诵经和炜桑是必须的,这些能够保佑平安、带来好运。登山客户到来之后,康布尼姑寺也成为了他们第一天适应性训练的徒步路线的终点,虽然宗教信仰不同,但是他们也同样祈求本地神灵的佑护。 这个生态系统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周围的村民。我们来到大本营的第二天早晨,由周围村民组成的马队应邀而来,花三天时间用马匹帮助登山队将辎重运到更高的营地。临走的时候,登山队的财务和马队的首领完成了交易,这次交易金额总共是一万两千块,按照事先的商议,具体价格是一人或者一马均为130元每天。马队的首领是望果村的村主任米玛加布,他今年五十岁了,代表村民和登山队交涉财务事宜。之前,他们的期望价格是150元每天,但登山队只给130元,因此有些不满。马队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式,他们给货物标记,然后通过抽签决定谁的马背多重的货物,以防止因为货物重量和体积的不均造成纠纷。他们大多数自己带着马匹的饲料和自己的干粮,吃饭的时候只借用登山队的火炉煮茶。

山在藏族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藏历大年初三,每家都会派一个着盛装的年轻男孩,在太阳升起前将风马旗挂在村边的神山上。
这样看来,对于山地来说,登山者更像是过客,而修行者和附近的村民则是本地人。我们的影片不仅仅要拍摄登山者,也要关注这里的“原住民”,把他们的视角和行动作为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4年的登山季拍摄中,摄影团队把镜头对准了珠峰绒布德寺的僧人阿古桑吉,他正是雷建军第一次来珠峰的时候带给经书的人,而他的孩子次培,那位请雷建军带回经书的孩子,是这一年第一个成功登顶的向导。在电影中大家能够看到,阿古桑吉一方面感受到珠峰顶部越来越变化多端的气候,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儿子和汉族客户们祈福。在登顶的那天上午,他在大本营,通过高倍望远镜关注自己儿子的安危。一个守护一方净土的僧侣,和他的依靠登山谋生的儿子,成为了一对迷人的人物关系,也是故事与文化的一个精彩的交点。通过不同人群的想法和行动,西藏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共处得到了呈现。
五、学校
在2013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我们开始进入位于拉萨的登山学校展开拍摄。拍摄学校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国内外纪录片作品可供参照,并且发展出来一条稳定的对于学校和教育的观点。不过,西藏登山学校仍然足够特殊,它是中国唯一提供登山专业教育、颁发职业文凭的学校。尼玛次仁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早年他是一名射箭运动员,后来长期在中尼边境的珠峰地区从事登山联络和服务。 自八十年代初西藏山峰对外开放以来,由于运作体制及传统的制约,中国所能提供的登山服务,很大程度上仅限于收取登山注册费和联络、接待工作。高山上的商业服务基本都是由第三国人员承担。在2000年以前,西藏登山协会每年接待了近百支国外登山团队,团队雇佣的夏尔巴人员多达三四百人,所付给的服务费用近百万美元;而西藏山区的农牧民群众,因为缺乏专业登山技能的培训,只能提供如牦牛运输、帮厨等简单的高山服务。 1994年尼玛次仁有了创办登山学校这个想法, 1998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1999年正式成立的学校。学校的创办精神、办学宗旨是培养一批有文化、专业技能过硬、具有良好服务意识的中国高山向导及高山服务人员,带动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推动中国登山事业的发展。来自珠峰地区生长在普通藏民家的孩子在这里学习如何登山,学习如何带领别人去登山,学习如何成为山的使者。 学校对学生的要求非常高,实行军事化管理,纪律严格。为了让学生毕业后可以成为好的登山协作,学校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都进行着严格的管理,在校期间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谈恋爱,违反者一经发现立即开除。每天早晨上文化课,学习藏语、英语、登山知识,每周前三天下午体能训练,后三天技术训练。
西藏登山学校的岩壁,学员们常在这里训练攀岩技能
在登山学校刚刚开办的那些年,这里对于后藏地区的青少年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地方,他们可以来到拉萨学习,穿着赞助商提供的鲜亮的衣服回到家乡,成为受人羡慕的登山英雄。不过,由于西藏的逐渐开放,这些年登山学校的光环逐渐褪去,现在的后藏年轻人有了更多选择的空间。 这所学校日常管理中的核心人物是副校长普布顿珠。普布顿珠是登山学校第一批的学员,属于业务能力较强的,曾经参加过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山峰的登山探险。对于普布顿珠个人来说,他认为严格管理对于这些学生尤其重要,特别是在拉萨这个环境里,如果管理不严格,学生们就会被外面的一些不好的风气带坏。普布顿珠对自己和对学生都有很高的期待,这也是他内心对学生之爱的来源。不断变化着的学校和拉萨,也成为了西藏传统和现代之间关系的某种缩影。
六、珠峰脚下
除了登山之外,我们的另外一个拍摄场景是珠峰脚下的定日县和聂拉木县,这些孩子们的故乡。我对定日县城的最初感觉,是从住宿和打针开始的。离开拉萨的之前的一天晚上,我在去学校拍摄之后不慎被放出笼子的看门狗咬伤,在拉萨的防疫站打完第一针之后,我拿了剩下的四针和五个针管,带来定日。 定日的人民医院在新城的东南角,就在从318国道通往县城的路边。我们穿过新城的雪豹路,经过了大门紧闭的上海大酒店,以及一条空旷落寞的商业街,终于来到安静的人民医院。大概是由于周末,抑或是午饭时间,医院空空荡荡看不到一个医生。最后我们在药房里遇到了一个女护士,问了问才知道这里的一些医生都休假了。这和昨天旅馆的工作人员准备自驾回家一起,让我更深地感受到定日这座城市在冬日的寂静气氛。 我想想要接受疫苗变质的风险,心有不甘,决定先在林卡路,也就是县城的老街道吃个饭,然后去防疫站问问。定日老街里,常常能够听到清脆的马铃声,接着就看到被打扮得花花绿绿的马拉着四轮车,马夫坐在车里赶马。有时候车子是空的,有时候则拉了一些青稞等货物。相比于中老年男子驾驶四轮马车,这里的青年人无疑更加喜欢摩托车。一路到了防疫站,和人民医院类似,这里也空空荡荡,在外头晒太阳的三个便装男子告诉我,这里只有给出生小孩注射的疫苗,以前有过狂犬疫苗,用完之后就没有进货了。最终,我只能冒着疫苗变质的风险,请街道诊所的医生,按照时间把剩下的四针注射完毕。 随着在定日县城拍摄时间的增长,我越来越能感受到这里浓浓的生活气息,西藏对我来说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地方,藏民的生活也不再是世外桃源般的单纯美好。这个离珠峰最近的县城,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谋生者,本地藏族,青海回族,四川的商贩,云南白族的银匠,河北的浴室老板,陕西的武警,大家都聚集在一起,互相成为客户和朋友。当通过田野工作逐渐参与到拍摄对象的生活、给我们之前的一些刻板印象祛魅之后,对于我们的人物塑造来说,一个很简单却常常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重新浮现出来:生计。在后藏这样一个农牧业为主的社会里,生活依然艰难,而珠峰,对这些年轻的藏族孩子而言,如同一个承诺,依靠攀登珠峰,他们有可能在读书升学之外找到一条离开这种艰辛生活的路径。 从县城走过一段山路,就是次仁多布杰的家乡。冬天我们跟着他走过这段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的时候,他说每次经过这片山地,小时候和朋友们来这里捉迷藏的景象就会浮现在他的眼前。初中毕业之后他收到了登山学校和市区职业中学的录取通知,同时还有参军作为第三项选择。他选择去登山学校,因为那里不需要学费,而且就业看起来更有保障。不过,他仍然把职业中学的录取通知书仔细收好,和自己小学、初中时的书籍、作业和试卷都整齐地摆放在亲手做的小书橱里。 最早认识次仁多布杰是宁金抗沙看到他对于藏传佛教的恭敬;后来他一直以一个好学生的样子出现,听话、读书、认真学习和工作。但在定日拍摄一个月之后再来到他的家中,和他交流之后,我们能够感受到更加丰富的人物情感。对这些年轻人来说,珠峰实实在在地代表着能够离开辛苦的农民生活。五六年来,他们都以登山为生活的轴线,上课、训练、一次次地高山协作。但是,登山会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成为改变他们命运的金钥匙吗?实际上,对于传统社会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如同成为登山向导一样,也成为了一个被赋予了很高期待的目标。在传统的西藏文化中,山具有丰富的内涵;我们也期待在这部纪录电影中,围绕“山”这个具体的意向,提供更多关于西藏的传统与未来的思考空间。
(图/文:梁君健。作者为《喜马拉雅天梯》的联合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