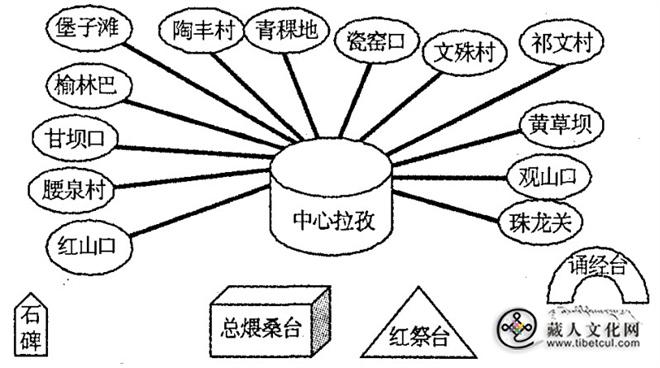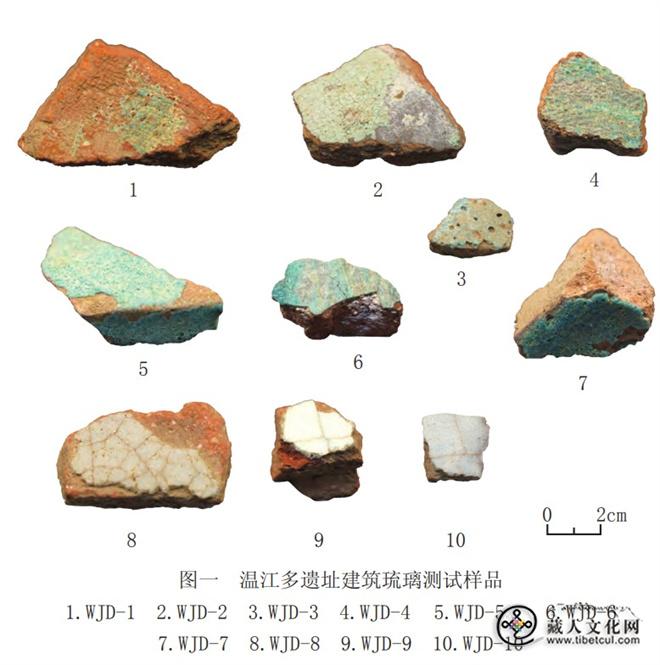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曾晓鸿
摄影:曾晓鸿
摘要:文章通过公元八世纪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灭苯、詹巴南喀被强行改宗佛教并重新构建苯教新派等历史活动, 解释了苯教新派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说明新派苯教的产生实际上开始了一个青藏高原土著文化传统与印度外来文化传统开始相互吸收和融合, 为以后藏民族传统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新整合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公元八世纪; 苯教新派; 詹巴南喀; 莲花生;
一、学术缘起
在苯教历史上, 公元八世纪的穆苯·詹巴南喀是一位无法回避的重要历史人物, 他不仅在当时的一些宗教活动和历史事件中举足轻重, 而且对后世的苯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撰写的著述和法本至今在苯教寺院和民间修行中成为重要的文献依据。除了他以外, 在晚期的苯教历史文献中还出现过其他几位同名的詹巴南喀, 即出生在大食的詹巴南喀、出生在象雄的杰尔邦·詹巴南喀, 还有一种说法, 认为止贡赞普时期也出现过一位詹巴南喀。在传统的苯教文献中, 不同时期的詹巴南喀的历史功绩及其影响又交相辉映, 历史的真实、宗教的神秘和后世的神话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错位的人文景象。本文以公元八世纪的苯佛关系和吐蕃历史人物穆苯·詹巴南喀为主要对象, 试图对这个人物及其有关的文化现象做一次力求真实的梳理和研究, 并试图以此来解释其对后世苯教新派的形成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二、公元八世纪的历史背景
公元八世纪是吐蕃在政治、军事和文化诸方面取得重要发展的历史时期, 在这个时期, 发生了若干个对吐蕃后世历史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在政治方面, 由于雅隆王朝长期的酝酿和东征西战, 在松赞干布时期终于冲出雅隆河谷, 迁都逻些, 吐蕃王朝横空出世。政治上的成功更加稳定了王室的权威, 增强了王室的号召力。政权的稳定和迁都逻些, 得到一个相对休养生息的时间和比原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随后一百多年来, 励精图治, 苦心经营, 到了公元八世纪, 吐蕃王朝已经成为中亚的一个强势政权。八世纪初, 吐蕃征战滇北诸部, 从唐朝监察御史李知古手里重新夺回滇北诸部;在河源地区, 与唐军对峙, 连年征战;在西边, 公元723年, 吐蕃攻破小勃律, 以谋取西域四镇的通道, 被求援前来的唐兵击败后, 于公元736年, 吐蕃攻陷小勃律,“小勃律被吐蕃役属, 葱岭以西二十余国皆臣服于吐蕃”;在东边, 与唐朝争夺南诏, 几经胜负;公元八世纪中叶, 吐蕃发兵唐朝, 沿路攻陷西域四镇及唐境十余州, 最终攻陷唐都长安, 十五天后撤兵。后与唐朝盟和立碑。[1]西边还与大食对抗, 争夺葱岭, 历经征战。[2]在文化方面, 自从松赞干布开始引进佛教以后, 苯教和佛教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和博弈, 吸收和融合之后, 到了公元八世纪, 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支持下, 佛教已经在吐蕃立足, 具备了可以大规模传播的土壤和条件。从印度来吐蕃传播佛教的译师们越来越多, 加上王室的大力支持, 与王室形成一定的合力, 在当时的社会上有了一定的地位。这种异文化的入侵, 早就引起了吐蕃本土文化传统即苯教信徒们的警觉, 并开始反击, 形成两种文化力量在吐蕃本土的冲突和较量, 这种冲突和较量不仅在宗教职业者之间发生, 而且在吐蕃王室的权贵中形成分别支持两个派别的世俗力量, 势力不分伯仲, 这种从宗教界波及政权内部的宗教冲突甚至开始危及到吐蕃王室的政权根基。在这种情况下, 支持本土的苯教还是印度的佛教成为吐蕃王室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重大的文化选择。如果不尽快完成这个文化选择, 不仅王室青睐已久的印度佛教无法全面传播, 而且可能危及王室的权威。对于王室来说, 支持佛教已经成为传统, 从松赞干布开始, 吐蕃王室就已经成为印度佛教徒们的坚强后盾, 而苯教又是吐蕃的土著宗教, 不仅在民间是唯一的宗教传统, 而且在王室仍然有着强有力的支持者, 其势力已经成为传播佛教的绊脚石。要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 必须有一位强权赞普才能完成, 到了公元八世纪中叶, 赤松德赞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敦煌文献PT.1287载:“赤松德赞时期, 法善政威, 赞普巍居于天地之间, 功勋昭然, 其行为堪称人之楷模” (1) 。充分显示了当时赤松德赞的地位和威望。
三、苯佛关系中的詹巴南喀
到了公元八世纪中叶, 赤松德赞作为赞普, 尽管已经权倾朝野, 并且他自己在内心里对佛教仰慕已久, 加上吐蕃王室扶持佛教已经形成传统。但作为本土文化传统的苯教仍然是吐蕃信徒最广泛的宗教, 具有绝对优势, 早期苯教历史文献甚至认为, 当时苯教在王室里的势力已经影响到了吐蕃赞普的权威 (2) , 可见, 当时苯教已经成为赤松德赞传播佛教的障碍。尽管如此, 如要只用赞普的决定来完成这个重要的文化抉择, 还要三思而后行。他要尽量避免冒犯那些遍布吐蕃全境的苯教徒们和那些辅佐他朝政的苯教重臣们, 以及跟随他驰骋疆场的信仰苯教的军事将领们。他要用一种巧妙的方式来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 既要完成自己的夙愿即在吐蕃传播佛教, 还要有一个比较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让苯教退出历史舞台, 还要让苯教徒们无话可说。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就是让苯教和佛教进行一次辩论, 用辩论的胜负来决定各自在吐蕃的未来。从他利用那次辩论的结果来驱逐苯教徒的做法说明他早已认定苯教已经是他传播佛教的障碍。关于这次苯教和佛教的辩论, 藏文文献最早的记载要数公元九世纪的《巴协》。根据《巴协》, 在这次辩论之前, 已经有过很多次民间的较量, 吐蕃的苯教徒直接与赞普请来的印度佛教徒发生冲突, 甚至公开要求他们离开吐蕃。尤其是当赞普正在推行佛教的关键时刻, 苯教徒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传统信仰, 近而对王权表现出不恭时, 更加坚定了赞普剪除异己的决心。《巴协》记载:“当时, 苯教徒和大臣们反悔说信苯教而非佛教。波德萨多说, 在一个国度产生两个宗教则罪孽深重。吾等辩论, 你胜则兴苯, 吾等返回, 佛教胜则灭苯, 共同施佛。共同商定大臣和佛教徒辩论, 但缺证人。(赞普) 行宫驻于素尔普姜布, 佛教方指派王舅年桑, 达赞东斯, 桑果·拉隆斯, 娘·夏米作为波德萨多的代表和辩论者。达热鲁贡、大星算师琼波·杜牧凑, 琼波·泽泽、觉乎拉·曼兰巴尔、采弥等被指派为苯教方的代表和辩论者。在辩论时, 苯教方论据不足, 缺乏逻辑, 佛教方论据充分且深奥, 辩论语言俱佳, 故苯教败北”; (3) “那个时期 (赤松德赞时期) ,国王的权势居高如天, 吐蕃全境幸福圆满”。[3]
令人奇怪的是, 《巴协》在记载那次辩论时, 悉数五位苯教大师的名字作为苯教方的代表和辩论者, 其中没有提及詹巴南喀, 《巴协》四种不同抄本亦同。[4]另外, 敦煌有关苯教的文献都是涉及苯教仪轨方面的, (1) 因而没有提及那次辩论, 也没有出现詹巴南喀的名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敦煌文献中的历史纪年部分不仅没有提及詹巴南喀的名字, 甚至没有提及苯教与佛教之间那场著名的辩论。至此, 虽然有关那场著名的苯佛辩论, 因为有当时佛教徒学者的历史著作《巴协》的记载以及后世苯教徒历史著作的佐证, 可以据为信史。但是, 被认为詹巴南喀参加过那场著名的辩论的说法, 目前尚缺乏确凿的历史依据。
在大约两个世纪之后, 《雍仲苯教宏扬史》记载的苯佛辩论中出现了詹巴南喀:“国王赤松让苯教徒和佛教徒辩论, 指派象玛相·春巴杰和安·达热鲁贡为苯教方证人, 齐布·释迦扎瓦和聂尔·达赞咚斯为佛教方证人, 桂·赤桑亚布拉和强曲多杰哲琼为总管, 国王在上座, 苯教方辩论人为詹巴南喀, 佛教方辩论人为玛氏游方人仁青却”。(2) 在这个记载中, 詹巴南喀作为苯教方的两个辩论者之一出现, 这是詹巴南喀作为公元八世纪苯教和佛教那场重要辩论的直接参与者第一次出现在藏文历史文献中。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文献的后记中有一句话 (3) :“大师们议定, 由詹巴南喀记录成文”, 从这个记载看来, 这部珍贵的历史文献似乎出自詹巴南喀之手, 而且是将其与大师们共同讨论的结果记录成文, 按理应该是可靠的事实。但是, 该文献语言的古朴程度与公元八世纪的金石文字相差较大;更有甚者, 这个文献的末尾, 出现了詹巴南喀之后的历史人物, 如达磨、云丹和沃松等, (4) 虽然此书对于赤松德赞之后的历史只有一页多一点的简述, 似乎有后人增补的嫌疑, 但毕竟出现了上述历史人物, 认定为后人伪托詹巴南喀的作品更为坐实。因此, 其成书年代无法推到公元十世纪之前。《雍仲苯教宏扬史》是在公元十世纪末和十一世纪之间, 由从康区到桑耶寻找伏藏的苯教掘藏师塔西·叶西洛哲 (5) 发掘后问世, 传世至今。紧随其后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世续题解详传》沿用了上述文献的说法。此后, 几乎所有的苯教源流文献都将詹巴南喀作为那次辩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来叙述。由此看来, 詹巴南喀直接参与公元八世纪苯教和佛教那场重要辩论的记载的最初来源很可能就是《雍仲苯教宏扬史》。虽然那场可以提前知道结果的辩论以苯教徒的败北而告终, 后世文献对詹巴南喀参加过那场辩论的记载也缺乏足够的证据, 但苯教徒对其深信不疑, 因而, 詹巴南喀作为苯教的代表参加那场辩论的说法使其在后世苯教徒中的地位变得更加崇高。当然, 他在苯教徒中的历史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参加过那场辩论的说法, 他是一位在苯教徒中享有崇高声誉的大师, 而且在佛教徒的历史记载中也时有提及:十二世纪的佛教学者娘·尼玛韦色 (1124-1192) 的《娘氏宗教源流》中, 詹巴南喀俨然以一位法力超群的历史人物出现:“詹巴南喀 (使法力) 雷击如射箭, 击中野牦牛”;[5]《布顿教法史》在罗列重要翻译师的名单时, 将詹巴南喀列为第25位;[6]龙钦·智美沃塞的《龙钦教史》将其列入赤松德赞时期的宗教大师和译师的名单中;[7]赤松德赞时期著名的“二十五王庶”中的齐格琼罗就是詹巴南喀。[8]等等, 这些记载足见其在赤松德赞时期重要的社会历史地位。
赤松德赞充分利用在辩论中苯教徒败北的机会, 立即开始迫害苯教徒, 为他传播佛教扫清障碍。他强令苯教徒改宗佛教, 一些不愿意皈依佛教的苯教徒, 或者被杀, 或者被驱逐。苯教塞康即神殿有的被拆, 有的被强行改成拉康即佛教殿堂。民间仍然不愿意放弃苯教信仰的百姓都受到各种惩罚。[9]甚至有一部分苯教学者被强行改宗佛教, 其中詹巴南喀最为著名, 因此又名南班·詹巴南喀, (1) 即被迫改宗佛教的詹巴南喀。他不仅表面上改宗佛教, 而且为佛教做了许多事情, 参与佛教活动, 以取得王室的信任。苯教历史文献还记载他削发为僧, 成为佛教僧人, [10]但这个记载未见于佛教历史文献, 留待进一步考证。民间传说他还是七觉士之一, 可未见确切的文献记载。但同时, 他还秘密地修行和传授苯教, 撰写了若干苯教著作, 传世至今, 成为苯教寺院里的教材。后世的苯教历史文献基本上沿用了詹巴南喀同时修行和实践苯佛两种宗教的记载,比如, “詹巴南喀等人承诺无教派成见, 顺应国王和佛教徒的意愿成为佛僧。将襄 (2) 在头顶上摇响后承诺放弃雍仲苯教并将襄藏匿起来, 将金刚杵和法铃在自己的眉间摇响后, 承诺皈依佛门并自己削发为佛僧直至三十五岁”。(3) 因为赤松德赞灭苯, 大量的苯教文献因为无法传播和修习被藏匿起来, 有待后世条件许可时再度传播, 藏匿者就包括詹巴南喀, 相传藏匿的文献中还包括他自己撰写的文本。
在詹巴南喀之前, 佛教在吐蕃只限于在王室的传播, 没有在社会上广泛展开, 因而也没有造成与苯教之间的文化冲突。但赤松德赞的灭苯, 导致苯教在政治上突然进入劣势, 受到严重歧视, 不愿意皈依佛教的苯教徒被杀戮或者被驱逐之后, 以詹巴南喀为首的苯教徒表面上不得不顺应王权的意志, 改信佛教, 但暗地里小心翼翼地开始撰写当时的王室和佛教徒当权者容易接受的苯教文本, 这些文本有些标明作者, 有些则以伏藏文献的形式流传, 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这些文本尊崇莲花生。因为当时, 莲花生是赤松德赞从乌仗那迎请的佛教密宗大师, 也是他极力传播佛教的主要推手, 更是赞普用来对付苯教徒的主要工具。在那种情况下, 苯教徒如流露对莲花生的半点不敬, 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因而, 对莲花生的态度可以证明苯教徒对王权的服从程度。詹巴南喀和当时的苯教大师们撰写的大量的苯教文本最初在地下流传, 逐渐在苯教徒中传播开来, 成为一种对佛教采取温和态度甚至尊崇莲花生的苯教流派逐渐浮出水面, 这就是苯教新派的最初起源。虽然这种新派的所有经论文献的宗教归属仍然是苯教鼻祖辛绕弥沃及其思想体系,仍然表现为一个与辛绕弥沃的教法一脉相承的传统, 但这种苯教新派的产生的确是赤松德赞的政治高压和莲花生为代表的强势佛教导致的一个产物。在这个新派苯教的文献里, 莲花生不再是一个像现实生活中那样是苯教的对立面, 而是苯教徒供奉的大师, 甚至逐渐地产生了修行莲花生的各种苯教法本,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 逐渐完成了莲花生在苯教新派传统中从人到神的演变, 莲花生在佛教传统中一样, 在苯教新派中的莲花生也同样被极度神话。以詹巴南喀为首的苯教徒对苯教的这种改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虽然在现实中, 这样的改变是被迫完成的, 尤其对吐蕃的本土文化传统来说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屈辱, 但在客观上成为青藏高原本土文化接受佛教文化的实质性尝试, 也是苯教和佛教在理论和教义方面开始融合的重要标志, 在这样的改变中, 詹巴南喀无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 佛教徒及其支持者考虑到吐蕃民众大多数仍然为苯教徒的现实和外来宗教传统在吐蕃立足的艰难, 为了迎合苯教徒, 同样吸收了大量的苯教内容, 用苯教徒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传播佛教, 比如, 被认为莲花生降服了诸多苯教神祇, 并根据苯教的修行和祭祀程序为许多重要的苯教神祇重新撰写佛教的修行法本和祈祷词, 使其变成佛教的护法神或者信仰佛教的地方神,使改信佛教的吐蕃民众感觉到这些世世代代保佑他们的神祇仍然在保佑他们, 甚至也与他们一样改宗成为佛教徒, 减缓了他们因改宗佛教可能受到原有神祇惩罚的担忧和恐惧心理。另外, 对苯教传统中的修行仪轨、煨桑净化招福降魔拉泽驱鬼朵尔玛招魂祭祀仪式等采取照单全收的态度, 不仅全盘接受这些仪轨所包含的宗教思想及其宇宙观和仪式程序, 而且重新撰写了这些苯教仪式的佛教文本, 将其改变成佛教仪式, 使人们熟悉的地方神祇的祭祀仪式和宗教仪式佛教化,逐渐消除了吐蕃人对强行佛教化的抵触心理和苯教徒因改宗佛教造成的对原有苯教神祇的恐惧心理, 使他们接受佛教更加容易, 更加心安理得, 逐渐放弃了抵触佛教的心理防范。这些文本有些作为莲花生的作品出现, 有些则以伏藏文献传世, 至今可以找到它们的多种版本。在后世作为伏藏出现的宁玛派文献中, 不仅这类著作越来越多, 而且莲花生大师成为藏文文献中传记文献最多的历史人物, 这些传记中被认为是莲花生降服的山神和地方神以及伪托莲花生之名流传的祈祷词和修行法本也越来越多, 苯教新派中的莲花生也像被佛教徒极度神话了的莲花生大师一样,逐渐成为无处不在、一个无所不能的神话人物。
由于上述苯教和佛教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代替了原先的抵触和对立, 缓和了赤松德赞对苯教的态度, 开始接受改变后的苯教, 加上当时的吐蕃民众毕竟还是苯教徒为绝大多数, 王室还要考虑到他们的感受, 因而, 赤松德赞执政后期明显放松了对苯教的制衡措施, 他说:“苯佛二教均曾经被弃, 现欲重新尊奉二教, 请二教均接受吾等供养。二教均具有伏藏, 以此为本。苯佛均善且真, 吾等在世时需要二教, 庶民生机需要二教, 众生善业需要二教, 世上敏威为苯, 善行为佛。从此苯佛二教相聚, 在素尔普姜布举行和睦聚会” (1) 。从这些文字看来, 在以佛教为主导的格局已经形成, 苯教徒的公开对抗已经被消除之后, 赤松德赞不仅开始善待苯教, 更为重要的是,“二教均具有伏藏, 以此为本”, 他希望和睦相处的苯教和佛教均以改头换面以后的伏藏形式为本, 这样二教的共同内容会更多, 将增进二教的和睦和融洽,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虽然这个记载可能出现于两个世纪之后, 但比较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不仅如此, 赤松德赞还对有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苯教重要人物表示了公开的支持:赤松德赞曾经对象雄著名的苯教学者杰尔邦·囊协尔洛波有过四项承诺:允许来自象雄的苯教徒传承苯教;将雅隆索嘎赐给囊协尔洛波的家族顾瑞布部落;免除他的税赋并将他安排到赞普的右排座; (2) 建造一座象雄国王的金质等身像。(3) 可见赤松德赞为了传播佛教, 安抚苯教, 曾经可能软硬兼施, 恩威并用。但是, 王权和社会对苯教和佛教相互吸收的认可甚至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更多似苯似佛的文献的出现, 甚至出现了大量的伪托印度高僧和翻译家的伪佛经, 从当时的贝若杂纳 (公元八世纪) 开始, 到后世的琼波·那觉尔 (990-?) 、恰·译师曲杰贝 (1197-1264) 等学者, 都曾经带着文献清单专门到印度去确认和考证那些文献的真伪, 可见当时各种真伪文献的混乱程度, 这种混乱也引发了后世苯教与佛教之间和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争论, 这是后话。
赤松德赞灭苯之后, 佛教有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发展时间, 期间, 修建桑耶寺, 建立译经场, 大规模翻译佛经, 为佛教在吐蕃的大规模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以后的穆尼赞普等均以弘扬佛教为己任, 继续推行佛教的发展和普及, 尤其到了赤热巴巾时期, 极度尊崇佛法, 佛教僧侣深度参与到政权里, 赞普下令修改律法, 规定每七户人家供养一位僧侣的制度, 僧侣成为吐蕃王朝里新的贵族集团, 赤热巴巾以繁苛的律法将佛教的地位推向了新的高度, 将传播佛教的事业推向了极致。但是, 这种极端的做法引来的却是物极必反的效果, 导致之后的达磨赞普灭佛, 佛僧被杀, 佛寺被拆, 佛经被烧, 佛教遭受了被赞普正式引进吐蕃后的第一次法难。可是, 这次灭佛同样招致佛教徒的报复, 达磨赞普被佛僧弑杀, 吐蕃王朝因此分崩离析。
从赤松德赞的灭苯, 到达磨赞普灭佛, 经历了大概半个世纪。(4) 半个世纪虽然不短, 但在历史的长河中, 它只是个瞬间。苯教和佛教先后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 均经历了一个相对艰难的历史时期, 但同时, 因为随着吐蕃王朝的灰飞烟灭, 整个青藏高原群龙无首, 各种政治和宗教势力占山为王, 互不统属, 被藏史称其为“吐蕃割据时代”, 在这样的状况下, 王权对任何宗教传统的大面积强力传播已经结束了, 强权政治对任何宗教传统的限制和制衡也不复存在。这样的政治境遇为苯教和佛教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再次复兴的条件和机会, 因而, 苯佛二教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开始了艰难的复兴, 当然, 复兴的形式有所不同, 佛教以律宗为主要内容开始传播, 苯教则选择了发掘和传播伏藏文献为主要方式, 各自选择这两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均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
四、詹巴南喀与莲花生的关系及其演变
公元八世纪与赤松德赞同时的詹巴南喀生于西藏达波地区的一个穆氏家族, 因而也被称为穆苯·詹巴南喀。父名穆辛·达巴, 母名哒氏卡尔甲木。(1) 关于他的生平活动及其年代, 文献记载多有不同且都比较简略。但是, 各种历史文献的零星记载, 都说明公元八世纪确实存在过这么一位历史人物并对苯教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则是不争的事实。詹巴南喀和莲花生在佛苯冲突中的关系已经在本文中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二者曾经既是苯教和佛教相互对抗的领军人物, 又是相互融合的积极推进者, 既代表了两个对立的阵营, 又促成了苯佛两个宗教传统在吐蕃的第一次实质性融合。但是, 詹巴南喀和莲花生的关系在后来的新派苯教中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两位来自不同地方的毫不相干的历史人物在后弘期的伏藏文献中变成了父子关系, 莲花生成了詹巴南喀的两个儿子之一, 这样的关系逐渐得到新派苯教徒的普遍认可。
《雍仲苯教宏扬史》等苯教史籍认为, 在苯教受到迫害时, 穆苯·詹巴南喀藏匿了大量的苯教伏藏文献, 以免灭苯时被销毁。这些藏匿文献, 被后世的掘藏师们陆续发掘和传播, 这种说法为后世伏藏文献提供了正统的宗教出处, 苯教新派中著名的四化身即四位苯教掘藏师 (2) 发掘和传播的苯教伏藏文献就属于这一类, 成为苯教新派的主要文献。在这些文献中, 对莲花生的尊崇和供奉一直是有别于苯教传统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但令人新奇的是, 在苯教新派的这些晚期文献中, 出现了若干位同名的詹巴南喀, 即生于大食的詹巴南喀、生于象雄的杰尔邦·詹巴南喀、生于达波的穆苯·詹巴南喀, 有的文献中还提到过止贡赞普时期的一位詹巴南喀。这些不同年代的詹巴南喀则以同一个人物的不同化身出现, 更有甚者, 詹巴南喀与著名的莲花生大师之间的父子关系得到更加详细的描述和进一步的强化。比如, 《世续题记详传》记载詹巴南喀云游印度并与空行母沃丹巴尔玛结合并生了一个儿子, 是苯教大师才旺仁增, (3) 没有提及莲花生的只字片语。说明詹巴南喀与莲花生之间为父子关系的说法至少在廓波·洛哲托麦(1280-?) 发掘《世续题记详传》之后产生。从现存文献中看来, 最早出现二者为父子关系的文献可能是18世纪的苯教掘藏师桑杰林巴 (1705-1735) 发掘的《莲花生大师传记俱亮明灯》。(4) 之后, 就是法国藏学家布隆多夫人研究过的一部钦泽旺波 (1820-1892) 撰写的莲花生传。(5) 在布隆多夫人看到的这篇传记中, 第一章就记述了琼雅木科杰与恰尊贡玛结合后生下了詹巴南喀, 他云游印度, 与婆罗门种姓的尼玛宁波俄巴尔玛结合, 生下了两个儿子, 长子雍仲敦才 (即雍仲敦塞) , 次子白玛同卓, 后者就是白玛迥乃即莲花生。[11]据此, 我们可以看到, 在苯教新派的伏藏文献中, 公元十三世纪詹巴南喀还只有一个儿子即才旺仁增, 但到了十八世纪, 就开始出现了第二个儿子即莲花生, 中间相隔5个世纪。
在藏传佛教的文献中, 生命的诞生有胎生、卵生、温生和化生四种, 著名的莲花生就属于化生, 他被认为是诞生自一个莲花中间, 没有父母亲。这样的描述在藏传佛教徒中妇孺皆知, 莲花生这个名字本身就起源于这个故事。但这样的描述同样在苯教新派的文献中有了变化。根据桑阿林巴 (1864-?) 发掘的《詹巴传记雍仲秘密巨库》 (1) 记载, 杰尔邦·詹巴南喀诞生于古代象雄王国的琼隆银城, 即今阿里噶尔县境内的卡尔东遗址。他以各种化身云游大食、印度、南诏、五台山、勃律、格萨尔、吐火罗、克什米尔等。在印度, 与桑炯国王的公主沃丹巴尔玛结亲。在他们造访外象雄、中象雄和里象雄来到琼隆银城期间, 在一个秘密之处即雍仲丹贝扎普,从沃丹巴尔玛右肺诞生了童瓦准塞, 从左肺诞生了雍仲同卓, (2) 童瓦准塞即才旺仁增, 雍仲同卓即莲花生。在这个记载中, 莲花生既不是化生, 也不是胎生, 而是从左肺部生出来的, 更为重要的是, 他有父母亲, 不是化生, 完全有别于佛教传统中的描述。
也许因为莲花生大师从一束莲花中诞生的传说在西藏变得家喻户晓, 使苯教徒关于莲花生有父母并诞生自肺部的传说变得更加另类的原因, 新派苯教文献中还出现了对大师诞生自莲花的另一种解释, 根据一部叫做《历史明鉴》 (3) 的历史文献记载, 炯亚尔木廓和恰尊贡玛结合后诞生了詹巴杜堆, 又被称为拉钦·詹巴南喀, 或者炯亚尔拉钦廓邦。他与印度空行母沃丹巴尔玛结合后生下才旺仁增和雍仲同卓两个儿子。在印度一个叫做玛拉杂夏的地方有一个曾经转生过七世的婆罗门的尸体, 相传如果谁拥有这个尸体就会得到各种成就, 因而, 神、鲁 、人和各种鬼怪都想抢到这个尸体。空行母给詹巴南喀献上各种贡品以后, 强烈要求他降服各种神灵鬼怪并取得该尸体, 詹巴南喀应允前往, 但因他沉迷于美妙的音乐不能自拔而未能如愿, 空行母只得到尸体上的一根发丝。空行母因此示怒, 派兄长才旺仁增赴吐蕃教化众生, 而自己背负着弟弟雍仲同卓秘密远赴印度。詹巴南喀极力阻止未果, 空行母背着幼子愤然远行至一个叫做玛拉 () 的地方, 将幼子置于一绽放的莲花中后出去化缘。傍晚后因莲花合叶将幼子包在其中, 空行母回来未能见到幼子而到处寻找。第二天早晨, 一位印度国王的管家在采摘供奉神祇的莲花时适逢莲花重新绽放并寻得幼子, 因得自莲花中而赐名白玛迥乃即莲花生。从此莲花生在印度、萨霍尔和吐蕃等地传播宗教。这个故事很巧妙地将雍仲同卓与莲花生合二为一, 即说明了雍仲同卓就是莲花生, 又提供了他被称为莲花生的另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 可谓天衣无缝。
除了詹巴南喀以外, 公元八世纪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贝若杂纳也为苯教新派的形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起初从师詹巴南喀修习苯教, 后皈依佛门, 翻译经典, 成为著名的佛经翻译家, 功勋卓著。他因苯佛无别而受到苯教和佛教的共同拥戴。相传在赤松德赞灭苯时, 贝若杂纳将许多苯教经典藏匿起来, 被后世的掘藏师们发掘后, 成为苯教新派的重要经典。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勒乌摩崖石刻中的贝若杂纳完全是以苯教大师的身份出现就足以证明贝若杂纳历史文化身份的多样性。[12]
随着苯教新派的诞生及其发展, 对这个新派的称谓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最初, 苯教徒将这个新派称作即新教诲派, 与此相对应的传统苯教就被称为即旧教诲派。但是, 后来的著名学者夏尔杂·扎西坚赞等人认为这样的称谓不准确, 因为辛绕弥沃的教诲不应该有新旧之分, 这样的区别是因为伏藏文献被发掘的年代有先后所致, 因而, 应该称为即新藏派和即旧藏派。与此不同的是, 佛教徒一直将这两个派别称为即白苯和即黑苯, 认为新派苯教与佛教相近, 就用白色来表述, 而旧派苯教相对比较传统, 保持原有的特色, 距佛教较远, 因而被称为黑苯, 用颜色来表达他们的好恶。
五、结语
由于赤松德赞的灭苯, 公元八世纪的穆苯·詹巴南喀等人被强行改宗佛教的同时, 又没能放弃自己原有的苯教信仰, 为了顺应赤松德赞的强权和维持苯教的生存和发展, 苯教徒以尊崇莲花生为主要特征开始重新构建一个新的苯教传统, 成为后世与传统苯教相对应的一个新的派别。加上为了使佛教在吐蕃立足, 佛教徒借用莲花生的法力和声望对佛教进行的重新构建, 使其成为藏族历史上具有浓厚苯教色彩的地方化了的藏传佛教传统, 吐蕃的苯教和印度的佛教在青藏高原上第一次实质性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在这个吸收和融合中, 穆苯·詹巴南喀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为后世苯教和佛教两个传统的进一步融合奠定了基础。
在后期的苯教新派文献中, 莲花生和詹巴南喀变成父子关系, 这样的神话及其传播强化了莲花生在苯教新派中的存在甚至被信仰的合理性, 使苯教徒更加容易接受这位曾经极力灭苯的佛教大师, 进而使这位历史人物很快完成了在苯教传统中从人到神的演变过程。
原本在宁玛派的文献中被描述成化生即从一朵绽放的莲花中诞生的莲花生大师, 在晚期苯教的传记中变成从肺部诞生, 并与另一位苯教大师才旺仁增一起成为杰尔邦·詹巴南喀的两个儿子。逐渐在新派苯教的传统中, 不仅来自大食、象雄和吐蕃的三个詹巴南喀成为同一个灵魂的不同化身, 而且, 将杰尔邦·詹巴南喀的儿子雍仲同卓与莲花生理解为同一个灵魂的不同化身, 在各种文献中尽量将二者合二为一, 因而, 莲花生在新派苯教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产生了专门的修行传承及其法本。将莲花生的信仰与詹巴南喀的信仰有机地结合, 不仅使莲花生在苯教新派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逐渐成为苯教新派中的一个主要信仰对象, 而且成为苯教新派与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因为苯教徒对莲花生的信仰, 拉近了他们与藏传佛教徒之间的距离, 增加了苯教徒对藏传佛教徒的亲近感和亲和力, 淡化了苯教徒对于莲花生灭苯的痛苦的历史记忆。
从詹巴南喀和莲花生开始的苯教和佛教的相互冲突和吸收开始了长达一千多年的全方位融合, 使以苯教为单一信仰传统的藏民族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接受佛教以后造成的分裂开始重新整合, 随着佛教逐渐占有青藏高原的主导地位, 其教义也更加深入人心, 滋润着藏民族的心灵, 成为藏民族主要的信仰和哲学体系。随着苯教和佛教逐渐融合并深入人心, 一个以苯教信仰为基础, 以佛教信仰为主导的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以整合之后全新的面目逐渐出现在最近几个世纪的藏民族的历史上。詹巴南喀在这样的文化运动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为后世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呈现提供了重要的可能和条件。
任何民族的传统文化, 都承载着这个民族历史的文化积淀和整体的价值观, 并用这个传统价值观塑造着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 培育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心态, 规范着这个民族的行为方式。这种单一和完整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有着它特殊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佛教没有传入吐蕃之前的苯教文化及其价值观就是这样。但是, 当另一个文化传统的传入, 尤其是大面积的强势传播, 必将对原有文化传统形成挑战, 甚至对原有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形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佛教传入吐蕃, 尤其是赤松德赞灭苯及其后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当原有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传统不得不共存时, 虽然会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或者文化自身的内涵等各种社会和文化原因, 两者之间会发生许多不平衡, 但免不了相互之间的影响和渗透, 尤其是一些发展历史久远、思想根基深厚、理论体系完整的文化传统, 都有坚韧的延续性、顽强的渗透力和宽厚的包容性, 苯教和佛教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 从公元七世纪佛教传入吐蕃以后, 苯教与佛教在对立中相识, 在冲突中融合, 各自都以不同程度的牺牲为代价融入到对方中, 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局面, 苯教因此被称为雍仲苯教, 佛教也因此被称为喇嘛教或者藏传佛教, 最后完成了藏民族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的重新整合, 这种整合的起源就是在公元八世纪的苯佛关系, 苯教新派就是在这种整合中产生和形成。当一个宗教传统的发展遇到阻力, 与强势文化传统之间发生冲突, 它的生存能力就取决于它有没有另辟蹊径、自谋生路的自我调节功能。公元八世纪的苯教以其顽强的生命力,接纳莲花生、学习佛教、改变形式、继续传播, 苯教新派就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注 释:
1 国际敦煌项目 (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网页, PT.1287, 此段引文由作者汉译。http://idp.bnf.fr/pages/collections_en.a4d
2 《雍仲苯教宏扬史》 (藏文版) , 见《苯教史料汇编》 [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177页。此书另一个书名为:的抄本现藏于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 明确注明是詹巴南喀的作品, 此书成书于公元十至十一世纪。
3 德吉编《巴协汇编》 (藏文版) , [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9年版:第24页。此段引文由作者汉译。
4 (1) CHOIX DE DOCUMENTS TIBETAINS, pp.1-74.CONSERVES A LA BIBLIOTHEQUE NATIONALE, Tome IV CORPUSSYLLABIQUE.Par Yoshiro Imeda, Tsuguhito Takeuchi, Izumi Hoshi, Yoshimichi Ohara, Iwao Ishikawa.2001, Institut de Recherches sur les Langues et Cultures d’Asie et d’Afrique (ILCAA) and Universite des Langues Etrangeres de Tokyo.Tokyo.
5 (2) 《雍仲苯教宏扬史》 (藏文版) , 见《苯教史料汇编》 [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124-125页。此段引文由作者翻译。
6 (3) 《雍仲苯教宏扬史》 (藏文版) , 见《苯教史料汇编》[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189页。此段引文由作者翻译。
7 (4) 《雍仲苯教宏扬史》 (藏文版) , 见《苯教史料汇编》[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188页。此段引文由作者翻译。
8 (5) 夏尔杂·扎西坚赞.《西藏本教源流》 (藏文版) , [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5年版:第246-247页。此书通常也被汉译成《嘉言库》。
9 (1) 南班即藏文之译音, 为的缩写, 意为强行改宗, 为缩写, 即佛教之义, 合成后就是被强行改宗佛教的人。
10 (2) 襄为藏文之译音, 是苯教特有的一种法器, 为一种单叶钹。在许多场景下, 襄代表苯教。
11 (3) 凯珠·隆多坚措.《教法史智慧辨析澄水珠宝串》 (藏文版) , 见《冈底斯苯教文献丛书》, 第一集:《教主本生传和历史部分》 , [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0年版, 第498页。温嘉·伦珠嘉措认为其成书年代为作者三十九岁时, 应该是1917年。见温嘉·格勒伦珠嘉措编写《本教历史年鉴》 (藏文版) [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9年版:第146页。
12 (1) 《雍仲苯教宏扬史》 (藏文版) , 见《苯教史料汇编》 [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187页。此段引文由作者汉译。
13 (2) 指国王议政时大臣和其他重要人物的座位排序, 排在国王右边的座位比左边重要。
14 (3) 囊塔·丹增尼玛编.大圆满象雄耳传经四部经续 中《大圆满象雄耳传经之苯没有被毁的原由》, 成都:象雄文明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26、194页。
15 (4) 因为其间的几位赞普生卒年代说法不一, 又非本文关注的主要议题, 故其具体多少年份不做具体考证。
16 (1) 丹增南达《觉悟上师之生平白色莲鬘》 (藏文版) , 见《曼日经师丹增南达全集》 (藏文版) 第二集, 加德满都赤丹诺尔布泽,图书馆第六套文集。2005年版:第264-265页。
17 (2) 洛丹宁波 (1360-?) 、米秀多杰 (1595-?又称协秀·雍仲杰波) 、贡珠扎巴 (1700-?) 和桑杰林巴 (1705-1735) 。
18 (3) 《世续题记详传》, 十三世纪苯教掘藏师廓波·洛哲托麦 (又称杰尔·托麦) 的伏藏文献。见《苯教史料汇编》 [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 2010年版:第269页。
19 (4) 苯教大藏经《丹珠尔》目录提供了两个似乎是不同简称的莲花生传记, 但均为桑杰林巴的伏藏文献, 即033:《莲花生大师传记》和034:《莲花生大师传记俱亮明灯》, 但为两种不同书名所提供的全称则是相同的:可见是同一个文献, 并注明了前者只有从41至78章, 后者只有80至111章, 说明收入苯教大藏经《丹珠尔》中的莲花生传记并不完整。见ACatalogue of the New Collection of Bonpo Katen Texts, pp.324.Edited by Karmay G.Samten&Yasuhiko Nagano,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Osaka, 2001.
20 (5) mK hyen-brtse'i dbang-po:La biographie de Padmasambhava selon la tradition du bsG rags-pa Bon, et ses sources", in Gnoli, G.&L.Lanciotti (éds) ,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Serie Orientale Roma LVI, 1, Roma, IsM EO:111-158。文中将这篇传记的题目译为《根据苯教密咒的传说而阐述的耆那之子莲花生简传》, 并说明:“各页背面于边缘处有如下标记:‘掘藏宝库, 以苯教徒的方式阐述的大师传, 钦则’”。说明布隆多夫人看到的并不是同一个版本。但这篇论文没有提供传记书名的藏文原文。这篇论文被耿昇先生汉译并收入《法国藏学精粹》第二集中出版, 其中“耆那之子”似乎是藏文的翻译, 如果是, 在此应该译为“佛子”, 而不应该是“耆那之子”。
21 (1) 桑阿林巴伏藏文献《詹巴传雍仲秘库》, 全称为:八卷本, 贡结寺木刻版。
22 (2) 桑阿林巴伏藏文献《詹巴传雍仲秘库》, , 贡结寺木刻板:第103页背。
23 (3) 《历史明鉴》 , 藏文手抄本。作者不详。
原刊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201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