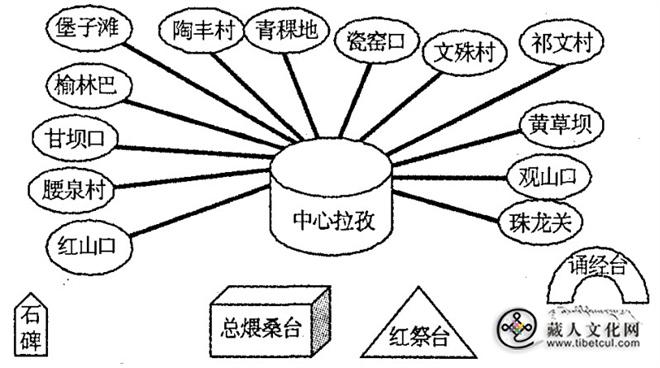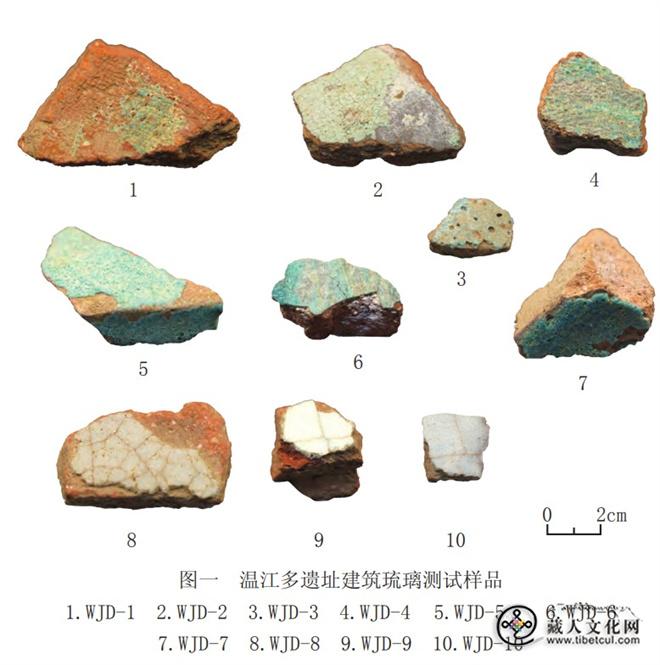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摘要:文章对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的苯教研究进行了详尽的介绍, 并就苯教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了具体的分析, 旨在深化学术界对苯教及其文化的探讨。
关键词:苯教; 藏学研究; 象雄文明;
有关苯教文化的研究历来是我国藏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虽然苯教文化是藏民族的本土文化, 从时间上讲, 上可以追溯到远古的象雄文明, 下可以论及21世纪的苯教及其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从空间上讲, 它遍及整个青藏高原, 曾经是青藏高原上唯一的宗教信仰, 可以说在藏民族的历史上, 曾经全民信仰的宗教也只有苯教。但是, 从公元11世纪开始, 佛教在青藏高原逐渐占有主导地位以后, 苯教这个曾经主导藏民族上千年的宗教信仰系统开始走向衰败, 逐渐成为一个只能在偏远地带生存的小型宗教。尽管如此, 不仅现存的苯教寺院、苯教文献、苯教徒和苯教的活动一直影响着藏民族, 更重要的是, 在一千多年苯教和佛教相互斗争和相互吸收中, 融入佛教的苯教文化内容仍然通过藏传佛教的文献、宗教活动和宗教观念在间接地影响着这个民族。因此, 苯教虽然在藏区已经变成一个弱势宗教, 但苯教及与其相关的文化传统对藏民族的心里素质、文化心态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却一点也不亚于佛教。
自从苯教在青藏高原的社会地位开始滑坡以后, 苯教逐渐躲到比较偏远的、僻静的、远离地区政治文化中心的地方休养生息, 保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而, 苯教文献的出版和传播也因这种大气候的影响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这种情况造成了苯教历史上除了两套仅有的苯教大藏经及少量的文献曾经木刻出版以外, 绝大多数文献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传世, 苯教文献的发行量显然无法与藏传佛教的文献相比。实际上这也是我国的藏学研究未能更多地关注苯教文化的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后, 我国藏学界才开始有了一些研究苯教文化的学术文章。相比而言, 西方学者的研究比国内学者要早一些。石泰安、霍夫曼和杜齐应该是先行者, 从斯耐格若夫就开始了对苯教文献的研究, 他们的研究为以后桑木丹、克威尔诺和布隆多夫人等人更深层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 南喀诺布和丹增南达也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与国际藏学界的研究成果相比, 目前国内藏学界对苯教文化的研究尚欠规范化和系统化, 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无法企及。正因为如此, 本人在从事苯教文化研究的同时, 一直想编一套苯教文化研究的论文集, 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苯教研究方面的成果展示给大家, 也算是对我国藏学界研究苯教文化成果的一个回顾和展示。
在苯教文化研究中, 象雄文明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不仅受到从事纯粹藏学研究者的青睐, 从事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们亦积极加盟, 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在我国藏学界, 最早关注象雄文明的文章应该是笔者于20世纪80年代用藏汉两种文字发表的《古老的象雄文明》1, 现在看来这篇文章过于简单, 不够规范, 有些观点也不够成熟, 但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万象更新, 新中国的藏学研究刚刚起步, 许多领域的文章少而又少, 苯教和象雄方面的研究更是无人问津, 因而, 这篇文章的主题及其观点在当时略感新鲜, 文章发表后立即在藏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它虽然不是作者文章中最好的, 但肯定是被引用最多的文章, 对象雄及其古代文明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 作者对象雄的文明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先后用中文发表了《冈底斯神山崇拜及其周边的古代文化》和《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等文章, 用英文发表了《冈底斯山地区曾经是古代喜马拉雅文明的中心》2的论文, 通过认真的研究, 笔者对象雄文明在古代藏族文明的发源地及其与古代波斯文明、天竺文明、雅隆文明和中原文明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认为, 冈底斯山及其周边地区曾经是古代喜马拉雅文明的中心, 这个起源于冈底斯山地区, 以苯教文化为主线的文化传统才是藏族文明的主要源与流, 这个在我国西藏本土起源的文化传统对藏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顿珠拉杰在完成了一次象雄文化遗址考察后, 发表了《西藏西北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考察报告》, 在对苯教文化所进行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他对西藏西北地区象雄文化遗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将这些遗迹与苯教文献中出现的一些零星的记载进行了对应和考证, 认为, 这些古代遗迹, 特别是其中出现的白石碑现象是象雄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佛教传入之前就已在西藏盛行, 而且这些白石碑与寺庙、佛塔和陵墓有着密切的关系。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是霍巍, 他是一位勤奋的考古学者, 在吐蕃墓葬研究方面卓有成效。他将考古学的研究建立在已有的象雄研究的基础之上, 认为, “象雄与苯教文化并不是从一开始便具有很高的水平, 而是通过长期的发展, 尤其是通过同周边地区所进行的文化交流, 并大量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因素之后, 才得以从一个游牧的“骑马民族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部落联盟国家”。“以西藏西部地区为其统治中心区域的象雄王国, 正是以其便利的地理与交通条件, 沟通了与外界的联系与交往, 方才成为西藏高原早期的文明中心”。对象雄文明在古代文明中的作用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另外, 石硕还以西藏文明东向发展研究为突破口, 对吐蕃时期象雄、吐蕃和苏毗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和发展作了深入的研究, 对发祥较早的象雄文明未能主宰吐蕃高原, 而起步较晚的雅隆文明统治青藏高原的历史原因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述。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近年来, 我国藏学界对象雄文明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其中有些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但不可忽略的是, 国际藏学界对象雄文明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丹增南达以其对苯教文献令人惊叹的熟悉程度对古代象雄所作的研究和阐述已经为西方藏学界所熟悉;南喀诺布教授一系列有关象雄文明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独树一帜, 尤其是其《古代象雄与吐蕃史》以深厚的文献功底对象雄文明进行了深入研究, 藏文版已经在国内出版, 英文和汉文的译本也即将问世;卡尔梅·桑木丹博士在藏学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已经成为西方藏学界的典范。此外, 丹·玛尔丁、亨克·布莱孜尔等依据文献进行的研究亦卓有成效, 细致入微。近年来, 美国学者约翰·布赖查先生对象雄的研究异军突起, 凸显了他的功底。他多次徒步走遍西藏西北部, 对存留西藏的古代象雄遗迹进行了至今最为详细的考察, 结合这些考察, 对苯教文献中的有关古代象雄文明的记载进行了尽可能的考证和研究。同时, 他还对神山遗迹和原始苯教中保留下来的拉巴进行了大量的访问和考察, 其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相比而言, 我国藏学界专门研究象雄文明的人员极少, 业余研究人员仅靠兴趣写几篇文章, 研究不成体系, 形不成规模, 更没有后续力量。一个领域的研究, 一旦不能持续进行, 就无法进一步深入下去。
苯教是青藏高原发展历史最长的一个宗教, 因而苯教史一直是苯教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马长寿的《苯教源流》[1]先走一步。他的学术视野比较开阔, 首先引用了查理斯·比尔的《西藏的宗教》[2]和大卫·聂尔的《林格萨尔的超人生活》[3], 还谈到斯拉日尔加所著的《苯佛之别》3, 这部书应该是扎敦·格桑丹贝坚赞所著的《苯佛之别》, 因为扎敦喇嘛的活佛名就是斯拉, 至今沿用, 而且他确实撰有一部不太长的《苯佛之别》。扎敦喇嘛是夏尔杂·扎西坚赞的高足, 他众多的著述在康区苯教界享有盛名。马长寿选用这样一部专著来阐述苯教也足显其颇具慧眼。他还访问过多丹寺4的一位苯教活佛和巴旺的一位苯教僧人, 根据后者的帮助, 他描述了巴旺即今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境内墨尔多及其周边的神山。最后用专章谈及苯教祖师辛绕弥沃。他还注意到在当地的苯教信仰中, 僧人虽然很重要, 但在苯教徒的日常生活中苯教密宗师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大约一大寨之内必有一名或二名 (巫士) 。盖喇嘛虽重要, 尚不必日日请求之, 而此富有地方性之巫士, 则为须叟不可离也”。马长寿第一次对苯教进行了粗略的考察, 简单地勾勒了苯教的轮廓, 有其一定的开创意义和学术价值。此后, 李安宅发表《苯教——说藏语人民的魔力般的宗教信仰》[4]一文, 该文主要依据土观的《佛教源流》和《拜玛嘎塘》两部佛教徒著作来谈苯教, 涉及的内容很少。文中还利用苯教历史三分法来试图叙述苯教的历史分期, 这显然是来自土观的著述, 除了将苯教九乘的标题翻译成汉文以外, 基本没有新意。
1981年, 孙尔康发表了《苯教初探》, 为改革开放后的苯教研究拉开了帷幕。他利用汉文文献中有关苯教的零星记载探讨了苯教的起源及其原始崇拜, 用土观法师《宗教源流》的资料阐述了苯教的历史分期, 最后对佛苯斗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并试图以此来阐释苯教在佛苯斗争中败北的历史原因及其社会影响。认为苯教“绝不是外方移植到高原来的宗教”;“吐蕃后来采取的‘崇佛抑苯’政策, 只不过是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 成为加速苯教衰落的主要条件, 但不是根本原因”。这样的观点为当时的学术界带来了新颖的思想火花, 引发了人们对苯教历史命题的新的思索。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 我国藏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相继有了一些新成果, 苯教研究也一样。陈士果、闵文义、李家瑞、吴均、郭卫平和曾国庆对苯教在川西北、江河源地区和白龙江流域的发展作了考察和描述, 专门讨论了苯教在安多地区的流传及其现状, 将苯教在藏族各个地区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呈现在学术界的视野中, 凸现了安多地区的苯教的现状及其学术意义。才让太利用苯教文献, 试图勾勒七赤天王时期的苯教状况。石硕对七赤天王的王权与苯教神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张云对吐蕃时期苯教的社会地位进行了评价, 尤其是对吐蕃与波斯祆教的关系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他从吐蕃早期的民间故事中寻找古代波斯文化的蛛丝马迹, 试图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苯教与中亚文化的关系进行分析, 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当时苯教研究的领域, 并对如“辛”与祆教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上述研究对苯教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可惜的是, 晏春元的《苯教起源地象雄为嘉绒藏区》的学术观点不可谓不新, 但因为作者不懂藏文, 对有关象雄和嘉绒的记载产生误解, 导致所得出的结论无法坐实, 将嘉绒与历史上的象雄混为一谈, 堪称败笔。总之, 在苯教历史的研究中, 因为对苯教文献的了解不够, 所涉猎的内容仍然非常零散, 不成体系, 始终未能勾勒出一个比较清楚的苯教发展史。
在苯教教义方面, 丹珠昂奔的《原始苯教与藏民族早期的伦理观念》一文, 以《什巴问答歌》等民间流传的道歌为主要素材, 结合藏文文献的记载, 对藏族古代的伦理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展示了早期苯教教义在藏族古代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谢继胜的《藏族萨满教的三界宇宙结构与灵魂观念的发展》一文, 试图将原始苯教中的三界宇宙结构与灵魂观念的发展和演变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诺布旺丹的《苯教大圆满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对苯教传统中大圆满的产生和发展, 及其与宁玛派大圆满的关系均作了有益的探索, 认为苯教大圆满是原始苯教与异源文化交流的结果。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 推动了对这个领域的进一步探索和发展。
在苯教神灵方面, 丹珠昂奔的《藏族神灵论》第一次对藏族古代宗教中的神灵系统进行了梳理, 尝试着对原始宗教中众多的神灵的产生、演变、地位及其功能进行科学的描述, 成为我国藏学界对原始宗教神灵系统研究的探路之作。格勒连续发表两篇论文, 以《黑白花十万鲁经》5为主要素材, 对该书所反映的原始苯教的诸神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可惜的是此后他对苯教的研究基本终止。
在苯教文献方面, 笔者的《苯教文献及其集成》和《苯教〈大藏经〉的形成及其发展》两篇论文, 前者对苯教五大伏藏文献群的产生、发掘、构成及其流传进行了研究, 对五大伏藏的传播途径及其重要人物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理清了其基本的历史线索。后者第一次将以五大伏藏为主要内容的苯教《大藏经》的形成、目录、抄本、木刻等历史内容穿起来, 并将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的苯教《大藏经·甘珠尔》瓦穹版抄本、阿拥版、温伦版、拉色版以及苯教《大藏经·丹珠尔》的编辑和出版及其版本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严格的学术描述。
苯教寺院一直是苯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的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 发表了一些重要著作, 可惜的是有些重要成果的汉文版尚未面世。在汉文成果中, 因为涉及嘉绒地区的苯教信仰、乾隆时期的金川战役等重大历史事件, 熊文彬的《广法寺与雍仲拉顶寺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该文第一次对广法寺和雍仲拉顶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研究和力求准确的学术描述, 引经据典, 观点坐实。笔者对作为青藏高原寺院庙堂前身的苯教塞康建筑的起源、形成、演变及其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从杜耐到塞康、拉康、杜康和寺院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 并将塞康文化的演变和现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 把塞康文化这个古老的文化传承及其在青海湖地区的残存第一次展示给学术界, 引发了学术界的兴趣。
在岩画研究方面, 汤惠生的《青藏高原的岩画与苯教》一文, 对青藏高原岩画中的许多重要内容进行了研究。作者在长期进行的调查和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故对与苯教有关的主题研究颇有深度。其后, 青年学者张亚莎的《西藏的岩画》更广泛地涉及了岩画中与苯教有关的主题, 结合历史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 对青藏高原古代先民的迁徙、原始崇拜及其与古代象雄王国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 颇显功底。
苯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是至今学者们颇费笔墨的一个话题, 首先学者们深感困惑的是苯教与民间宗教概念的界定及其学术分野, 虽然有较多的论文发表, 但至今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好在大多数学术论文更多地倾注到对民间宗教现象的描述及其社会功能的研究等方面。林继富的《牦牛与藏族原始文化》一文虽然未能充分利用苯教文献对牦牛崇拜的起源做出准确的解释, 但对牦牛崇拜现象进行了分类和研究, 尤其将牦牛崇拜与古代赞普上天下地时的天梯现象联系起来, 认为“藏族牦牛崇拜是牦牛信仰最集中、最主要的文化表露”。达尔基的《雍仲苯教圣地墨尔多山》一文考察了神山信仰这一青藏高原古老的信仰方式在嘉绒地区墨尔多神山的具体形态及其宗教功能, 用身临其境的调查和学者的独特视角对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研究, 认为“墨尔多神山是雍仲苯教善男信女们心目中的灵魂支柱”, 形象地描述了根植于民间的古老的圣山信仰在今天的青藏高原仍然具有的不可撼动的稳定性及其普遍性。
以上大量的事实表明, 半个世纪以来, 我国许多学者通过亲临调查、认真研究和辛勤笔耕, 将苯教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但由于种种原因, 一些不足和失误也随处可见。比如将藏文klu翻译成“龙”就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笔者没有考证过这个错误何时出现, 但将苯教文献klu vbum翻译成《十万龙经》并被广泛引用导致这个错误被迅速扩散, 至今仍有许多人以讹传讹, 甚至衍生了许多错误的概念。其实, 在苯教文献中, klu是栖息于岩石、树林、山川、河流甚至大海里的种类异常繁多的众多生灵的总称, 在汉文化中没有一个可以相对应的词汇, 只能音译成“鲁”, 而“龙”在藏文化中有其相对应的名称即vbrug, 其文化表象和文化内涵及其文化功能均与汉文化中的“龙”基本相似, 因而“鲁”和“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龙”有时可以被认为是“鲁”的一种, 而决不能等同于“鲁”。还有, 将khyung翻译成大鹏鸟同样也是个明显的错误, khyung是远古喜马拉雅文明中一个特殊的神鸟, 虽然在喜马拉雅邻近的各种古代文明中有不同的形态, 但这个神鸟在南亚文化中被称为Garuda, 它的最初起源是古天竺婆罗门教中遍入神的坐骑, 与湿婆和梵天一样都与冈底斯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个神鸟飞临象雄的卡佑并生出白、黑、花三色卵宣告了古象雄穹 (khyung) 氏部落的诞生。而汉文中的大鹏鸟始见于《庄子》的《逍遥游》:“背若泰山, 翼若垂天之云, 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 绝云气, 负青天, 然后图南”。这里的大鹏是一个状若泰山, 翼可遮天蔽日的巨型神鸟。成语鲲鹏展翅、鹏程万里皆由此出。由此可以看出, 虽然都是神鸟, 但起源、形状、角色、功能均不同。随着佛教的引进, 天竺的Garuda传到了汉地, 同样被翻译成大鹏鸟, 可惜的是, 这样的译法将两个文化传统中不同的文化特质混为一谈了。所以, khyung也只能音译为“穹”, 而决不能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文化概念等同起来。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就是苯教历史三段论, 即将苯教历史分成笃尔苯、恰尔苯和居尔苯三个历史阶段的观点, 由于对这个学术观点理解的偏差导致了许多不准确的学术观点。在整个前宏期和后宏期初期, 苯教和佛教之间长期的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 造成了这两个宗教传统之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局面, 因而互相指责对方剽窃自己的内容是这些争论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佛教学者止贡·玖丹贡布于公元12世纪下半叶在他的著作《惟义经典》 (dgongs gcig yig cha) 中提出了著名的苯教历史三段论。但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学经制度及其学位晋升制度的不断完善, 学僧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佛教经院哲学的修习上, 很少有人关注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苯教, 直到公元18世纪, 这个三段论并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因而, 当土观法师重新用这个三段论来叙述苯教历史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早在600年之前就有人提出了这个学术观点, 尤其是他关于苯教历史的章节被达斯翻译成英文并于1881年发表时, 西方学界将其当成土观的论点广泛引用。同样, 土观法师的宗教源流汉译本于1980年问世, 藏文本于1984年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面世。20世纪80年代, 当时藏族历史宗教方面的资料严重短缺, 苯教文献的出版更是寥若晨星, 土观法师的名著用藏汉两种文本几乎同时出版, 立即受到了中国藏学界的高度关注。在没有苯教文献作为参考的情况下, 土观法师有关苯教历史的三段论先入为主, 成为此后描述苯教历史时被广泛引用的著名观点, 并逐渐被藏学界所熟悉。虽然, 法国学者石泰安先生于1988就发现并指出这个论点来自12世纪的止贡·玖丹贡布, 而非土观法师, 但他的论文是用法文发表的, 国内学界很少有人知晓。随之, 旅意著名藏族学者南喀诺布教授也在他的《古代象雄与吐蕃史》中提到这个三段论的起源, 但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 这个三段论是佛教徒学者给苯教历史所下的一个定义, 而非苯教对其历史的正统描述, 苯教徒学者并不承认这个三段论的合理性。而且这一描述尚欠连贯性和完整性, 尤其缺乏苯教历史发展的主线。由于历史的原因, 止贡·玖丹贡布只是直观地看到并强调了苯教内容中的非苯教成分及其对佛教的吸收, 但没有注意到或不愿注意到, 苯教同样是一个有独立的创始人、完整的神系、繁杂的仪轨、浩繁的文献和悠久的历史这样一个自成系统的信仰传统的事实。这个三分法被广泛地引用, 导致对苯教史的许多不必要的误读。关于这个三段论的由来、涵义及其演变过程, 本人另有专文讨论[5], 不再赘述。
在评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苯教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在很多方面仍显不足。首先, 在苯教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 仍然有大量的文献, 尤其是手抄本文献散失于民间, 未能得到整理和出版, 这些散失于民间的文献有失传的危险, 亟待抢救;其次, 对那些已经整理和出版的文献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 这些文献中绝大多数是手抄本, 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还是珍本甚至孤本,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虽有幸面世, 却无人问津, 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再次, 苯教研究队伍需要培养和壮大, 目前我国苯教研究没有一个成形的队伍, 只有两三个专职研究人员, 加上别的藏学研究者当自己的研究涉猎到苯教时撰写少许有关苯教的学术文章。当然, 近年来苯教徒自身的研究力量有所发展, 有一部分年轻的僧人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有的甚至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
纵观我国藏学界对苯教文化的研究, 其学者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群体, 即用藏文发表学术成果的学者和用汉文发表学术成果的学者, 因为前者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藏族, 具有熟悉藏文文献、了解苯教习俗、因语言等便利条件而调查方便等优势, 但也具有教派偏见影响学术观点、缺乏研究方法和手段等不利因素。后者具有无教派偏见、掌握研究方法和手段、学术视野开阔等优势, 但也具有不熟悉藏文文献、因语言不同调查不便、不了解苯教习俗等不利因素。因而, 这两种文字的研究成果也有不同的特点, 这些成果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也因此有所不同。因为所涉及内容的原因, 这里将以汉文发表的研究苯教的成果为例, 谈谈这些论文的特点。
第一、从理论上, 我国的宗教学理论基本上是从前苏联接受的, 前苏联的宗教学研究固然有很多方面的成就, 但其研究原始宗教的理论和实践基本上基于对西伯利亚各种宗教的研究之上的, 他们总结出来的几种分类模式即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等就成为前苏联研究原始宗教的一个思维定式。从20世纪初, 马克思和列宁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精神导师, 尤其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 完全照搬了前苏联的许多学术理论, 宗教学研究的理论就是其中之一。中国起初翻译前苏联的宗教学理论著作以及以此研究的西伯利亚萨满教的成就, 进而将这个思维定式套用在中国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的理论和研究实践上。由于对革命导师及其苏联革命精神的敬仰和膜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凡是从前苏联学到的理论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前苏联的宗教学理论也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我国各民族宗教的理论基础, 进而机械地认为所有的原始宗教都不外乎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等几种模式。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 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民间宗教都一律被分类成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来进行叙述和研究。这样的思维定式和学术研究方法在研究西伯利亚的宗教时也许合适, 但是当它被机械地套用到中国各民族的原始宗教研究时并非适合。尤其像苯教这样既有原始宗教的成分和特点, 又具有系统宗教的几乎所有的特点和成分的宗教时, 就显得尤其不合适宜。即便就是在研究原始苯教成分时, 它的许多内容都与西伯利亚的萨满教并不总是雷同。显然, 原苏联的宗教学理论早已不适应中国的宗教情况。改革开放以后, 从马克斯·韦伯等欧洲经典宗教学家的宗教学理论著作到现代欧美新兴的宗教学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 逐渐开始影响中国的宗教学研究, 中国内地的民间宗教和少数民族原始宗教研究也开始逐渐摆脱原苏联的研究模式。但到目前为止, 用汉文研究苯教的学者群体仍然没有摆脱这个模式, 因为他们大多数不熟悉有关苯教的藏文文献, 对作为原始信仰的原始苯教有所了解, 但对作为系统宗教的苯教的认识仍然非常有限, 因而, 除了极个别学者以外, 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仍然局限在作为对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的苯教的描述上, 或者利用一些熟悉藏文的学者的已有研究成果来阐释象雄文明和苯教信仰中的诸多问题, 无法涉猎苯教的教义、仪规、历史、文献等比较重要的主题, 更无法对苯教进行全面的和宏观的描述。
第二、用汉文撰写研究苯教论文的学者群中, 还有一些较年轻的藏族学者, 虽然他们中大多数都有佛教家庭背景, 但因为他们绝大多数人接受过高等教育, 基本上没有藏族固有的教派偏见, 能够很平和地看待苯教与佛教的关系, 以及苯教对藏族文化的影响, 因而他们也越来越认识到苯教在藏族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地位。本民族学者具有这样的认识加强了学术界对苯教的重视, 也淡化了藏民族固有的歧视苯教的宗教偏见, 这一切都反映在他们的学术成果中, 自然也促进了苯教研究的健康发展。
第三、因为语言的限制, 一些年轻藏族学者不仅无法更深入地接触苯教文献, 同样也无法及时了解用藏文发表的研究成果, 因而他们无法及时吸收藏文研究成果中的优秀部分, 导致他们的一些研究有重复之嫌, 在一些藏文研究成果中早已解决的问题上进行重复劳动。另外, 因为苯教文献没有汉译, 只能通过汉译的佛教历史文献中有关苯教的零星记载和一些二手资料, 研究的内容比较零散, 不成系统。但这个群体能够较好地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 因为他们中很多人可以直接阅读外文, 并且许多外文研究成果已经翻译成汉文发表。还要说明的是, 虽然这个群体较少有宗教偏见, 但因为苯教文献很少被翻译成汉文, 他们只能利用翻译成汉文的具有较深宗教偏见的佛教历史文献来认识和研究苯教, 因而, 他们也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佛教徒原有的一些宗教偏见, 并习惯于先入为主地认同佛教徒的一些宗教偏见, 不利于对苯教的正确认识。
本文对用汉文发表的苯教研究成果进行一个粗略的回顾, 旨在希望苯教研究这个学术研究领域能够更加活跃, 出现更加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民族学研究集刊, 1943, (3) .藏事论文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2]The Religion of Tibet by Charles Bell.
[3]The Superhuman Life of Gesar of Ling by Al-exandra David-Neel.
[4]西南人类学 (英文版) , 1948, (4) .李安宅藏学文论选[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2.
[5]才让太.苯教历史三段论之由来及剖析[J].中国藏学, 2008, (4) .
注释:
1此文汉文版发表在《西藏研究》, 1985年第 (2) 期, 发表时遗漏“的”字, 成为“古老象雄文明”。
2Kailash Area was the Center of Himalayan Civilization, 首先在2008年6月在法国召开的国际苯教学术讨论会上宣读, 即将发表在意大利中远东研究院的学术刊物East & West (《东方与西方》) , 因为是用外文发表的, 故没有收录在这个论文集中。
3原文作《十万龙经》。
4原文为bun tsio znam i, 没有翻译出含义, 按照现在的撰写法应该为Bon chos rnam dbye, 应该翻译为苯佛之别。
5日道尔丹是rtogs ldan的音译, 今称为多丹寺或卓登寺, 离阿坝州阿坝县所在地只有5公里。
原刊于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200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