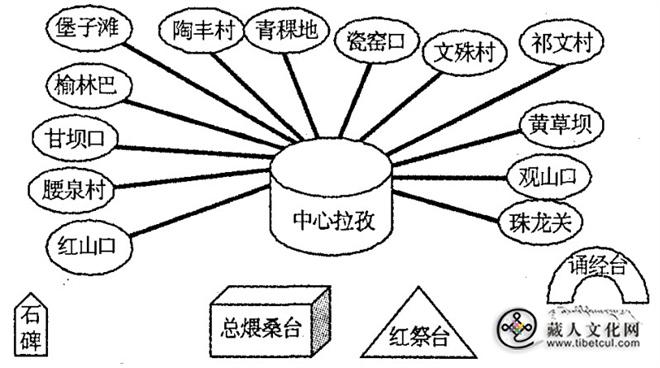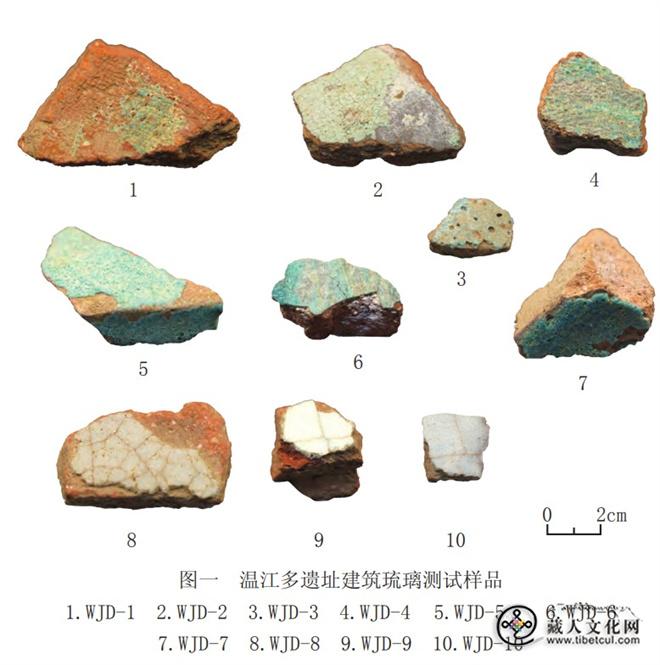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曾晓鸿
摄影:曾晓鸿
摘要:大通老爷山花儿会是青海四大花儿庙会之一,在河湟民间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本文从老爷山花儿会的起源与发展、老爷山花儿会的当下境况、花儿会演唱内容及曲令特点、基本功能等五个方面开展田野作业,获取第一手资料,进而从整体上把握老爷山花儿会的文化语境与民俗意义。
关键词:老爷山花儿会;当下境况;演唱内容;曲令特点;基本功能
引言
大通地处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北依祁连山余脉达坂山,南靠省会西宁市。全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2280~4622米,属典型的高原大陆性气候。作为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上的一座重镇,大通所在的北川河流域曾为古丝绸之路的南辅道,因而历史文化丰厚,文物古迹众多。纵观历史,大通属于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交流碰撞的文化地带,随着不同民族间的相互交融,瑰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艺术和民间文化艺术逐渐得以沉淀,从而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回、土、藏、蒙等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分布格局。县城境内的老爷山因其便利的地理位置,浓郁的宗教氛围,再加上久负盛名的“花儿”会,一度成为大通旅游宣传的文化名片。大通也因此被追溯为“河湟花儿”的发祥地之一,享有“花儿之都”的美誉,先后两次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花儿)之乡”。2006年,老爷山花儿会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老爷山位于大通县桥头镇北川河畔,原名“元朔山”,山势呈西北东南走向,高差悬殊,主峰海拔2928米,相对高度差达486.5米。由于它在历史上是扼守西宁的北部屏障,故而赢得“北武当”之誉。又因山顶建有大元宫,庙内塑有关公像,因此得名“老爷山”。老爷山北面与牦牛山相向,西面和娘娘山相望,三山对峙耸立,将桥头县城围在其中,形成一个山间盆地。山上古庙星罗棋布,一路数来,有药王庙、玉皇宫、百子宫、柴家大殿、无量殿、古塔、七真祠、太元宫等,这些庙宇建筑错落有致,绿树掩映中偶现红墙绿瓦,与老爷山自然景观浑然天成。老爷山最早因道教建筑而著名,供奉在柴家大殿内的真武大帝是镇守北方的武神,被民间认为是当地的保护神,故而备受崇信。每年六月举行的朝山会活动,因其规模较大、规程繁多、仪式神圣而吸引了广大民众参与其中,以此为依托的老爷山花儿会,更因其浓厚的文化意蕴和诗意的民间狂欢而声名远播。
一、老爷山“花儿”会的起源与发展
老爷山花儿会起源何时,并无文献记载可考,学者大都根据已知花儿研究成果和与之相关联的民间口传资料和民间习俗中获取线索,推断其肇始和发展脉络。
(一)“花儿”会的起源
1. 民间传说与“花儿”会
民俗学者万建中认为,“传说也是一种历史话语,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对所记忆的历史事实的阐释。”老爷山花儿会究竟缘何而起,民众自有他们独到的解释方式——民间和史诗传说。笔者在田野调查中,获取了两则颇具代表性的民间传说。其中一则由一位年逾花甲的老者讲述:
很久很久以前,老爷山上只有朝山会,到了清朝末年,山下有个名叫才让措的藏族妇女,她在“六月六”这天的朝山会上唱了一首花儿,用的是谁也没有听说过的新令儿。她那优美的声音赛过了青铜的唢呐,那悠扬的调儿飘到山间,满山的鸟儿都停止了鸣叫。人们问她是什么令儿,她说那是“长寿令儿”,因为“才让”就是长寿的意思。这样一来,每年六月初六那天,人们都会听到才让措在老爷山上唱花儿,于是,满山的人就把她围起来,跟她学长寿令儿。后来,学的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慢慢就有了老爷山花儿会。
上述传说至少包含了如下四个方面的信息,即:花儿会与朝山会有着一定的关联;会期是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会址始终以老爷山为核心;花儿会规模不断变大,参与民众逐年增多。另一则传说与玉皇大帝和西王母有关,在大通民间妇孺皆知:
有一天,西王母与众仙聚会,玉皇大帝高坐宝殿,见众仙毕集并朝拜自己,便乐得合不上嘴,深为自己是三界至高无上的天神而自豪。这时,西王母看透了玉皇大帝的心思,便对玉皇大帝说:“你坐这个宝殿的年代太久了,人间的帝王换了一茬又一茬,你就不应该让位吗?”众仙听了都暗暗点头。西王母又说:“现在该轮到我坐了,你以为如何?”玉皇大帝被突如其来的提问弄得不知所措,想了一想,便计上心头,说道:“也罢,我给你一件宝物,你到西方须弥山界去,那里有两座大山,你能挑到这里来我就给你让位”。西王母接过针一般细长的宝物,化作一个大姑娘去西方挑山。回来时昼夜兼程,走到大通县境时,碰上了一位老汉。老汉见她用很细的铁丝挑着两座大山感到很惊讶,便问到:“姑娘,你用那么细的铁丝挑山,不怕它折了吗?”谁知道刚一说“折”,宝物就折断了,两座山落在地上:一座成为老爷山,另一座成为牦牛山。西王母驾云站在老爷山山头上,不禁流下泪来。这一天正好是人间的“六月六”,西王母的眼泪便成了“六月六”的“洗山雨”。而六月正是苍松挺拔、绿柳垂枝、野草丰茂的季节,游山的人们每当走到林荫深处或坐在火烧台上时,就会围成个大圈,献歌比赛,各显其能。有人善于编唱,就有人随声附和。随着唱点的不断扩大,从山下到山顶,人们簇拥在几十个唱点周围,编的编,唱的唱,和的和,吸引了无数花儿爱好者,发展成了现在大规模的花儿会。
这则传说首先点明了老爷山和牦牛山的来历,以及老爷山与道教神仙的关系,今日老爷山顶星罗棋布的道教建筑足以印证此种说法;然后讲述了六月六“洗山雨”的来历;最后,由“洗山雨”再次强化了花儿会的时间(农历六月初六)、地点(从老爷山上到山下)和规模(从初具规模到逐年增大)。
比较上述两则传说,不难发现,无论是道教圣母西王母,还是现实中的普通妇女才让措,民众在讲述的过程中总希望自己的习俗文化与这些具体的人物产生关联,并从神圣化和生活化的两个层面去强调这种习俗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传说的强大功能,也是老百姓传承民俗和生活文化的重要方式。
2. 朝山会与“花儿”会
根据民间惯制,每逢农历六月初五至初六,来自大通县城关、西关、衙门庄、代同庄、煤窑、庙沟、新城、上下柴家堡等村落的民众自发组织队伍,汇聚至老爷山隆重举行进香、还愿和祈福仪式,谓之“朝山会”。老爷山花儿会的起源显然与朝山会的举行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趋吉求福是节日习俗产生的原发性动因的话,那么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原始信仰则是其产生的土壤和温床。显然,在经过了“升幡”“降幡”“行香”和“朝山”四项重要仪式活动后,严肃庄重的朝山会活动便告一段落,参与其中的民众很快融入到花儿会的情境之中,完成了从神圣活动到世俗生活的身份转化,纷纷加入各自熟悉的花儿民间组织,做了忠实倾听的观众,或者是纵情而歌的歌手。
学者赵宗福在其专著《花儿通论》中提出:“参加庙会的年轻人在唱神颂佛之余,更有一番对爱情婚姻的乞求,而这种乞求一是对神佛的默祷,二是用歌声向异性含蓄或直接地表露情感。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男女唱花儿谈情说爱就成了庙会的重要内容。到了解放前若干年,因为新思想的广泛传播,庙会的宗教迷信色彩大大削弱,而唱花儿的成分大大增加,再后来庙会就纯粹变成花儿会了”。书中还引用了具体花儿作为例证:
红白的巾幡鄂博上插,手拉手佛跟前跪下;
三世的夫妻把誓发,四世里还不能罢下。
你背上罗锅我背上枪,上山走,要吃个黄羊的肉哩;
你拿上黄表我拿上香,进庙走,要吃个不罢的咒哩。
考察老爷山花儿会与朝山会的关联,不难发现,朝山会的如期举行为民众的精神寄托提供了必要的信仰语境,每逢六月初六,老百姓将一年来的祈愿默默诉诸于各自的村庙和老爷山上的三官庙,以庄重的仪式获取心灵的安慰。而花儿会的同时举办,又为他们提供了世俗意义上的狂欢语境,尤其为那些情投意合的青年男女带来了对歌和幽会的绝佳时空。
(二)“花儿”会的发展
老爷山花儿会从祭神为主的朝山活动演化为娱乐主题的民间集会,期间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沉淀过程。如果我们从永乐太子与朝山会的起源这一传说中读释出有效信息的话,那么可以推测这则传说产生的时间至少是明朝永乐年间。据相关文献记载,可以粗略获悉,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元朔山天贶节实质上就是老爷山朝山会的前身,1919年(民国八年)编纂的《大通县志》中有“每逢天贶,士民游集,称大会焉”的提法,我们从“游集”二字可以解读出,在具有朝拜意味的“集”的同时,“游”字已体现了一定的娱乐含义,“大会”的提法更为我们廓清了这一概念,即游艺的大会,自然指花儿会了。由此可以推断,老爷山花儿会滥觞于明代,形成于清朝,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前为成长期,新中国成立以后趋于成熟。“文革”时期急速凋零,改革开放后得以恢复发展,直至今天发展壮大。
自1984年始,大通县成立了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领导小组,对全县“花儿”进行全面普查,搜集整理并出版了《大通县花儿集》;2000年,大通县将传统的“六月六物资交流大会”更名为“六月六花儿会暨物资交流大会”;2005年,花儿会规模进一步扩大,被政府定义为“青海·大通六月六花儿文化旅游节”;2010年再次提高节会规格和水平,被定名为“中国·青海老爷山花儿会”,至今已连续举办十二届。
从近年来田野作业所获资料来看,大通县政府对老爷山花儿会进行了全方位策划和升级,制定了“高标准、高水平、高规模”的标准和要求,主要通过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广大民众共同参与的方式来继承、发扬民间文化艺术,全力打造“中国·大通老爷山花儿会”这一民间盛会。在此过程中,“国家在场”与民间协调达到了有效的统一。在政府与民间的合力作用下,老爷山花儿会的内容显得极为丰富和庞杂,主要包括老爷山朝山会、原生态花儿会演唱、皮影展演、民间文艺调演、民众自发组织的小型歌会等。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在“国家在场”的大文化氛围中,民众自发组织的花儿会日趋式微,老爷山花儿会的“民间性”呈现淡化态势。
二、老爷山“花儿”会的当下境况
(一)“花儿”会时间
根据民间传统,老爷山花儿会从农历六月初三开始,至初七结束,会期共五天,其中,六月初六是当地群众所称的“正日子”,也是整个花儿会的高峰期。这个时段正处于夏耘过后、秋收之前的农闲季节。麦田里的燕麦草早已锄尽,庄稼在阳光和雨露中抽穗,田野里一派生机,天气也处于青藏高原舒适宜人的绝佳时段,庄稼长势喜人,风景如诗如画。劳苦了大半年的老百姓开始进入一贯的生活调节方式——“浪”会场,唱花儿。
他们要寻找一个山清水秀、树木茂盛的地方唱花儿,老爷山自然是民众首选之地。原因除了朝山会的“神圣召唤”之外,主要是其山顶有高大的苍松,山腰有蜿蜒的石阶小路,山下更是溪水潺潺、草坪如茵。穿行在这样的风景之中,与心仪之人互诉衷肠,对于平日拘谨内敛的老百姓来说,六月六的老爷山是一个绝佳的时空所在。
在他们纵情高歌,忘乎所以的情绪里,一种源自生命的原始力量涌动而出,不由引发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赞。颇有意思的是,在六月初六的午后,老爷山几乎每年都要下一场小雨,民众称之为“洗山雨”(笔者在参加2013年、2014年和2017年的老爷山花儿会调研活动中,确实遇到了六月六“洗山雨”),老天爷为何要“洗山”呢?除了众人熟知的有关西王母的那则传说外,民间还有一种颇为秘密的解释——据说六月六这天,老爷山上汇聚了大量相知相爱的青年男女,他们欢歌于丛林深处或庙宇之侧,难免做出野合之事,留下污秽东西,老天爷看到这些,便泼洒雨露,将老爷山冲洗干净。野合所生子女,也往往被认为是神庙所赐——老爷山的老虎洞内供奉有送子娘娘,未孕女子常来这里摸鞋,以求取子嗣。
(二)“花儿”会参与人
随着老爷山花儿会知名度的不断提高,近年来的花儿会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参与的人数在逐年上升。除了大通本县民众的积极参与,还有来自湟中区、湟源县等西宁地区的近邻和来自互助县、平安区、乐都区、民和县等海东地区的民众。六月初六的大通老爷山花儿会,由原来周边地区的几万人参与猛增到十几万人,可谓歌声悠扬,人山人海。
就身份而言,老爷山花儿会的参与者主要有歌手、农民、商人、学者、媒体工作者、民间艺人和外地游客等诸多群体。笔者在老爷山顶的花儿会场中,遇到了来自湟中县甘河滩的何女士和她的亲朋好友们。在简陋的茶桌旁,她们围圈而坐,手捧一杯冰糖茶,饶有兴致地观看着台上花儿歌手的表演。据何女士讲述——每年六月六,只要有时间都会来浪老爷山花儿会,她们从内心深处喜欢花儿,平日出门踏青和友人聚会时,愿意喝点酒唱唱花儿,以舒心怀。可惜现在年轻人听流行歌曲的多,唱花儿的越来越少了。老百姓想从电视上收看花儿大赛的实况,无奈山高沟深,信号接收不到,所以一有空闲,便会结伴来参加花儿会。尽管何女士不能从理论高度评述她所看到的花儿会,但颇能代表普通百姓的心声——相对于政府组织的大型花儿歌舞表演,他们更喜欢老百姓自发组织的花儿对唱和混唱形式。舞台表演约束较多,民间花儿会比较活泛,歌者可以即兴创作,加上与观众的互动,能发挥出较高的水平,也更受民众的亲睐。
在农民群体中,更有来自不同地域的汉族、回族、土族、藏族、撒拉族等多民族群众。他们二三十人一圈,或围坐树下,或临水而歌,气氛热烈而融洽。用汉语方言表达的爱情观念和生活理想充满着泥土的气息和“草根”的智慧。这样的民间盛会自然吸引了不少小商小贩,他们在道路两旁搭起简易帐篷,卖起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吃食——面皮、拉面、酿皮、粉汤之类。一场花儿会下来,少说也得两三个小时,伴随着微微扬起的会场,憨厚的庄稼汉们呼朋引伴,随机而坐,一大碗面片足以弥补他们在享受了精神大餐之后预留的那点小小的物质需求。妇女们要辣辣地吃一碗酿皮,孩童们一边舔着糖球,一边摆弄着新买的玩具。
当然,在众多“草帽”和“凉帽”中间,还穿梭着一些衣着讲究、斜挎背包的群体,他们用各种姿势调整着手中的照相机或摄像机,一看就是媒体记者或民俗研究者。一年一度的老爷山花儿会,因他们的参与和宣传,提升了影响力,也颇受学者的关注。
(三)组织形式
毋庸置疑,花儿会的原初形态由民间自发组织形成,随着各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战略的推行,老爷山花儿会的“民间性”逐年呈淡化态势。相对而言,在以县政府为主导的现实语境中,老爷山花儿会的组织形式显现了更多“官方行为”。
以“2014中国·青海第五届老爷山花儿会”活动方案为例,不难发现这届花儿会旨在加强民族文化的传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坚持“政府主导、节俭办会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原则,以花为媒,全力打造“大通世界,花儿之乡”文化品牌,以歌会友,推动文化旅游融合,着重突出欢乐、喜悦、祥和的乡土气息,充分展示以老爷山“花儿会”为代表的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让观众充分感受“山水大通,美丽无限”的田园文化氛围,展示“青藏高原生态休闲旅游名县”的旅游形象,推动“美丽大通”建设及乡村旅游大发展、大繁荣,把大通打造成生态休闲胜地、民族风情走廊、西北花儿之乡。显然,政府行为具有了多种意义的指向,而老爷山花儿会为多种目标的达成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语境。
当然,除了官方组织的花儿大赛及其他文化活动,老爷山花儿会的民间组织以灵活而微弱的方式存在着。这些组织虽然不是标准化的“社会组织”,但是,“它们都具备一定的组织化水平,开展着自己特有的活动。组织活动表现为事件,是通过若干个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结果,那么,个体行为必须遵循组织的整合才能构成统一的群体事件”。显然,老爷山花儿会的各个民间组织是在朝山会的神圣语境中,经由民众自我选择与调适,最后以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形式存在着。
以老爷山脚下的某一花儿会民间组织为例,我们可以真实地走进老百姓自发组织的花儿活动现场。在山下草木密集的树林里,老百姓或蹲坐在草坪上,或背依大树,这儿一堆,那儿一伙,较为随意地形成了花儿表演的小小场域。起初演唱形式为两人之间的对唱互动,随着参与者的不断增多,有第三人甚至多人开始介入其中。这样一来,就容易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局面。越来越多的听众将歌者围在中间,无形当中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演出舞台,演唱活动也就成了表演性比较强的对歌活动。每每唱到精彩之处,歌者或诙谐俏皮,或声泪俱下;听众则鼓掌欢呼,或默默无语。会场气氛时而热烈,时而平静。这些小小的花儿歌坛,依据天然场景各居一处,踮脚便可看到另外一处。置身其中,每个人都被此起彼伏的歌声浸染着,歌者和听众都在借助这一难得的语境,寻找着自己中意的歌手和连手(男女朋友),在各个歌坛之间穿梭。笔者在2013年老爷山花儿会的田野作业中,听到一位回族中年男子在人群中唱出了这样一首花儿:
白牡丹白着耀人哩,
红牡丹红着就破哩;
尕妹的跟前有人哩,
没人哈一搭儿坐哩。
显然,这位男子看到了刚刚走进人群模样俊俏、身着民族服装的土族女子,开始对着她做出打招呼的手势,并且歌唱。他的花儿自然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看那女子作何回应。土族女子显然非常吃惊,继而呈害羞之态。她在同伴的鼓励和观众的期待中稍作思索,张口做出回应:
石崖上长的墩墩草,
石崖下长的是花椒;
阿哥戴着的白顶帽,
坐下是好,就怕是阿娘来喊叫。
土族女子的精彩回应得到了观众的热烈喝彩。回族中年男子一听便知这次遇到了个厉害角色,不由清嗓捋袖,做出迎接锋芒的架势,那土族女子则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自信的眉宇间透着朴实的英气。
不难发现,这样的民间组织形式极具生活化和真实感,花儿艺术最大的生命力——面对此情此景,可以即兴创作,可以超越时空,可以跨越民族和地域界限,以普通百姓共有的民间情怀去歌唱生活,表达情感,感叹生命。这种极具创造性和草根性的内在气质是官方组织的花儿会所不具备的,正因如此,老百姓才钟爱它,守护它,视它为精神家园,一辈子不离不弃。然而颇为遗憾的是,随着官方组织的影响增大,一些人歌唱花儿的初衷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们往往更在意的是能否获奖,因为一旦获奖便可借机“抬高身价”,在较高层次的花儿演出中获取高额报酬。民间歌手用花儿养活自己本身无可厚非,但在这样的目标驱使下,要想真正传承花儿艺术的精髓,着实令人担忧。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民间自发组织的花儿活动,从真正意义上传承了花儿的艺术内涵,并在老爷山这一相对有限的“文化圈”内,起到了各民族可以相互交流、打破禁忌、增进友谊等积极作用,也为他们和谐共处、共同促进区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美好愿望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语境。
三、演唱内容及曲令特点
“花儿”是老百姓的诗歌,是他们表情达意最为直接的方式。生活的点点滴滴,生命的绵延不息和命运的风风雨雨,都被老百姓总结成一曲曲心韵,再借助不同的花儿曲令表达出来。可以说,是生活赋予了他们这样的诗情,也是生活给了他们无比深刻的生存体验。唱一曲花儿,心就宽了,唱一首“少年”,世界就充满了阳光。在老爷山花儿会上,我们总能领略到生活在西宁四区三县及互助县、平安区等附近地区民众的精神风采,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悲欢离合都与一枝花儿的绽放有关,当然,也一定与这枝花儿的凋零有关。
(一)演唱内容
1.歌唱爱情
在各类民间歌谣中,以爱情为主题的歌唱类型占较大多数,花儿也不例外。因此,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花儿也是情歌的一种了。这种歌谣之所以为老百姓所钟情,主要因为它是老百姓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艺术性比较高,数量也很多。“这不但同它的部分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受时代、地区、民族的局限有关,也同它在民间的长期流传和由于人民的喜爱而对它进行反复加工有关。”笔者在2017年老爷山花儿会调研中记录了一对民间歌手的花儿对唱实录,并深深为他们的率真、幽默和真诚所打动,现择其要者,略述乡间的爱情是如何用花儿表达出来的:
男:院坑里栓着的大黄狗,
硬奔着咬月亮哩;
撇下个尕妹了转身走,
从今后见孽障哩。
女:油菜花开给着路边上,
石榴花开给着岭上;
有人了我俩儿单走上,
没人了你把我领上。
在老爷山花儿会上,这样的对唱颇具典型性。歌者大胆率真,热情任性,将一种原汁原味的民间爱情盛宴摆在了观众面前,其中不乏诙谐幽默,充满了民间温情与智慧。如果不亲临现场,我们很难揣测男女歌者的演唱风采和观众的情绪反应。分析歌词,不难发现——活态的花儿演唱不像花儿文本里记录的那样合乎规矩,上述唱词中,歌者总是根据对方和观众的反应临时调整着情绪和歌唱内容,因而在形式上显示出较大的随意性与灵活性。
不难想象,经由美艳的花儿碰撞后的青年男女,最终牵手走向密林深处,老爷山也就成了他们爱情开始的地方。绕过丛林,我们又听到更多年轻女子情窦初开、大胆追求朦胧爱情的花儿:“二系子草帽往前戴,恐怕是南山的雨来;十七十八的人人爱,恐怕是婆家里娶来。”还有不畏外界压力,坚决捍卫美好爱情的宣言:“清水们打得磨轮子转,磨口里淌的是细面;宁叫皇上的江山们乱,决不叫我俩的路断。”以及对爱情的真诚、专一的誓言:“山里的松柏树冬夏里青,铁桦树它是个实心;维你者半路里起二心,太子山倒插在海中。”这样的忠贞不渝之情,着实让人感动。当然,在花儿会场上,还有许多表现恋爱双方天各一方,诉说相思之苦的花儿:“兰州的木塔藏里的经,拉卜楞寺院的宝瓶;疼烂了肝花想烂了心,望麻(瞎)了一对儿眼睛……”歌声凄婉幽怨,闻之潸然泪下。在花儿会即将划上尾声的时候,我们又听到这样的难分难舍:“青石头栏杆玉石头桥,桥倒时栏杆儿倒哩;今儿的日子里遇一遭,再遇时迟哩吗早哩?”这样的花儿充满了生活意蕴和健旺的生命力,这样的世界就是老百姓最为真实的情感世界。
2.歌唱青春
在民间,“花儿”与“少年”是两个充满着朝气和阳光的词语,许多花儿都表达着对生命的礼赞与思索,许多少年都憧憬着生活的美好未来和希望。正如这首花儿所唱的:
石头塌了路开了,
一对儿麝香过了;
尕妹是牡丹才开了,
阿哥是绿叶儿配了。
唱词用比兴的手法描绘出少女初绽的青春美丽,美艳的花儿自然有绿叶的陪衬。又如:“尕妹的身材一根葱,模样儿活像个鲜桃”,这样的歌唱,似乎能将听众带入古诗“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情境之中,从而产生典雅与朴野相互交织的生命感悟。“花儿里赛不过藏金莲,人里头好不过少年”,意在昭示人们:青春易逝,要珍惜韶华,有所作为,这样才不虚此生,作为有梦想的普通民众,大家都懂得“年轻的时候草尖上飞,老了时再不会后悔。”
3.歌唱故乡
故乡是一个人的出生地,也是其精神回归之地,无论身在何处,故乡一直是作家诗人书写的核心意象,也是花儿倾力赞颂的对象。在老爷山花儿会上,我们总能听到许多介绍故乡,并为之自豪的花儿。老百姓在描述美景的同时,总能将不同的情愫融入其中,表达出丰富的意蕴。如:
晴天里飘一朵白云彩,
雨天里打一把伞来;
青海大通是花儿的海,
好花儿到这里摘来。
这首花儿不仅勾勒出蓝图白云、微雨纸伞的诗意图画,更重要的是点明了青海是“花儿的海洋”,大通更是“海洋中的海洋”这一颇具宣传效应的意义指涉,尾句隐约透露出这样的意蕴,要想结识这些美丽的花儿,那就请到大通来吧。又如:
老爷山上的老虎洞,
神秘得很,
迷住了万人的眼睛;
人伙里我唱的少年俊,
赛百灵,
阿一个唱家来竞争。
老爷山顶有诸多庙宇仙洞,群众在朝山祭神的仪式之后,自然要融入到花儿会的热闹氛围中去。在花儿会的现场,定然有一些民间艺人和歌手。颇具自信的地方歌手喜欢以东道主的身份向围观的群众发出挑战或邀请,来自异乡的歌者自然不会轻易错过一展歌喉的绝佳机会,他们用欣赏的语气赞美老爷山的美丽,当然也会用自信的花儿迎接东道主的挑战,如此,热闹的花儿会又将掀起一阵新的高潮。
4.思乡念亲
众所周知,大多庄稼人春耕过后便踏上了远赴他乡打工的征程。越是农闲季节,他们越难以回到故乡——趁着天气好,多出活儿,多挣点钱。如此一来,花儿会上就多了些悲怆的音调,那些都是思乡念亲的花儿:
左手里抓了方向盘,
右手里抓了个档杆;
七月八月的你别盼,
回来哈十月的半间。
从歌者计划的回家时间来看,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外度过的,若不是生活所迫,庄稼人是不愿意离开故土外出打工的。家里的掌柜的出门了,留下孩子和老人,留下独守空房的女子在寂静的乡间,那是怎样的一种孤独与愁苦!我们在老爷山花儿会上,经常听到这样的幽怨之音:
大河的沿上牛吃水,
鼻圈儿落到个水里;
端起饭碗想起个你,
面叶儿捞不到嘴里。
这样的思念,清晰而具体。仿佛那个外出打工的人只是牵牛饮水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然而终究没有回来。面条都快凉了,吃了那么久也吃不完一碗——出门在外的人吃饭了没有?
高山上落了鸡爪雪,
平川里落了个雨了;
手里端的是红泥水,
心儿里牵扯掉你了。
出门在外的人当然听不到来自花儿会场的真情诉说,置身工地的,这些血性的汉子们天不怕地不怕,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家,家里的娃娃和那个她。可以说,正是花儿,用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传递着他们的思念,一年又一年。
(二)曲令特点
花儿的曲调在民间俗称“令”,不同的“令”包含不同的文学内容和音乐形象。因此,在花儿中,“令”及其衬词的运用决定了花儿的音乐风格。地域不同、民族各异,花儿的音乐风格也各具特色。就老爷山花儿会的演唱情况来看,其曲令特点主要表现为鲜明的地域性、多元的民族性和浓郁的生活化气息。
1.地域性
老爷山花儿会上,以地域命名的花儿比较多见。如“河州令”“马营令”“川口令”“互助令”“孟达令”“吾屯令”“老爷山令”“梁梁上浪来令”等。其中,尤以《老爷山上的刺梅花》最具代表性。
老爷(么)山上的刺(呀)梅花,扎是着扎来着折(啊)两把;只要你尕妹妹说(啊)句话,死哩么活哩是我(呀)不怕。(尕罐罐儿煤疙瘩儿实话拉加一挂捡着来啊,我的红花姐呀,阿哥把你想着,实话拉加想着……)
这是一首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花儿,老爷山不仅山高路陡,而且植物繁茂,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刺梅花美艳好看,但若要得到它,需付出一定的代价。尽管这首花儿的唱词较为简洁,但歌唱时其中的衬词多而复杂——尕罐罐儿煤疙瘩儿实话拉加一挂捡着来啊,我的红花姐啊,阿哥把你想着,实话拉加想着!一般花儿的衬词较为清晰明了,这首花儿的衬词将“尕罐罐儿”“煤疙瘩儿”和“红花姐”连缀到一起,造成了意义繁复和情感叠加的抒情效果,民众一听便知其中意蕴——在青海东部地区,唯有大通县盛产煤炭。因此,衬词中出现“煤疙瘩儿”也就不足为怪了。
一般而言,普通歌者喜欢这些随性而颇具生活气息的花儿,花儿传承人则会选择较为经典的曲令进行演唱。在老爷山花儿会上,我们常常听到歌手表演极具河州风味的《河州大令》:
(哎)上去个高山(者哎哟)望(呀)望平(了)川,
(哎哟)平川里有(啊)一朵(儿)牡丹;
(哎)看去是容(啊)易(者)折去是难(吔),
(哎哟)折不到(我的)手(儿)里枉然。
歌声嘹亮而悠远,将一个男人“求之不得”的怅惘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听到这首花儿,令人不禁想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诗意与落寞。
2.民族性
有学者指出,“花儿流行于中国西部6个省区和9个民族中间,地域之广,民族之多,在中外民歌中是极为罕见的”。这9个民族具体包括汉族、藏族、土族、蒙古族、裕固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据调查,除了离青海比较远的裕固族,汉族、藏族、土族、回族、撒拉族的民众常常活跃于老爷山花儿会现场,东乡族和保安族次之。
在这个多民族聚集的民间狂欢节上,具有民族特点的花儿曲令可谓风格独具、多姿多彩。各民族群众“你方唱罢我登台”,尽情表达着他们的生活认知和精神诉求。我们在调研中有幸聆听了来自大通本土的花儿歌手童守荣所唱的《撒拉令》:
(哎哟——噢)两朵儿莲花(者)一条(了)根(哟),
(哎兮)好莲(了)花(呀)才打了(呀)骨朵(呀)儿了;
(哎哟——噢)我俩的身子(哎)一个(了)心(哟),
(哎兮)好缘(了)法(呀),才想在(呀)一处(呀)儿了。
(哎哟——噢)唐僧(么)取经(者)回长(了)安(哟),
(哎兮)十四(了)年(呀),受给了(呀)八十(么)一难;
(哎哟——噢)能叫(个)海枯(者)黄河(儿)干,
(哎兮)石头(了)烂(呀),嫑叫(个呀)我俩的路断。
撒拉族是繁衍生息于青海黄河岸边的一个民族,他们从遥远的撒马尔罕地区迁徙至青海东部,靠的是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至真至善的信仰。在爱情的表达方式上,他们表现出了同样的执着与真诚——宁愿海枯石烂黄河干,也不能让爱情之路中断!蕴含其中的坚贞不渝之情直追汉乐府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在2016年的老爷山花儿会上,有藏族群众演唱的《尕阿姐令》深情、逼真、生动。歌声所到之处,恍若仓央嘉措情歌款款而来,又似山顶庙宇的桑烟袅袅而去。
摞摞(么)层层的一卷(儿)经(啊),经一(了)卷(呐),尕喇嘛睡着(么)者(噢)哩(呀啊);(尕阿哥你看我来哩说者,哎哟哦花儿那你来哩吗不哈)偷偷(么)摸摸的一片(儿)心(啊),心一(了)片(呐),想死哈谁知(啊)道(噢)哩(呀啊)?(尕阿哥你看我来哩说者,哎哟噢阿哥那你来哩吗不来)
花儿曲令繁多,且各不相同,大多表现为衬词的使用不同。《尕阿姐令》的衬词为——尕阿哥你看我来哩说着,阿哥那你来哩吗不来……歌者内心焦灼而热切的期盼之情溢于言表,听者无不感动凄然。
作为回族和土族聚居的县城,近年来大通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土族花儿歌手。他们所钟情的《三闪令》也是老爷山花儿会上最具民族特色的花儿曲种。
(哎——哎哟噢……)大河沿上的(吔吔吔吔)麻石(了)头(呀吔),(哎哟)一面儿尖尖,一面儿弯弯,一面儿扁扁,尕磨上能当个底扇(呀);我就背上了走,手拿的(吔吔吔吔)皮绳(嘛哎哟哎哟哎哟哟嗬哟嗬哟嗬)太(呀)短。(哎——哎哟噢……)给阿哥绣给的(吔吔吔吔)满腰(了)转(呀吔),(哎哟)面子是单单,里子是毡毡,牛毛的边边,羊毛俩扎给个牡丹(呀);你就勒上了去,人前头(吔吔吔吔)夸我的(哎哟哎哟哎哟哟嗬哟嗬哟嗬)手(呀)段。
虽为民间歌谣,但唱词对仗而不失工整,押韵而不重复。比兴手法的应用更显水乳交融,情景互渗。其中的“满腰转”“毡毡”“牛毛的边边”“羊毛的牡丹”等意象清晰而具体地勾勒了土族群众生活的基本场景,听谓之亲切,唱谓之惬意。
除了典型的《三闪令》,土族群众还喜欢唱《溜溜儿山》《梁梁上浪来》等曲令。回族民众则擅长《尕马令》《白牡丹令》和《晶晶花令》。“这些民族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也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共同用汉语演唱花儿,体现出了一种民族亲和、兼容共存的内在精神。”因此,关注花儿曲令的民族性特征,也是保护和传承花儿的重要内容之一。
3.生活化
在青海,花儿可谓老百姓生活的百科全书。花儿涉及内容上至神话传说历史,下至油盐酱醋“草根”,无所不包,无所不容。这也决定了花儿曲令大多具有清晰可感的生活对象指涉。频频传唱于老爷山花儿会的诸多曲令,如《拔草令》《尕马令》《白牡丹令》《憨敦敦令》等直接源于生活,透过生活繁复的肌理,表达着民众朴素的生活观念和审美理想。此处引述民间歌手严美颖所唱的《拔草令》,我们可窥见流露其间的生活矛盾与深深思念交织着的情感褶皱。
(哎)川里(呀)的麦子(哈)浇三(哎)水(啊好),渴死(哎)了山上的(那个)豆(啊)儿(呗);(尕阿哥你听见了没哈……)(哎)跟前(呀)的花儿(哈)看三(哎)回(啊好),亏死(哎)了路上的(那个)肉(啊)儿(呗)。(早啊门俩尕肉儿呀……)
每年农历四五月份,给麦苗拔草、为洋芋松土是老百姓必不可少的工序。此时的田间地头,布满了花花绿绿的风景——她们是留守麦田的村妇村姑,家里的男丁已外出打工,心上的人儿已远走他乡,身处空阔而寂寥的庄稼地里,一种难言的思绪涌动在心间,不唱就成了心病,倾诉出来,便是优美的花儿。“川里的麦子”,意义指向大山的外面,那是一个无比精彩的世界,麦子可以无数次地获得雨露的滋润,而身处山顶坡地的豌豆却久旱而不得甘霖。“渴死了山上的豆儿”既是农事的直接反映,更是与离别之人焦灼互念的内心实描。“尕阿哥你听见了没哈……”“早啊门俩尕肉儿呀……”,两句衬句,如泣如诉,令人感动不已。
老百姓认为花儿都是心上的话,这样的情感内核也构成了它作为民间诗歌艺术价值和生活本身的恒定因素。歌手马全在老爷山花儿会上所唱的《憨敦敦令》则唱出了生活中的美与诗意:
(啊呀啊——啊哟噢,花呀啊——花儿哟—)天宫里借(呀)一把(哟噢)金(呀)梳(了)子,(阿哥的个憨呀敦敦呀)龙(呀)龙宫里要一把银打的篦子;摘下(个)月(呀)亮(着哟)当(呀)镜(了)子,(阿哥的个憨呀敦敦呀)给(呀)给尕妹梳给个辫(呀)子。肝花儿连(呀)给地是心(呀)系(了)子(哎),(阿哥的个憨呀敦敦呀)我(呀)我俩人好上(么)一辈子。(哎哟——好上一辈子——)
天宫里借来个金梳子,龙宫里要来个篦子,摘下月亮当镜子,给尕妹梳给个辫子——不得不叹服,老百姓的智慧是源自生活的;老百姓的诗意,是带着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和执着追寻得以自然流露的。不难想象,在蓝天碧野间,端一盆清水,让心上人坐在身旁,用心为她梳好辫子,看着她青春姣好的面容映在水中,抑或感叹她一头乌发渐渐被岁月的季风吹白,那是一种不离不弃的情怀——无论时光流去多少,无论世事怎么改变,阿哥的憨敦敦,他们肝花连着心,约定彼此要好上一辈子!有了如此动情的花儿,生活自然充满意义。
四、基本功能
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不论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都具有满足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作用,即都有一定的功能。它们中的每一个与其他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都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花儿是西北民间极为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其在民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交流与倾诉功能
在民间,生活与物质层面的交流和艺术与精神层面的交流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面对农事和日常生活,老百姓的交流是显性的,他们往往通过最为直接迅疾的交流方式达到预期目的;而在涉及精神与文化方面的问题时,老百姓自然要选择约定俗成的仪式行为和语言惯制,达成他们的交流愿望。譬如,在神圣空间与神灵对话时,他们往往借助诀术歌诉诸愿望、接受神谕。在世俗时空内,老百姓在表情达意特别是表达爱情理想与观念时,他们自然选择了民歌。对于青海民众而言,花儿是酣畅淋漓地表达爱意的唯一形式,没有花儿,可以说难觅爱情。
穿行在老爷山的林木溪流间,随处可见青年男女在来来往往的陌生人中寻觅着可以对话交流的异性:
汽车的大路宽上的宽,
路边里没栽个电杆;
这一个尕妹欢上的欢,
为啥你没唱个少年?
颇有意味的是,民众在异性间搭讪的方式也是如此诗意和含蓄。眼前走过一位女性,大胆的男子开始了这样的挽留与招呼。如果对方有意,那么一场花儿的对话就此拉开了序幕:
汽车的大路宽上的宽,
路边里栽了个电杆;
尕妹妹浪会着遇许仙,
老爷山要续个前缘
应答的女子显然以“白娘子”自喻,这次来老爷山浪花儿会怀揣了美好的愿望——遇到“许仙”,再续前缘。这样的应答方式既含蓄又充满智慧,再骄傲的男子也不禁会心头一震,刮目相看。显然,这样的交流是有效的。接下来,他们可能会进行更为深入的交流和碰撞。结果或是牵手迈进幸福的门槛,或是好聚好散,去追寻各自心上的花儿。
我们也可以在老爷山花儿会上看到,没有对歌和擂台,老百姓独自吟唱花儿,引来无数观众的场景。这种情形大多处于倾诉的需要。古典诗歌里的“思妇诗”即属此类,而在花儿中,常见出门在外的人,开始了思乡的旅程:
尕马儿拉到树林里,
树林里有什么草哩?
口口儿声声出门哩,
出门者有什么好哩?
一句“出门者有什么好哩”不仅是念乡心切的真情表露,更是对现实无奈的致命倾诉。众所周知,当下的村庄已不再是原来那个炊烟袅袅的村庄了,成年人都外出打工,只留下老人和孩童固守着孤寂的庄廓,于是孩子上学、老人养老、庄稼耕作等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而外出打工的人,不一定能如愿拿到血汗钱……这一切不得不令人喟叹深思——出门者有什么好哩?不出门,又该怎么办?这样的花儿实际上就是生命中不断绽开的伤口,面对高山流云敞开嗓子倾吐一阵,再深的内心苦痛也会因之减缓。
(二)调节与娱乐功能
庄稼人一年四季与农田打交道,所有的农事活动都是围绕着节令和时序展开的,在这中间少有余暇。农历六月初六实属难得的农闲时间,他们不约而同纷纷从各地赶来,在老爷山花儿会上一展歌喉,大半年的辛劳便可得到暂时的延缓。“民间文艺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娱乐性,人们参与这些活动,首先不是为了受教育,而是为了消除疲劳,恢复精神。”如果没有了正月的社火表演和六月的花儿表演,很难想象,民众的精神需求如何得以满足。
在进行完朝山仪式之后,一路走来,老百姓因不同的精神需求会前往参拜药王庙、玉皇宫、百子宫、无量殿、七真祠、太元宫等庙宇,此举无疑是他们精神得以慰藉的重要途径之一。了却的“神圣情感”的愿望,接下来顺理成章地要达成“世俗情怀”的抒发,于是纷纷参与花儿会,开始演唱花儿。
上去个大通老爷山,
松树儿罩严着哩;
尕妹的跟前坐一天,
活像是过年着哩。
由此首花儿可以感知,老百姓此时此刻的心态是放松的,他们完全沉浸在花儿的海洋中,歌唱生活,寄情理想。尽管生活中充满了诸多坎坷与磨难,但在老爷山花儿会现场,他们忘却了一切烦恼,尽情享受着这个难得的狂欢时节。“过年”这一话题意味着可以农闲在家,置办丰富的年货,可以走亲访友——对老百姓来说,幸福的存在感因“过年”而得以空前的强化。而此刻,“尕妹的身边坐一天,活像是过年着哩。”这种心灵的彻底放松与愉悦情境,在日常生活中是极为少见的。因此,他们沉醉在花儿的歌声里,久久不愿醒来。
上去个大通老爷山,
山对山,
无量殿保下的平安。
只要尕妹俩见一面,
心舒坦,
九架山当成了塄坎。
精神和心理得到良好调节的庄稼人,此时面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因为他见到了心上人的面,内心充满了喜悦,这种喜悦很快转换为生活的动力。在离开老爷山的那一刻起,或许他就下定了某种决心,因为他矫健的步伐让身后的尕妹看到了作为一个男人的力量与自信——九架山都可以当成塄坎,今生今世,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三)认知与审美功能
万建中认为:“民间文学出现于无文字的原始社会,而且一直伴随着民众现实生活的发展而演变。这一事实决定了这种以口头语言形式创作和传播的民间文学具有其他文学,尤其是作家文学所不具备的特性功能,那就是将知识传授作为自己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
花儿是生活艺术和知识的总结。我们在花儿会上经常听到刚刚被歌者即兴创作出来的花儿文本,这是由其丰富的生活底蕴和系统的生活知识构成的。因此,在花儿会上,除了表情达意,花儿还肩负着传递一定的文化知识的社会使命。懵懵懂懂的年轻人在聆听与传承花儿的过程中,自然获得了必要的生活知识与文化知识。调研组成员曾在老爷山花儿会上捕捉到如下颇具认知意味的花儿:
老爷山上的老爷庙,
金柱上贴的是纸条;
维人的行规不知道,
全听个尕妹的指教。
“维人的行规”意在指明追寻伴侣也有其礼仪规程,不可贸然行事,否则轻则为人所笑,重则为人所弃。歌者自谦不知道规矩,恳请对方予以指教,这样的谦逊友善的态度比起那些盛气凌人的姿态,自然容易获得对方的好感,进而达成进一步交流对话的可能。
唱一首花儿者宽心哩,
年轻人听了者想哩;
老汉们听了者年轻哩,
娃娃们听了者长哩。
这首颇具铺陈特点的花儿,直接点明了老百姓心目中的花儿功能。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歌唱花儿可谓人人咸宜,各取所需。年轻人听后“想哩”——这里面的“想”字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爱情、友情、亲情、生活、苦难……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唱。老年人听了后“年轻哩”——这是极富浪漫情怀的一种认知与表达,老年人都曾年轻过,现在他们也聆听或歌唱花儿,能够融入这样的语境中,并感受生活的变迁和命运的真相。娃娃们听了“长哩”——孩童的成长总是浸润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之中,可以说他们自小耳濡目染于花儿的绽放,长大了自然能够传承和享用这样的民间文化,并用以指导自己的生活行为。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花儿本身是一种生活知识,演唱花儿也就成了传递民间知识的重要途径。
欣赏花儿表演实际上也是一种审美活动,审美活动的产生由人的审美需求决定,正是审美需求、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构成了审美活动的基础。当下青海诸多村落已经慢慢失去了用讲故事的方式来驱散精神云翳的文化语境,在极为有限的精神活动空间,花儿演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老百姓最钟情的审美理想。因此,“只有审美理想的召唤,才使自然需要变成审美需要,使审美需要不仅仅是一种走入现实并不断进步的欲望,还使人得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面对现实的诸多苦难,老百姓往往很难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花儿表演可以说及时弥补了民众的精神缺憾,并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审美活动。笔者采自2019年老爷山花儿会的一首歌者自编自唱的《三闪令》足以表达民众对爱情的期盼、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寻之情:
大通就是个好地方,老爷山雄壮,娘娘山漂亮,鹞子沟浪上,这是旅游的地方,六月六会上,开心的花儿哈漫上。
心想着阿哥见不上,手机俩打上,信息们发上,口儿里念上,等给着常走的路上,眼泪儿汪上,期盼着人伙里遇上。
这首花儿上阕连用几个排比句式,表达对故乡大通美好风光的赞颂之情,同时也点明了“六月六花儿会”这一文化语境;下阕则用一连串的动作语势强化了“念君心切”的情感思想,深挚而又感人。打手机、发短信、等候在常走的路上——这样的表述既生动具体,又具时代气息,颇具生活的质感和美感。尤其是“眼泪儿汪上,期盼着人伙里遇上”一句在文学审美内涵上,与《九歌·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用花儿认知世界,再用花儿融入这个世界。这是青海民众朴素的生存哲学。
结语
老爷山六月六花儿会跟所有的花儿会一样,是一个集民间信仰、游艺杂耍、民间商贸和民间歌会于一体的文化空间,作为民俗主体的普通民众徜徉其中,他们在获取神圣的精神寄托的同时,也用演唱和观赏花儿的形式得到了世俗生活层面上的精神慰藉。但是,由于时代发展变迁,参与者身份的不断变换和政府行为的过多干预,使得原生态的老爷山花儿会正在慢慢走向衰落,“非遗”视角下的传统花儿会如何得以保护传承,亟需我们做出更为合理和科学的研究,并提出行之有效的保护对策。正如学者所言,“各种文化活动的展开所依赖的环境、场所或某种特定的、定期的文化仪式及其参与的人群的行为和规程,共同构成了花儿庙会的文化生态环境,对花儿存活的这一生态环境的的抢救和保护,是花儿庙会得以顺利开展、延续、传承下去的基本保障,任何对花儿的曲意改造,‘画地为牢’式的做法,都将是对花儿庙会这一民俗文化生活的肢解和破坏。”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对青海各大花儿会的研究与保护是否契合民间立场与民俗情怀,值得本土研究者不断反思与内省。(注释、参考文献从略,请以正式出版刊物为准)
作者简介:刘大伟,男,青海互助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民俗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原刊于《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