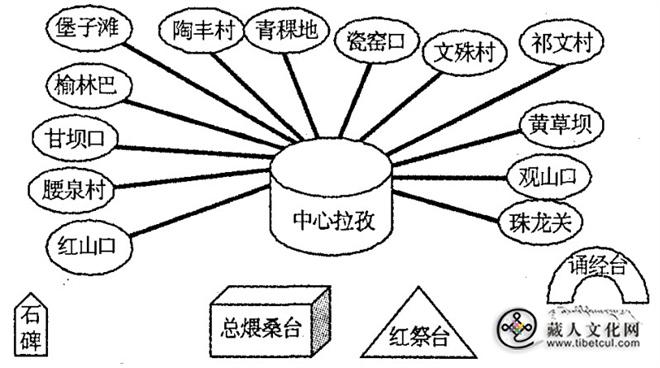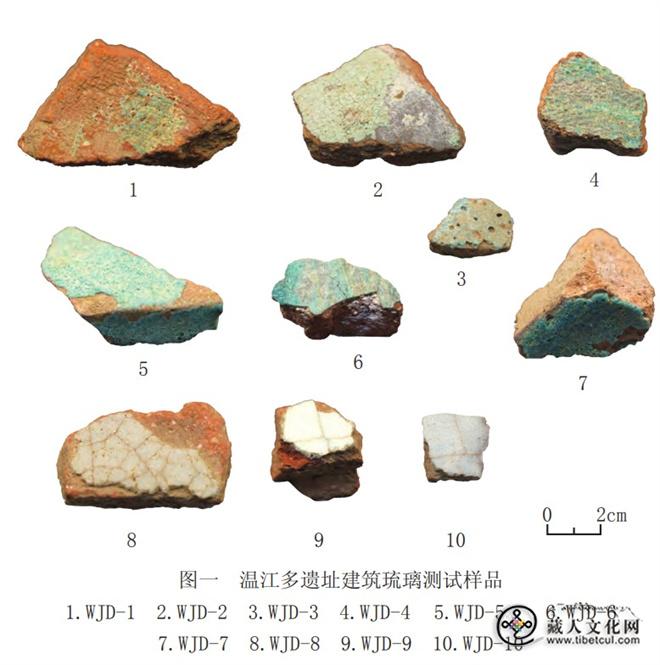摘要:本文以一个与藏传佛教密切相关的传统手工艺画师群体——唐卡画师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唐卡画师置于西藏社会历史变迁和藏传佛教兴衰的角度,分析他们的地域来源、僧俗身份、执业与传承模式等,并结合同时期藏传佛教的施助体制,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从而理清唐卡画师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前后发展脉络。
关键词:西藏唐卡;画师;历史源流
三、从个人到集体——寺庙兴建热潮推动唐卡画师群体发展
从萨迦派政权统治到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正值中原的元明两代。这一时期,西藏经过了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的确立,形成许多僧俗结合的地方势力,在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以萨迦最为强大。此时蒙古王朝的崛起,促使了全国的统一,从此西藏的经济社会逐步走向安定。在中央王朝的高度重视下,藏传佛教艺术迅速发展,佛教绘画活动日趋成熟,并探索出了一条与上一时期非常不同的道路 :高度重视佛教的传播,大力兴建寺院并向蒙古和汉地推进,接纳和引进优秀的外来文化,并将吐蕃传承下来的文化特色与之交融、碰撞、衍变、传播,从而集大成为一体。在这种丰富活跃的文化背景下,出现了兴建佛教寺庙的热潮,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画师在空间地域上的不断流动,促使了地方性画师群体的成熟和早期本土绘画流派的出现。
(一)本土地域性画师群体崛起
1. 元朝宫廷画师
元朝时期,以西藏萨迦寺为中心的后藏地区,曾出现过一个绘制壁画和唐卡的热潮。1260年,元朝皇帝忽必烈在上都称汗,同年将乌斯藏的管理权授予八思巴(图3),封他为“大元帝师”(图4)。八思巴不仅是精通工巧明的大师,还亲自参与唐卡、壁画的绘制。这种由高僧、大德指导,并亲自参与绘画实践且一直延续下来的作风,是藏传佛教艺术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保障。
 图3 八思巴肖像唐卡(局部)
图3 八思巴肖像唐卡(局部)
 图4 《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像》,15世纪晚期—16世纪
图4 《忽必烈册封八思巴为帝师像》,15世纪晚期—16世纪
 图5 阿尼哥塑像(局部)
图5 阿尼哥塑像(局部)
同年,八思巴邀请80位加德满都①河谷艺术家到萨迦寺进行艺术创作活动,这支艺术家队伍由尼泊尔纽瓦尔王朝 17 岁的艺术天才阿尼哥(A niko,1245-1306)(图 5)带领,于 1261 年抵达萨迦,[9] 萨迦寺院大殿内的众多作品皆属于尼瓦尔风格。《元史》和《造像量度经》中对阿尼哥的评价极高,《造像量度经》的前言中赞扬他为“更超群者也”,工艺水平“天下无比与”。②有学者依据《萨迦世系史》中的记载推测,阿尼哥“为此塔建设费时两年”。两年后,阿尼哥完成在萨迦寺的任务,被八思巴举荐到忽必烈的宫廷,一直从事佛教艺术工作达40余年之久。阿尼哥于1273年被任命为“诸色人匠总馆”,他不仅持续创作,还对大量工匠进行培训。可以说,艺人在由外圈移动到核心圈的过程中,将技艺与文明带入,这种以尼瓦尔艺术为基础,融合部分汉地艺术风格的造像图式,逐渐形成汉文文献中所称的“西天梵像”,或通常所说的“元代宫廷藏传佛教艺术”,[9] 对于明、清绘画艺术有着直接的影响。
2. 多民族混合的职业画师群体出现
1306年,阿尼哥在元宫廷去世。同年,夏鲁寺地方的世俗首领的扎巴坚赞前往大都,得到元帝的支持,大规模重修夏鲁寺。扎巴坚赞邀请元朝宫廷画师群体赴夏鲁寺绘制壁画。文献中未对画师个人有详细记载,根据现存壁画风格判断,一般认为画师群体为多民族的混合体,有尼泊尔画师和汉族画师,很可能是阿尼哥在世时在元朝宫廷培养的画师人才 ;夏鲁般若佛母殿题记中发现有钦巴 • 索南邦的名字,“在资料不确凿的情况下,断定题记画师钦巴 • 索南邦为阿尼哥徒弟之一,并将其他般若佛母殿中尚无画师署名的壁画均判定为钦巴 • 索南邦之作”。[10] 夏鲁寺汉藏合璧的建筑样式,以及壁画中体现的具有浓郁汉风的人物样貌及其衣着,也是元代画师多元交融流动的生动体现。
3. 本土地域性职业画师群体成熟
元朝末期,西藏地方政治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元朝扶持的萨迦派政权逐渐走向衰落,新的地方政权——山南的帕竹地方政权崛起,控制了西藏大部分地区。明朝对西藏的管理推行“分封多建”的新政策,江孜地区的统治者江孜法王家族也逐渐兴盛。与此同时,始于元代大规模的宫廷藏传佛教艺术在此时期也走向了鼎盛阶段。
后藏拉堆地区在1330-1456年间相继建起了三座吉祥多门塔式的佛塔建筑,即觉囊大塔、江塔和日吾且塔。经维塔利考证,引《唐东杰布传》的记载,认为拉堆洛领主派遣了大批画师来参加日吾且塔的修建,从而在该地云集了一大批来自洛、绛和阿地区的画师,同时考证发现,这些塔内的壁画继承了夏鲁寺的艺术风格又有了地方化的发展。维塔利将参加上述三塔艺术创作的艺术流派称为拉堆艺术流派(国内学者熊文彬也赞同此一观点,大卫·杰克逊推测此处的拉堆艺术流派与他考证的北方流派(“羌鲁”)可能是同一风格流派,但缺乏文献证据 ,国内学者李健认为,不管风格名称如何,在 14世纪至15世纪上半叶后藏的昂仁,拉孜一代应该确实存在一个民间的工匠群体,从事寺院修建、佛像塑造和佛画绘制。),这一流派的出现,说明了本土地域性画师群体的成熟。
1418-1436年间,白居寺及吉祥多门塔由著名的江孜法王饶丹 • 衮桑帕在一世班禅大师克珠杰 • 格勒贝桑的赞助下创建。其壁画上保留下来的很多题记殊为难得,意大利藏学家图齐和中国学者熊文彬都对其做过专门深入的研究。从图齐《梵天佛地第四卷江孜及其寺院》(第二册题记)中对吉祥多门塔内的壁画题记的研究,可知当时参与修建的地方性画师群体是以拉孜和乃宁画师为主,其中的拉孜即在前述的拉堆地区,可见直到15世纪上半叶,“拉堆艺术流派”的民间画师群体仍在后藏地区占据优势地位。乃宁则是新崛起的另一地区绘画人才中心。题记还反映了当时的赞助人与画师施助模式施主们既是白居寺的施主,又是画师的施主,他们对布施的具体内容都有明确的指涉,就是聘请画师绘制壁画。
从加德满都河谷的阿尼哥进藏到后藏西部拉堆艺术流派的形成以及一部分新的绘画人才中心的崛起,近两个世纪的交流传播反映了元代空前大一统额背景下,西藏本土地域性画师群体逐渐代替域外画师从而占主导位置,画师群体的赞助人也从以往单一的以皇家转变为地方世俗贵族。
(二)由僧入俗的转变
僧俗比例是测度古代画师群体社会特征的重要指标。虽然古今都强调唐卡佛像最好由僧人来画,但从上文中的案例得知,在15世纪上半叶,僧人画师的比例已经大大降低了,画师主要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俗人画师。
俗人画师群体的出现反映了两点原因 :一是在寺庙大规模修建时,画师的需求量巨大,需要画师随工程移动且花费大量时间投入,早期的兼职型高僧画师远远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而元代宫廷画师群体的成熟和佛教的传播和复兴也为图像学知识从宫廷向民间或是从寺庙向民间普及提供了可能,从而使画师身份有了由僧入俗的转变。
(三)西藏本土画派的出现
元明时期,本土各类绘画流派的创立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表明了西藏本土绘画风格的基本成熟,对唐卡艺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汉语“流派”一词在藏语中是“lugs”,本意指“方法,形态,体裁”或“习惯,风俗,规矩,礼仪”。[11] 在绘画中引申为风格、流派。前文有提及到吐蕃王朝前期形成的尼风画派,传说是松赞干布兴建大昭寺时,吐蕃本地的画师普遍学习尼泊尔画风而形成的,而之所以认为元明时期才是西藏本土画派出现的时间节点,是因为吐蕃早期的西藏绘画不仅受尼泊尔单个地域风格的影响,所以尼风画派并没有得到当时和后世的公认。
据文献记载,西藏出现的第一个本土画派是齐乌冈巴画派,创始人是久乌岗巴,产生于13世纪。从某种意义上来,齐乌岗巴画派的出现标志着西藏绘画本土化风格的诞生,表现了藏传佛教艺术从纯粹引进域外艺术形式 ,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磨合 , 把外来艺术特征完全融入当地的文化土壤。有学者猜测当时很可能只是产生了画派的雏形,并早已失传,但从萨迦南寺、夏鲁寺、白居寺吉祥多门塔等壁画,以及珍藏与昌都等地寺院和海外博物馆的少量唐卡作品中,都可以窥探齐乌冈巴画派的风采。
在随后的历史时期中,各类大小画派的依次建立,最主要的是15世纪中后期建立的勉唐派和钦则派、16世纪建立的噶玛噶智派,以及17世纪建立的勉萨派,地域跨度十分广泛,包括西藏、青海、四川等藏区,以及蒙古、中原等地,时间上跨度整整600多年,而延续至今。
综上,元明时期,即萨迦派政权时期到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唐卡画师群体经历了以下转变 :一,西藏本土地域性画师群体崛起,逐渐代替了域外画师占主导位置,高僧、大德指导,并亲自参与绘制工作的传统被延续下来,成为西藏佛教艺术和绘画艺术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僧人画师的比例大大降低,民间俗人画师群体出现,画师身份有了由僧入俗的转变 ;三,画师的传承模式渐渐摸索出几种固定模式,由寺庙和宫廷引入民间 ;四,画师的赞助和供养从以往单一的以皇家赞助转变为私家(地方世俗贵族)赞助赞助,或皇家与地方世俗贵族等共同构成公众赞助;五,地方性画师群体的出现推动了本土绘画流派产生,西藏本土绘画风格的基本成熟。
四、从民间到官办——画师行会的建立
形成于明朝后期的格鲁派通过在新疆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借护教之意,战胜了统治西藏长达两百余年的噶举派势力,在宗教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最终在642年建立了以拉萨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时期对应中原的清朝。政权领袖五世达赖喇嘛 (1617-l682年 ) 受顺治帝正式册封后,清朝中央政权对两藏行使主权管辖,这标志着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整个卫藏地区开始受到比较有效的行政管理。这一时期也是卫藏特别是拉萨诸多寺院宫殿重修扩建的一个高潮期,沿用元代以来在宫廷制作藏传佛教艺术的传统,前后藏优秀画师也开始从各地云集拉萨。
(一)五世达赖与布达拉宫的两次重建
为巩固政教合一的甘丹颇章政权,罗桑嘉措试图重塑一个新的政教中心,由噶厦政府的首席噶伦第司• 索朗绕登主持,重建布达拉“白宫”及宫墙城门角楼等,并扩展到整个拉萨城,他“将吐蕃时期已经消失的寺院重新恢复”,[12] 于1648 年修建完成。此时根据第司 • 桑结嘉措的意见,召集了前后藏、尼泊尔、汉地等共 66 位技艺高明的画家进行布达拉宫白宫壁画的绘制,根据十世班禅画师的噶钦 • 洛桑彭措的著作中得知,其中的画师首领是一位僧人画师——追古• 曲英嘉措(图 6)。
 图6 追古·曲英嘉措
图6 追古·曲英嘉措
追古 • 曲英嘉措起初只是扎什伦布寺的一位普通僧人,后师从勉唐派著名画师勉拉却吉杰洛桑群培,系统地学习了绘画技艺和造像量度知识,成长为一位精通工巧明的大师。后来,在四世班禅大师的近侍画师勉拉却吉杰洛桑群培和贡秋伦珠的大力推荐下,曲英嘉措接任了班禅近侍画师之职。[2] 当时,为五世达赖喇嘛讲授宗教度量体系的高僧画师素尔 • 曲映让追对他的评价说 :“如果曲英嘉措不当喇嘛,而像我们一样只是绘画,而不做任何其他事情,那么在艺术上,他肯定会像伟大的勉唐巴 • 绛央巴一样,无人能与之匹敌。”这里,曲映让追结合自身因其宗教导师的身份使其无法将全部精力花在绘画创作上的经历,指出了僧人画师作为佛教高僧与唐卡画师之间的矛盾 :在西藏,真正的僧人很难成为完全的画师,尽管他们的绘画水平可能远在一般俗人职业画师之上。
1690年,第司 • 桑结嘉措在五世达赖圆寂后为其修建灵塔,开始主持修建布达拉宫的红宫,使之成为布达拉宫今日的大体模样和规模。参与红宫壁画绘制的画师队伍更为庞大,总共召集勉钦两派的画师236 人,其中包括了以洛巴扎 • 丹增诺布为总画师,绒巴 • 索朗结布为副总画师的勉唐画派画师160人,以桑阿卡巴 • 曾培、阿旺等人为代表的钦孜派画师68人。画工的总人数为白宫的3倍之多。洛巴扎 • 丹增诺布是有确切记载的第一位负责西藏最高级别绘画工程的俗人画师。
(二)第一个民间佛教画师群体与官办绘画作坊的出现
1694年,布达拉宫红宫完工以后,第司 • 桑结嘉措挑选出了25位画师,最早以角楼“索京瓦”,也就是以大昭寺的一角殿堂,作为专用画室,后来成立了西藏第一个民间佛教画师行会组织——画社,藏语名为“拉日白吉度” (Lha-zo-ba-skid-sdug),意为“神佛绘制者苦乐与共团体”,其中,“吉度”(skid-sdug)即为“苦乐”,也是“自愿组成的民间社团组织”。[13]“拉日白吉度”成为了西藏最高级别的画师群体,主要由俗人画师组成,专门为达赖喇嘛的宫廷和西藏地方政府绘制壁画和唐卡。这一行会的建立,使一种全新的皇家通过绘画作坊来赞助和供养画师的施助关系开始固定下来。自此,唐卡的艺术创作活动也逐渐进入专业化的时期。
后来,画师行会经过不断发展壮大,又形成了另外两大官方的绘画作坊——“宋穷”和“冲肖”。画师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高,生活水准也有了基本保障。根据学者李健对西藏大学丹巴饶旦教授(祖孙三辈都曾任职于西藏噶厦政府“雪堆白”)的采访得知,政府派一僧一俗两位官员共同管辖。僧官为“列参巴”,俗官为“仲道”。管理机构则由 7 人组成,除了两位派来的官员,还有两位相当于总画师的“乌钦”,即“技艺精湛的大师傅”,以下依序为“乌琼”“居玛”,相当于总画师的执事、助手,当然,他们也是唐卡绘制的优秀人物。从噶厦政府所领得的珠宝、金、银、红铜等贵重颜材料交由总画师“乌钦”保管,他还负责掌管所有工匠的招收、派遣与工作的安排。关于画师的来源及他们在行会组织内的待遇及地位,丹巴饶旦教授说道 :“ 所有画师经过层层考试而进入,选择有天分的画师继续训练 ;画技高的人被喻为大师傅,免除个人赋税、优赏酬资,直到封认官品。 画师还著书立作,传度量经与手抄本。” ,“虽然画师在地位上有级别,最高画师相当于七品官的地位,但都是在工艺技术上获得表现,与实际的政治没有关系。”[14] 最后一任“乌钦”扎西次仁也曾讲述,画师原来是分散在各地的农奴,到拉萨后成了专职画师,由地方政府每年供给每位画师以固定的物质报酬,报
酬多少依行会内部画师的技术等级分配,早期约300斤糌粑、35斤牛羊肉和30斤左右的酥油等,生活安定,绘画时间充足,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当然剥削是有的,画师行会具有垄断性,非画师行会成员不能在拉萨从事商业性绘画。如果行会内画师想外出揽私活,就要上交行会一定的税金。
 图7 《乾隆皇帝僧装像》图8 《宝生如来与菩萨像》
图7 《乾隆皇帝僧装像》图8 《宝生如来与菩萨像》
画师行会的建立和画师队伍的空前壮大进一步提高了画师群体的社会地位,并推动唐卡艺术向更专业的水平发展。大量经典壁画、唐卡被留存和传播在寺庙、宫殿中,如悬挂于布达拉宫萨松朗吉殿的彩绘唐卡《乾隆皇帝僧装像》(图7)、专为乾隆皇帝定制的寿礼《宝生如来与菩萨像》(图8)等。画师行会的建立还使唐卡绘制的功用有了新的扩展,地域流动大大增加。除了传统的宗教上的用途外,唐卡开始成为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沟通关系的“神圣礼物”。这种向中央王朝进贡与赏赐的做法自元明以来一直存在,到了清代则更加盛况空前。“《大清会典》中蒙古,安多和康区很少有进贡佛像,唐卡的记载,而卫藏地区的佛像和唐卡均有频繁进贡……清宫崇奉格鲁派,所以在唐卡的内容上格鲁派占有绝对优势,其他教派的作品绝少见到”。[15] 故宫所藏的若干幅唐卡,除了清宫自己造办的之外,主要就来源于进贡,且以来自西藏的为主,且很可能就是由噶厦政府控制下的拉萨画师行会来完成的。
(三)中央政府的积极参与和供养
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与清王朝的密切来往,使得清廷也积极向西藏进行交换与供养,并以刻板译经与绘画雕塑等活动支持佛教事业,这些举措促使了为寺院、贵族“制作圣物”的官制画坊蓬勃发展。此时,五世达赖喇嘛及其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和清朝政府共同成为清代画坊的支持者与供养人。
清代中央王朝在康熙时期设立了“中正殿画佛处”,负责宫中藏传佛教事务,进行唐卡和佛画像的绘塑活动,雍正时期承袭,于乾隆时期达到鼎盛。罗文华在《龙袍与袈裟》一书,关于清宫藏传佛教绘画的机构与画师的研究中,呈现了北京“中正殿画佛处”的建置经过与内容 :中正殿画佛处原是宫中专供皇帝使用的佛堂,内部供养许多“驻京喇嘛”。这些僧侣分为两种,一类是念经的喇嘛,另一类是参与绘塑活动的画佛喇嘛。画佛喇嘛被指派工作后,白天在宫里参与绘塑活动,晚上才回寺院。画佛喇嘛在起稿后请皇帝提出意见,修饰后再正式绘制,并解决创作过程中关于图像学、教义、神圣仪轨等问题,使完成之作与一般在养心殿所完成的绘画有所不同。如此,中正殿画佛处的制作可以保证宗教艺术品的神圣性,并加强与驻京喇嘛在佛学上的探究与合作。渐渐地,拉萨与北京形成彼此往来的绘画组织,如十三世达赖进京
朝觐时,画师次仁宏也随同,并将大量清末宫廷粉本带回拉萨。此外,中正殿画佛处收有大量蒙汉地区的古今造像,为画佛的工匠喇嘛,或称“中正殿画佛像人”提供最好的范本。画师团体也有领袖的等级之分,称为“佛画副达喇嘛”,他主要的工作是接受皇帝谕旨,负责召集画师喇嘛们,并承办从起稿到御览的绘画过程。但目前对于这些喇嘛的出身、所属寺院以及如何选拔都未有详细记载。[15]
此时还出现朝廷下令西洋画匠郎世宁等人与喇嘛画师一同完成唐卡画作的独特情况,将西洋的技法与西藏唐卡绘画相结合 :雍正时期,出现以西洋立体写实技法绘制面相,并辅以“中正殿画佛处”的喇嘛完成平面的佛身,使宗教内容不偏废。乾隆时期佛殿阁楼的“普陀宗乘寺等图一章八分”也是由宫廷画师与画佛喇嘛合作完成的。画面中,寺院与象征天地的树石由喇嘛设计并具有宗教考虑,再佐以具备阴暗处理的西洋技法。[15] 只有清朝皇帝御制的唐卡,在背面另附一白绢,上书有皇帝旨意、绘画的内容和由谁绘画哪一部分以及于何时完成,或写明是某某进贡等等,突破了西藏本土唐卡画师不留名的传统。
(四)全民唐卡热
随着官办画院朝着专业化、产业化的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一些民间和寺庙的画师群体也被聚集起来,出现了百姓聘请画师绘制唐卡的热潮,形成了民间的绘塑作坊——“拉茹”,此时期的唐卡数量明显增多,有些大型寺庙和布达拉宫等宫殿的唐卡藏量,可达成千上万。与此同时,唐卡的制作工艺、技术与材质也在不断成熟,品类逐渐增多。
此后,官办的手工艺专门组织也在民间团体的基础上抽调形成,如金属铸造组织“雪堆白”、泥木工组织“多吉辛巴”、陶器制作的官办作坊等等。官办组织大规模集中优秀的工匠,使得如巨型唐卡或大体量佛造像这类本就只可依靠团队合作才能完成的大型工程变得不那么艰巨。通过合作交流,工匠们的技术也得到飞速提升,从而诞生了很多伟杰出的佛教艺术作品。同时,民间作坊与官办作坊相互交流、补充,使得不同行业均呈现出了丰富多才的蓬勃势头。
综上,从五世达赖喇嘛统治下的甘丹颇章政权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期间,唐卡画师群体经历了如下转变:一、从布达拉宫的两次重建到民间佛教绘画的行会组织 “拉日白吉度”,和后来“宋穷”和“冲肖”两大官方画院的建立,使得此时期的主导画师群体组织经历了从民办到官方的转变,画师地位大幅提高 ;二、僧人画师作为佛教高僧与唐卡画师的双重身份进一步出现了矛盾点,尽管他们的绘画水平可能远在一般俗人职业画师之上;三,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密切流通、交换与供养,使五世达赖喇嘛和中央王朝共同成为清代画坊的支持者与供养人,并共同完成了图像帝国标准化的时期 ;四,宫廷画坊出现早期的绘画创新苗头和产业化发展趋势 :清代中央王朝的官方画坊有了西洋画匠与喇嘛画师一同完成唐卡画作的情况,且注明了具体分工和进贡人姓名等,突破了西藏本土唐卡画师不留名的传统 ;五,皇家赞助规模的宏大引导了私家赞助热潮,供养物品的种类数量开始有明确规定和记载,画师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五、从传统到革新——画师的对外交流与近代绘画的创新趋势
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 • 土登嘉措是西藏近代政治舞台上一个极为特殊和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出生的年代正值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社会转型期。清政府经过了几代繁华盛世后开始走向衰败,阿旺洛桑 •土登嘉措坎坷多变的一生可以说是那个暗流汹涌、风云变幻时代的真实写照。
即使面临着现实的社会动荡,西藏的唐卡艺人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仍有着不少在以拉萨为中心的西藏各区域聚集。据诺布旺丹、叶星生等学者研究,从五世达赖时期传承下来的拉萨画师行会在当时画匠有54户,从业者71人,而成立时仅有 5人。除了唐卡画师之外,土登嘉措还将从事木器彩绘的画匠并入画师行会;日喀则地区的扎什伦布寺内,有画师 50多人;在勉唐画派创始人勉拉顿珠的出生地,山南地区洛扎县,有著名民间艺人40余人。可见,到民主改革前,整个西藏的绘画艺人至少有数百人之多。近代西藏唐卡出现了绘画革新的潮流。据历史记载,十三世达赖喇嘛因战争逼迫分别于1904和1910年先后两次走上了背井离乡的流亡道路,曾一度来到青海、内蒙古地区、外蒙库伦、中原等地,最后于 1912年返藏。在随行的队伍中有一位专职画师次仁久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宫廷画师,出生于西藏山南地区曲松县,曾获乌钦 (大师父) 职称,是现在西藏著名画师丹巴绕旦教授之祖父。)(1872-1935),他在途中注意搜集绘画资料,学习到了汉族美术,其画风受到了中原内地传统绘画的影响。从现在留存的画作看,次仁久吾描绘了很多传统唐卡中未曾涉及的现代事物,是西藏与内地绘画艺术交流促成创新的典范。学者费新碑甚至将当时这一类风格的绘画归为“汉风”。
 图9 根敦群培 图10 安多强巴
图9 根敦群培 图10 安多强巴
根敦群培(1903-1951)( 图9) 和 安多强巴(1915-2002)(图10)被认为是西藏现代美术的先驱,二人曾是师徒关系。他们都来自安多,都曾入哲蚌寺学经,都曾学习过传统的唐卡绘画,但个人创作的都超出了唐卡绘画的范畴,给西藏美术史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敦群培的艺术创作中凸显了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如藏族史学家恰白 • 次旦平措所说的,根敦群培的一生如同蜜蜂一样,飞遍每个山谷和原野,从各个地方的鲜花里汲取营养酿成蜂蜜,用藏文符号记录和储存下来,成为无法估计价值的珍贵著作和资料 ;[16] 安多强巴的绘画艺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学习和继承了根敦群培的绘画理念,另一方面对传统唐卡的绘制风格进行了大胆创新,他受到现代摄影技术的启发,注重写实风格的运用 ;他试图将西方绘画的技法与传统的佛教绘画结合起来,打破了传统绘画单一的宗教束缚感,为之后许多处于观望状态的唐卡画师指明了从传统中走出去的方向。尽管当时的传统画师不一定支持他的创新,但他实际上开创了“安多强巴画派”,这是今天西藏画师们普遍认可的事实。
结语
总的来说,唐卡画师几乎与藏传佛教的兴起同步出现,在历史上的兴衰也与藏传佛教的兴衰同步。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时期唐卡随着佛教传入西藏开始,唐卡画师在不断的对外交流、学习和技艺积累中,经历了从外到内,从无到有,从浅到深的转变 :在地域上,画师的主要来源从早期地单纯依靠域外引入到中期本土画师登上历史舞台,再到后期本土画师队伍壮大成熟从而占主导位置的过程 ;在身份上,唐卡画师经历了从兼职型寺院高僧画师到寺院专职画僧再到民间俗人画师的转变 ;在组织上,随着藏传佛教的发展下的寺院兴建和复建热潮,推动了民间职业画师群体的成熟和官办绘画作坊的出现,各种画派相继诞生;在风格上,唐卡画师经历了从严守传统到大胆革新的路线;在画师的供养上,一种类似于赞助人体制的“施助制度”从13世纪逐渐成熟,形成了与皇家、寺院、世俗贵族、平民百姓均有密切的联系的供养模式,且其目的主要指向宗教而非艺术。从吐蕃王朝崛起到民主改革的历史场合中,涌现出许多灿若群星的唐卡巨匠,代表了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艺术成就,是他们使得唐卡艺术呈现出如今的多姿多彩局面。研究唐卡画师的历史,一方面见证了一门伟大的民间艺术的兴衰,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背后为之努力的画师的坚毅与智慧。
参考文献:
[1]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2]丹巴绕旦,阿旺晋美.西藏美术史略[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
[3]巴·笆囊并.拔协[M].佟锦华,黄布凡,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4][法]海瑟·噶尔美.早期汉藏艺术[M].熊文彬,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29.
[5]康·格桑益西.藏族美术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220.
[6]Steven M.Kossak and Jane Casey Singer: SacredVision—Early Painting from Central Tibet. The
Metropolitian Museum of Art.Abrams.Inc.New York.1999.
[7]于小冬.藏传佛教绘画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
[8][德]大卫·杰克逊.西藏绘画史[M].向红茄,谢继胜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明太年出版社联合出版,2001.
[9][意]罗伯托 维塔利.西藏中部早期寺院[M].伦敦:SERINDIA出版社,1990.
[10]杨鸿蛟.11至14世纪夏鲁寺般若佛母殿绘塑研究[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5.
[11]西北民族学院藏文教研组.藏汉词典[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
[12]陈乃华.无名的造神者——热贡唐卡艺人研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13]张怡荪.藏汉大辞典[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14]李健.西藏唐卡艺人:职业行为变迁与多元平衡策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5]罗文华.龙袍与袈裟[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
[16]熊永松.西藏当代美术研究[D].东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作者简介:刘 畅(1992-),女,江苏盐城人,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博士生,紫金文创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设计艺术史与文献研究。
原刊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