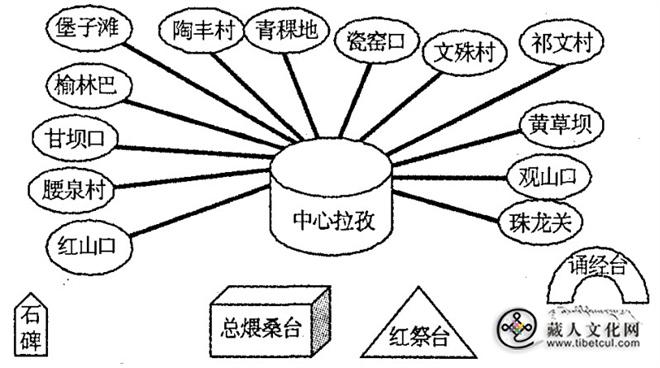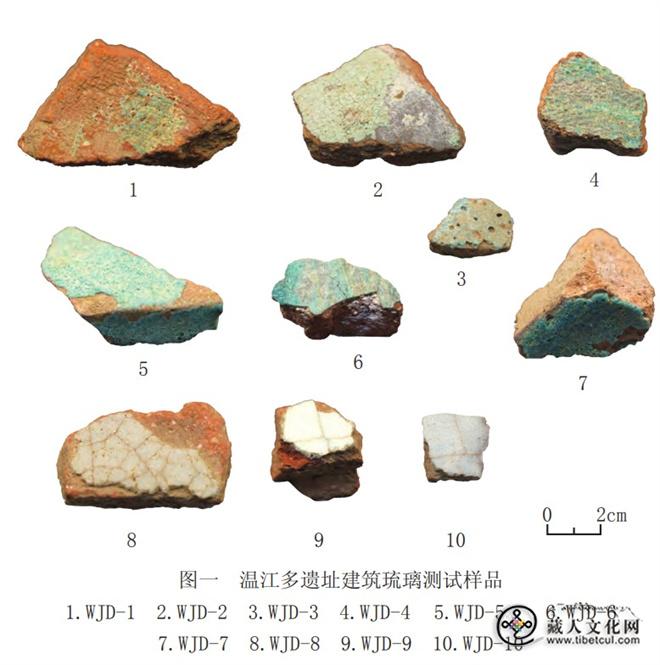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内容摘要:尼泊尔的塗金铜佛在佛教信徒心目中有着不可取代的神圣和珍贵性,作为佛陀身体之一部分的佛像随着信徒流动到世界各地,形塑着佛教社会共同的“业报一布施一功德”观念和认同。从纵向的历史来看,早在公元6世纪,就有了“蕃尼古道”上的政治、文化、商贸等方面的互动往来,藏地最早的佛像加工艺人也是尼泊尔土著民族尼瓦尔人。作为孕育佛教的圣地,直到今天,藏族信众仍然对尼泊尔充满了想象。本文考察了尼泊尔鑒金铜佛像的制作、流通过程和现状,分析了佛像,在跨国别、跨族际的全球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中的作用。
关键词:尼泊尔;湮金铜佛;贸易;藏传佛教
佛像对于佛教信众来说,具有和佛祖一样护佑弟子的神圣力量,作为一种宗教圣物,它不仅是一个连接佛与人关系的中介,同时也是佛法修习观想过程中一个可视的工具,其作用在于让信众面对具象化的实物而忆念佛的功德,心生正念和恭敬心,并发誓发愿学修成就功德。对于普通藏人家庭来讲,每日清晨洗漱完毕,为佛堂里的佛像供净水,寓意崭新一天的开始,日落前收回陈水,意味着在佛的保佑下一天顺利结束。在笔者的老家热贡,谁家的佛堂里供上一尊从尼泊尔请来的佛像是一件无上荣光的事情,左邻右舍都会争相瞻仰叩拜,事实上,对尼泊尔生产的鑒金红铜佛像倍加尊崇是整个藏区比较普遍的现象。
综观国内佛像销售市场,以拉萨、成都、西宁三个国内规模比较大的藏传佛教佛像销售市场为例,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目前国内顶尖的佛像造型技术并不低于尼泊尔,而且在佛像的产量和销量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可价格却要远远低于尼泊尔佛像。笔者在藏区针对不同身份、职业的僧俗做过访谈,让他们在国产和尼泊尔产的佛像中做一选择,答案一面倒地偏向尼泊尔佛像。藏人为什么会如此偏爱尼泊尔佛像呢?尼泊尔佛像又是怎样流通到藏区的呢?基于这样的问题,笔者于2016年9月从西藏边境吉隆乘车进入尼泊尔,重走历史上的“蕃尼古道”,对尼泊尔鑒金铜佛的制作、销售、流通过程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査,现将实地调研情况做一简述。
一、历史上的“蕃尼古道”
尼泊尔对藏人来说,是一个既遥远又很近的他者。藏人称尼泊尔为“瓦域”,“瓦”意为羊毛,“域”为地方之意,即羊毛的地方,从这个对他者的称谓中即可窥见早期尼泊尔和吐蕃之间羊毛贸易的事实。尽管两地之间山路崎岖,峡谷深邃,也挡不住人和物的流动,不管是今天还是久远的过去。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蕃尼古道”、“茶马古道”、“丝绸麝香之路”等等都取道喜马拉雅山,通向尼泊尔和印度。“蕃尼古道”是其中一条以今西藏日喀则市的吉隆沟为起点跨越喜马拉雅山脉,连接吐蕃与尼婆罗、印度的一条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从文献记载来看,尼泊尔和吐蕃之间的往来大约始于公元6、7世纪。随着吐蕃势力逐渐强大,疆土不断向外扩张,曾对尼泊尔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控制,吐蕃军队深入到印度平原中部和北部的这段历史不仅在尼泊尔的文献中有记载,还在诸多藏汉史料如《娘氏宗教源流》、敦煌吐蕃文献P.T.1288《编年史》、《旧唐书•尼婆罗传》等都有记述。公元639年,尼泊尔赤尊公主经吉隆入藏,被诸多学者认为是“蕃尼古道”的开通肇始。后随着吉隆县宗喀山口《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的发现,以及国内的霍威、李孝聪和日本足立喜六等学者在结合《释迦方志》基础上考证,提出“蕃尼古道”从聂拉木、普兰、吉隆出境的东、西、中三条道路,其中吉隆中道是交通最便捷,往来最频繁的一条路线。事实上,在深邃的吉隆峡谷中,有一条贯穿整个喜马拉雅山的裂缝,这条天然通道两头的人民很早就往来于此了,因此“蕃尼古道”在民间开通的时间要远远早于赤尊公主入藏。
据藏文史书《白史》记载,松赞干布的迎亲队伍从拉萨远赴芒域迎接尼婆罗塔库里王朝鸯输戈摩之女赤尊公主,这里所说的芒域就是指今天吉隆沟一带。相传当时公主将随身携带的三尊释迦牟尼佛像留了一尊在此,并修建了帕巴寺,帕巴寺的建筑带有浓郁的尼泊尔风格。随赤尊公主入藏的侍从中有不少是精于手工业的尼瓦尔人,他们“专业金银铜锡玉石及妇女首饰等细工。制作极精巧、至于花卉,雕镂逼真,惟其习尚稍异,然普通礼节,无异藏人。”“此外,他们还兼营银行,并善于经营各种商务。他们也信奉佛教,在拉萨的各大庙宇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足迹,在城里也随处可见。”这些尼瓦尔工匠还参与了拉萨著名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的修建,对西藏雕刻、绘画等艺术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在拉萨八廓街有_家已经传宗三代的尼泊尔佛像专卖店,因为经营者头戴白色帽子,故当地人称为“夏帽嘎布店”(“夏帽嘎布”是藏语,意为白色帽子)。
“蕃尼古道”也是佛教文化传播交流的要道,佛教徒往来于此道,把神圣的佛法带到了吐蕃及中原大地。著名的阿底峡大师途经此地,赞叹其灵气和美景,美其名曰“吉仲”(意为幸福村、舒适村),“吉隆”这一地名由此而来。此外,著名的吐弥桑布扎、莲花生大师、玛尔巴大师、卓弥译师等等高僧都曾取道与此,唐玄奘、玄太、道方、道生、玄会等高僧也通过古道前往尼泊尔、印度求法。据藏文史料《布敦佛教史》统计,“自天竺、迦湿弥罗、尼婆罗等地前来西藏传法的班智达93人,译师192人。”
“蕃尼古道”还是一条重要的兵道。公元647年,唐王玄策出使天竺遭劫,向吐蕃求援,藏王松赞干布派精兵七千余经此道攻打叛匪阿罗那顺,大获全胜。公元1791年(藏历水鼠年)7月,廓尔喀先后两次入侵西藏吉隆、绒辖、聂拉木等地,并一度占领了吉隆,后福康安率领清军直入吉隆和尼泊尔交界的热索,击退廓尔喀,收复吉隆。一些骑兵也留在了尼泊尔境内,据说是尼泊尔藏系民族达芒人的先祖,“达芒”这一族名也是藏语“骑兵”之音译。
“蕃尼古道”也是一条重要的商贸通道,吐蕃的药材、皮毛、乳酪、酥油、食盐,印度、尼泊尔的佛经、铜器、佛像、香料、木雕、宝石,以及中原地区的丝绸、瓷器、纸墨、布料等等,都经此道流通交易,而吉隆则是这条商道上的边境商业贸易中心。笔者在尼泊尔调研时,听说加德满都市内有一个练兵场,古时是尼泊尔国王给赤尊公主的陪嫁地,叫“擦唐”(意为盐市),是蕃尼之间茶盐互换的集市。国内学者张云也指出“古代就有一条自东北向西南贯穿青藏高原的连接党项一女国一天竺三地的食盐之路。”可见,人与物的跨界,跨族际流动交往,在这条古道上由来已久,而作为共享喜马拉雅区域的两个国家,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至今仍在延续和发展。
二、尼泊尔鑒金铜佛的制作
尼泊尔鎏金铜佛的加工地和商铺多集中在帕坦(Partame),这里是尼泊尔的第二大城市,最古老的“历史之城”、“艺术之城”,整座城市可以说就是一个中世纪古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帕坦在古代是加德满都河谷大麦、水稻、小麦、粟等的贸易中心,但如今却是金属、木头、宝石的手工艺制作中心。帕坦的佛像加工场一般是以家庭作坊的形式存在,这些作坊多隐匿于民宅区,若无向导,外人很难发现。这里的住宅房大多为两至三层的独立楼房,房前自带小院。笔者走访的几个作坊均是隐藏在曲折迂回的密集的民宅中,走在小道上可以听到院子里传来叮叮咚咚的敲打声。这些家庭作坊的规模并不大,通常由2-4人组成。
制作鑒金铜佛的匠人一般集中在尼瓦尔人(Newar)中,尼瓦尔人作为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历史最早的土著民族,曾在帕坦有独立的王国,也拥有悠久的金属加工和从事贸易的历史。尼瓦尔人和藏族有着深远的历史交往关系,他们不属于印度人种,语言是藏缅语系,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信仰藏传佛教的宁玛派。虽然在尼泊尔的政治历史上,尼瓦尔人从没有成为主角,但是在文化传承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尼瓦尔人虽然以热衷于佛像艺术著称,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从事佛像加工,传统上只有几个特定的种姓家族才世代传承这份技艺。比如Tamrakar家族以加工红铜盛名,Shakya家族则主要加工黄铜和青铜。据说,原来制作佛像的家庭都和僧人一起居住在寺院里,所有家族成员一起参与整个过程,一起合作完成佛像的制作。
鑒金铜佛的整个加工过程分为五个步骤,分别为做蜡型、外模、浇铸铜液、细节修整、鑒金等五道工序,而其中最难也最考验艺人工艺水平的是第一步做蜡模型和第三步对初具形制的铜佛进行细节加工。制作模具一定要严格按照《造像度量经》中所规定的尺寸规范,一个好的模具可以反复利用数百次,可以一次性生产出大量佛像。而对初步完成的铜佛进行五官、手脚、纹饰等部位的细节加工是很费时费力的工序,技艺高超的工匠在这一步骤中使得佛像脱颖而出,成为精品。
帕坦的佛像加工至今仍然以手工制作为主,有的佛像甚至是全手工作品,所以佛像的制作周期较长。制作一尊12寸释迦牟尼的佛像,通常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此外,尼泊尔佛像制作需要不同工种的艺人合作才能完成,一尊佛像一般要经过7、8个工匠之手,这是不同于国内佛像加工的一个显著特征,艺人告诉我:“一尊佛像倾注了500个人的辛苦劳作。”虽然听来觉得夸张,但其实反映出完成一尊包含配饰的完整佛像需要凝聚多名匠人的才智,大家通力合作的事实。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同样的释迦牟尼佛像,在尼泊尔很难一次买到两尊形制一模一样的。
三、尼泊尔鑒金铜佛的贸易概况
尼泊尔鑒金铜佛作为一个具有向外辐射力的商品,形成了一条凝聚着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文化链条。佛像生产者和商铺的经营者基本上都是尼瓦尔人,尤其是在帕坦,笔者在调研中没有发现其他族裔的人专门开店出售佛像,但在藏人比较集中的博德纳社区,有两三家由藏人经营的佛像专卖店。所有佛像商铺的招牌上都标有醒目的“handicraft”(手工)字样,强调佛像加工的纯手工特色。尼瓦尔人经营的佛像商铺一般多以亲友合资的形式,有自己的生产作坊,可以零售店中摆放的成品,也可以专门定制自己需要的佛像。只要提供佛像的图片、尺寸,一两个月后就可以拿到成品。商铺的经营者一般都会讲英语,有些人会讲简单的藏语和几句汉语,彬彬有礼且极具耐心,会不厌其烦地为客人仔细讲解佛像的特点和价格。购买佛像时可以讨价还价,一旦触到商家的底线,他们就会发誓,非常严肃地亮出最低价格。如果顾客选来选去,几番折腾,最终没有成交,店家依然会笑脸相送,不会流露出丝毫的不满,因此在尼泊尔购买佛像是一件轻松愉悦的事情。懂得市场行情的人,一般不会去店铺,而是直接去佛像加工作坊选购,价格也自然比商铺亲民很多。藏人佛像专卖店很少,但也有为数不多的几家,这与藏人不提倡买卖佛像的观念有宜接关系。
市面上流通的尼泊尔鑒金铜佛的类别按其属性来分,有佛类、护法类、度母类、上师祖师类和一般神灵类等,这些琳琅满目的佛像有各自的功能,消费者购买佛像时都有明确的要求,比如说需要增长智慧的文殊菩萨,增长寿命和保佑健康的药师佛、无量光佛,或者是增长财运的赞巴拉财神等等。根据访谈得知,尼泊尔鑒金铜佛中消费者需求量最大的佛像分别为释迦牟尼佛、度母、药师佛、无量光佛、赞巴拉、莲花生等。这些蕴含宗教涵义和知识的佛像,保留着明显的传统佛教文化特征,其形态、颜色、尺寸等细节都严格地传承和延续了藏传佛教《造像度量经》中的要求,并没有大的或者是明显的创新痕迹。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有佛教信徒也有一些非信教徒;有亚洲人,也有西方人;有观光客,也有艺术收藏爱好者;有个人,也有寺院、博物馆、学校、公司等不同机构和组织,可以说这是一个身份多样,跨越族际和区域的庞大群体,这些形形色色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怀揣不同的目的,把尼泊尔佛像“请”到了世界各地。在调研中得知,其实佛像最主要的消费者并非藏人,而是中国国内的汉族信众,一位报道人告诉我:“一般情况下,藏人多买的是小型佛像,多用来供在自己家中的佛堂,因此购买力不大,加上信仰的原因,他们对佛像的细节要求基本没有,只要是他所需要的尼泊尔手工佛像就行。而汉族信众喜欢买质量上乘,尺寸巨大的佛像,可能是送给某个寺院或者上师的,作为买家,对佛像的细节要求很高。”
面临全球化浪潮的尼泊尔鑒金铜佛,虽然在制作过程中严格地遵循着传统,但在整个全球化贸易过程中还是接受了现代高科技的影响。
比如一旦买卖双方有了相互的联络信息,很多订货、付费、邮寄等环节不再需要双方见面就可以完成,微信(WeChat),Skype等等即时通讯软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笔者多次发现佛像卖家,通过微信接收客户所需佛像的图片,商讨价格、制作时间、细节等问题进行线上交流,线上营销成为尼泊尔佛像贸易中的一种新兴的、重要的交易方式。此外,在泰米尔和博德纳,聚集了大量的跨国快递公司,这些公司通过铁路、公路、海运和空运等各种交通方式,进行快速投递。笔者自己购买的佛像,通过尼泊尔申通快递,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安全到家了,可见从购买到交钱收货,只要消费者所需的佛像有现成品,整个过程较之以往变得更加快捷方便。
四、佛像贸易背后承载的佛教价值观
美国人类学家史拜洛(Spiro)通过对上座部佛教与缅甸人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把佛教分为少数的规范僧侣所追求的、彻底从轮回苦海中解脱的“涅槃佛教"(Nibbanic);普通信众注重积累福德,消除业障,一方面渴望从轮回中解脱,另_方面又安乐轮回,并希望提升个体在下一世轮回中投生地位的“业力佛教"(Kammatic);注重人生当下福利的"祈福佛教"(Aportropaic)三种体系。他认为对于普通信众来说,“与其说宗教理念是用来思维或分类,还不如说宗教是永爱生活的。也就是说,宗教理念是用来提供希望,满足期望,消解冲突,应付灾祸,以及将失败合理化,在'苦'中寻找意义,亦即处理活生生的生活现实。”这一点对藏传佛教社会来说也是极具说服力的,轮回和慈悲是藏传佛教的哲学基础,涅槃境界是每一个佛教徒的最终目标,然而精英分子和寻常百姓之间对于佛教教义的理解和实践有着天壤之别。普通信众对于神圣的佛教所报的却是非常世俗的态度,相信在“六道轮回”中,今生的种种皆为“业力”所致,且相信消解业力的方法就是在今生多多“积累功德”,一个人积德越多,其恶业就会随之减少。
功德积累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持戒,禅修,或者布施,虽然禅修是最为快捷的通往涅槃的方法,但对个体的要求比较高,一般人很难达到要求,相较而言,持戒和布施是信众常采用的形式。其中,持戒要求个体严格遵守佛经中戒律,如有违背反而造下恶业,所以布施就成为最受欢迎的积累功德的方式。布施有很多具体的方法,在佛像贸易中,消费者花费金钱迎请佛像这一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功德,这种功德也是不可让渡的;佛像生产者严守《造像度量经》制作佛像,也是一种功德的积累;销售佛像的业主会一再强调他们卖的是圣物,因此绝对不会漫天要价,买卖双方在这一过程中是绝对坦诚相待的,卖出一尊佛像,然后把所得费用分发给所有工匠,或再做其他形式的布施,因此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积德方式;而承担净化、圣化佛像的活佛、上师这些精英分子满足民众的需求,也是一种功德的积累;面对供奉的佛像,每日供水念经磕头祈福,更是一种功德。
虽然说,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文化的技术层面是最容易改变和变革的,但对于佛像来说,不管外在表层发生多少改变,佛像所蕴含的佛教的神圣性这一核心要素并没有发生变化。随着藏传佛教东风西渐,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佛像成为了一种可以产品化的佛教产物并走向全世界,因佛像而连接在一起的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信众和僧职人员这一庞大的群体,也分享了一个共同的佛教价值观。
综上所述,通过尼泊尔鑒金佛像贸易的总体考察发现,全球化虽然无所不及地席卷了世界的边边角角,但全球化并非只是单向的、同质的,唯没有时空和距离间隔,人与物全球流动的今天,个体对外来事物的体验与回应也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结果,而这种结果可能既是全球化的,也是本土的,民族的。尼泊尔鑒金铜佛的生产者、销售者都非常地强调它的“handicraft”纯手工特性,尽管是国内运用高科技手段、采用质量上乘的红铜或合金,并聘请尼泊尔工匠亲自完成模具,生产出来的佛像在形制、质量和数量都要优于尼泊尔本地生产的佛像,但当在尼泊尔谈及此类问题时,工匠也好,销售商(包括尼瓦尔人和藏人)也好,普遍会告诉你一个“神秘”的答案,说尼泊尔本地生产的鑒金铜佛可能是因为气候、材料、圣人(指活佛)加持等等的特殊原因,中国国内的技术再好,机器再先进也无法相提并论云云。这些口径一致的反工业说辞,其实就体现了个体在文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调适和应对。从另一个角度讲,也为本土文化的重新建构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机会。我们所谓的传统其实也是全球化、现代化的结果,是一个不断被创造和建构的“新的传统”。这也是尼泊尔鑒金佛像在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中仍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原因之一。
研究"物质宗教"(MaterialReligion)是进行宗教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和领域。从整个藏传佛教传播发展的历史来看,佛教用品是始终参与其中并与之紧密相随的,这些佛教用品更是从另一个角度在推动藏传佛教文化的传播,同时也促进了跨区域、跨族际商品贸易新市场的发展。因此,以尼泊尔鎏金铜佛为例,透过佛像的制作、流通过程和贸易链等事实,可以得知作为圣物的佛像在跨国别、跨族际的全球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深刻的意义。(作者简介:当增吉,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宗教教研室副教授、博士)
原刊于《西藏艺术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及引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