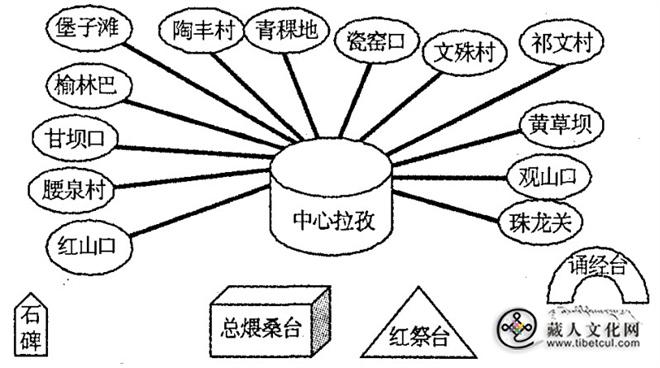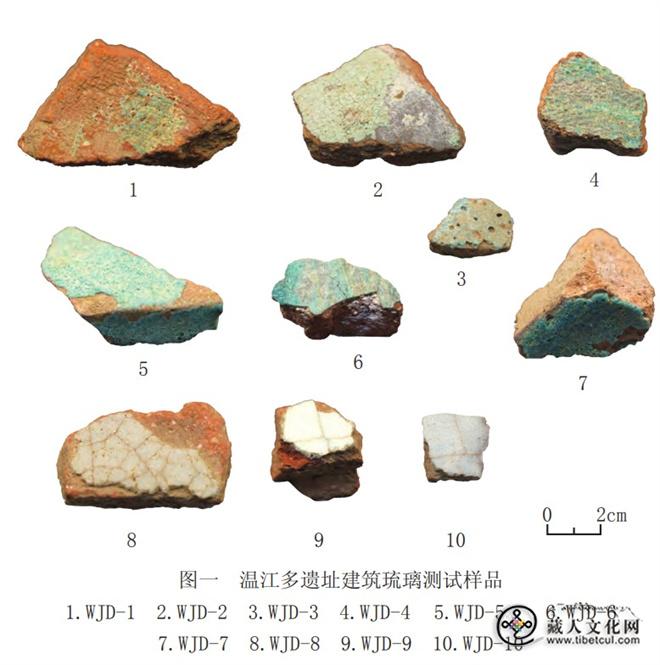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以康区白玉寺“莲师羌姆”为例
摘要:白玉寺莲师“羌姆”凭借对“甲羌”的周期性展演,完善了自身宣扬佛理,整合僧俗,聚揽信众的宗教仪式功能,而围绕着“甲羌”的来源,在不同身份的人群中形成了不同的历史记忆。文章主要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通过对文成公主引入说、汉藏通商说以及皇帝开许说等多重记忆生境的考证,挖掘其背后所隐喻的文化信息。特别是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借助当下时空与历史情境的对话,复现了藏边社会民族之间频繁的经济往来、族际互通及政治秩序互构的发展样态。凸显了在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展演“甲羌”所发挥的培育民众共融情感,强化族群文化认同,构筑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甲羌;羌姆;康区;汉藏交流;文化记忆
康区白玉寺“莲师羌姆”文化是汉藏文化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珍贵文化艺术现象。羌姆仪式是藏传佛教宗教法舞的一种基本形式,传说由“莲花生”大师引入藏地,最初带有强烈的宗教神秘性与神圣性的意味,在藏传佛教宁玛派文化传承中占据重要地位,现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羌姆”仪式也逐渐由请神敬神之舞向娱神娱人转变,其神秘性与神圣性渐趋淡化,现世性逐步增强。从现有的研究内容来看,国内外藏学界对于“羌姆”文化的关注视角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将“羌姆”作为一种表演形式,从戏剧编排、音乐演奏、舞蹈动作、面具制作等角度,分析藏族艺术精粹的审美情趣及其文化价值,如银错(2020)①对化隆县支哈加寺羌姆的考察与岳岚(2014)②对青海佑宁寺羌姆面具的 审美解读等。其二,则是从宗教文化的层面,对其祭祀、供奉、宣法劝善等功能进行探讨,揭示其在藏传佛教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如红星央宗(2021)③在研究新龙苯教寺院中的“羌姆”时,将其回归到“密乘修供仪轨”的范畴中,探讨其仪轨范式、知识生产与社会关系。总之,目前从整体层面对“羌姆”仪式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皆侧重于对各地各寺“羌姆”共有程式的描述与分析,就“羌姆”展演中各剧目的个性细节挖掘尚且不足,仅在旦增益西(2021)④对“朗达羌姆”以及白玛措(2014)⑤对噶陀寺莲师初十羌姆的研究中略有提及。因而普遍存在“以全述偏”的问题,忽视了不同教派、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特征,特别是缺乏通过法舞展演对该文化与人及社群关系的探讨,至于其所包摄的文化交流之隐性话语,更是鲜少涉及。
笔者于 2022 年藏历六月初十(原为藏历五月初十,因疫情原因推迟一个月)于甘孜州白玉县白玉寺参与本年度“莲师法会”,期间发现在整场宗教法舞的表演程式中,除“羌姆”中基本的迎神、供神、切割“林尕”等程式之外,还穿插有部分具有汉式表演特征的情节即“甲羌”。那么为何在如此庄重肃穆的宗教法舞中会穿插带有“逗趣”性质的舞蹈程式呢?作为仪式中明显外来的汉文化符号,究竟渊源于何?又是何时、如何作为共享文化,并最终整合为一完整的文化事项传承至今?而在今时今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大背景下,“甲羌”的展演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对于这些问题答案的探讨,无疑将成为对新时代如何重述各民族“集体记忆”,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间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有力回应。
一、白玉寺的莲师“羌姆”
“羌姆”,即藏文“འཆམ”音译,原意为跳跃或舞蹈,后随佛教金刚密乘在藏地的传播,逐渐演变为密宗修供仪轨的一种表现形式。当前学界从已有的文献材料推论的一种普遍观点为,“羌姆”发端于赤松德赞时期,莲花生大师在桑耶寺落成大典上所创立的金刚步舞,即以印度佛教密法的修习方式与藏地原始苯教文化中的傩仪相结合,用舞蹈的形式来调伏鬼神,驱邪穰灾。这一情形在藏传佛教早期文献中皆有佐证,如《莲花遗教》载,莲花生“第一个将舞蹈形式用来表演降魔伏怪的故事。”⑥又《五部遗教》云:在庆祝 桑耶寺落成的开光法会上“咒师们拿着鼓跳羌姆”⑦“莲花生大师为调伏恶鬼为所行仪轨中率先运用了一种舞蹈。”⑧另外《西藏王臣记》载:“莲 花生大师降伏了一切八部鬼神,令他们立下誓言,制定诸神所喜的祭祀物品,又说出了镇伏凶神的歌词,在虚空中作金刚舞。”⑨虽不能将彼时“金刚舞步”与后来的“羌姆”完全等同,但从二者的呈现形式我们可以推断其中的渊源关系。现今“羌姆”当是随后弘期藏传佛教各派鹊起而复兴,由各寺院根据佛教教义及自宗密法修行特色在原本巫舞的基础上重新完善编排,最终形成具有规范法本的系统化的金刚法舞。其在不同的法会期间进行展演,并被重新赋予了献祭、供养、驱邪、加持等多重性质。
莲师“羌姆”,则是为纪念祈请莲花生大师而举行的大型宗教仪式展演,其主要内容为设坛净地,再现了吐蕃时期迎请莲师及莲师化身八相,加持众生的场景,普遍流行于宁玛派以及与宁玛派关系密切的噶举派、萨迦派当中。白玉寺作为宁玛派六大祖寺之一,始终尊莲花生大师为本尊佛,自然也有举办莲师法会跳“羌姆”的传统。
白玉派莲师“羌姆”全称“大自在申月初十供舞——净相增盛——黑帽派莲师金刚舞”,是“由伏藏师古如·曲旺的净相白马与黑帽两种传轨中发展出来的黑帽派传轨,遵照帕仲乃东的传轨编排。”⑩“据说是在第七代德格土司向巴彭措时期,随西藏楚布寺噶玛·让迥多吉黑帽法脉传至八邦寺,最终与宁玛白玉派合流于白玉寺”⑪。其羌姆表演共包括二十五个程式,“跳舞僧众披戴面具、黑帽及披风起舞。”⑫展 现了净地、迎神降神、莲师八相加持、荟供、娱 众等整个过程,具体如下:
二、“甲羌”在莲师“羌姆”中的展演
“甲羌”即“རྒྱ་འཆམ”,为“རྒྱ་རྩེད་ཀྱི་འཆམ”的简称,“རྒྱ”指汉族、汉民,“རྩེད”有嬉戏,嬉闹之意,“རྒྱ་རྩེད་ཀྱི་འཆམ”也意为汉民或汉地嬉戏之舞蹈,其通常作为莲师法会所跳法舞程式中的一部分展演,一般包括两个戏目,即戏狮舞与杂嬉舞,从表演者衣着与舞蹈动作来看,具有明显的汉式嬉戏特征。根据现有文献及田野调研材料,笔者发现,对“甲羌”这一情节的展演普遍流行于藏彝走廊地带,且集中分布于康区宁玛派及与其在法脉或地缘上有一定关系的噶举派、萨迦派寺院之中,包括德格地区白玉寺、噶陀寺、佐钦寺、八邦寺,昌都康巴噶寺,玉树赛康寺等等,却而少见于卫藏及安多地区。
白玉寺的“甲羌”情节集中于整场莲师“羌姆”的尾部,属于整场法舞仪式中的补足程式,即第二十三场嬉狮舞(སེང་གེའི་འཆམ)与第二十四场杂嬉舞(རྒྱ་རྩེད་ཀྱི་འཆམ)。演出时,分别由两组僧人(一般为两人组与四人组,有的寺院是八人组)著黄色与蓝色的汉式对襟短褂与长裤,头戴清代官男子的“暖帽”,在高亢的唢呐声中,先后以哈达引狮、戏狮,并在环场巡游的过程中与围观僧众互动,人们可以抚摸甚至拉拽雪狮,与其互逗。本场表演间隙,表演者们会围成一堆,作讲汉语之姿,而后进行倒立、叠罗汉、翻筋斗、摔跤等表演,形式与汉地民间流行的杂耍类似。由于法脉相承的关系,德格地区白玉寺分寺埃旺寺等寺(ཨེ་ཝཾ་དགོན)的表演形式与祖寺相同。而在噶陀寺,“甲羌”的表演形式更为丰富,除与狮互动外又分为两场,即“汉官表演”(རྒྱ་དཔོན)与“杂耍表演”(རྩལ་རྩེད)。其中,汉官衣清朝官员华服,在杂耍之前,绕场转圈,脱帽致敬并用汉语向观众们问好。表演杂耍的舞者服饰则为刺绣繁复的对襟坎肩,且表演过程中需要俗人辅助抬杆,才能进行踩高跷、爬平衡杆、单双杠等演绎,其技巧动作难度更甚。另外,有些寺院如八邦寺还有长袍马褂样式的演出服,甚至有的衣服上还会印有“清”兵字样。总之,无论从语言、动作还是服饰的角度来看,此一情节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世俗娱乐意味更强,而这显然与庄严肃穆的宗教神舞形成强烈的对比,且其并不存在于早期莲师“羌姆”的法本当中。那么,这一情节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被编排进入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并逐渐整合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固定下来?其背后又有何种文化逻辑在悄然运作呢?根据笔者的多方访谈,我们将在后文作出探讨。
三、关于“甲羌”的多层记忆与历史隐喻
关于白玉寺的“甲羌”从何而来?这一问题的答案,就笔者目前搜集到的口述与文献材料来看,各家众说纷纭,争议颇多,似乎对于同一事件,人们形成了多层次的历史记忆,口述中对于具体的历史时期、人物、事件多数模糊不清,甚至在一些叙述与事实之间存在明显的相悖性。
(一)作为共享之历史记忆:文成公主引入说
据白玉寺负责教习“羌姆”的堪布所述,“甲羌”这一表演形式早在吐蕃时期,便由文成公主引入藏地。其与莲花生大师所创金刚舞步一同被安排呈现在桑耶寺落成的开光大典上。汉嬉部分作为开光之后的余兴节目,包括了狮子舞、长寿和尚、鹿舞、杂耍背人等等,除用以供养莲师与寂护大师之外,也有为君助兴,与臣民同欢的效果。⑬
这一说法,基本存在于寺院年长一辈,资历颇深,教法知识渊博,特别是专司“羌姆”教习的堪布之中。他们大多熟知藏传佛教教法史,特别是对于本派重要人物及事件年代能够如数家珍。“‘甲羌’这个,以前桑耶寺开光的时候就有,你去找那些藏传佛教的史书,里面都写了。”顺着这一线索,笔者开始翻阅相关史籍,并结合堪布们的口述做出了相应推论,以回应自己的疑问。为何从表演者服饰来看,非“唐制”的表征十分明显,且白玉从地缘上看与吐蕃腹地又相距甚远,但寺院中在知识层面颇具影响力的堪布们,却仍旧将其追溯至桑耶寺修建甚至是文成公主入藏时期呢?
有关桑耶寺开光大会上的表演,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有相应的记载:阿阇黎菩提萨埵在为桑耶寺开光之时,举行了盛大的娱乐活动,娱乐内容是:“一个名叫俄帕拉(རྔོག་ཕ་ལ) 的人,能轮换骑乘七匹骆驼;有些人将刀集在一起,在奔驰的马上,将刀掷向对面的刀门上(རལ་གྲིའི་སྒོ་འཕེན);有的人两人相叠(མི་ཉིས་བརྩེགས),(似叠罗汉)手举旗幡等等”⑭。开光后举行喜庆宴会时,“所有男女少年装饰打扮,手执牦牛尾,击鼓、歌唱、舞蹈,他们(学着)牦牛叫声、狮子吼声和老虎啸声。他们(戴着)面具(扮成)幼狮,舞蹈者(佩以)美丽的装饰,手里拿着鼓,游戏、散步等等。上述人们向赞普供奉。”⑮从这 些表演动作中,我们的确能够看到部分“汉家杂嬉”之影。但确认其是否为“甲羌”,以及是否 能将其来源追溯至文成公主,还有待商榷。
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有带唐朝乐舞。《柱间史》中曾记述了唐皇为文成公主准备的丰厚嫁奁,“百鸟朝凤雄狮吼,日月争辉彩虹舞,松柏常青百兽走,绫罗绸缎织锦绣,赠予赞普当希有。”⑯并称赞其“舞乐无不精通”,⑰同时,《娘氏宗教源流》中也提到,文成公主在启程之时,随“有二十五岁且身手敏捷的勇武力士五百人,贵族血统芳龄十六的少女五百人”,且运送释迦牟尼佛像之时,“其周身围绕众侍女,弹起琵琶乐,唱诵庄严歌。”⑱此时由公主带来的乐舞是否为后期桑耶寺开光时所表演的舞蹈,难以判断。但回归唐初的宫廷生活,即可了知,唐代百戏已在宫廷与民间并盛,宴群臣时,亦备百戏。且此时,角抵百戏类型颇丰,不乏倒立、走索、耍大雀、戏狮等剧目。高祖武德初,孙伏伽曾上书谏言百戏之过:“百戏散乐,本非正声,隋末始见崇用,此谓淫风,不得不变。近太常假民裙襦五百称,以衣妓工,待玄武门游戏。臣以为非诒子孙之谋。传曰:放郑声,远佞人。今散妓者,匪《韶》匪《夏》,请并废之,以复雅正。”⑲足以见得百戏在宫廷中的影响程度。因而,在为公主挑选的陪嫁中,存在专擅百戏者也不足为奇。另外公主本身精通乐舞,入藏后,在传授农耕历算等技术的同时,于宫廷中推广乐舞表演也不无可能。更重要的是,文成公主作为汉藏友好交流之始,开启双方文明互通之门,也加深了吐蕃对中原文化的认同。
又有金城公主入藏之际,“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⑳,赤松德赞出生后,玄宗又派一汉族戏童与其为伴㉑,便不难推断赞普曾受到中原戏目的熏陶,又桑耶寺修建过程中本身便有汉族工匠的参与,则在其开光后的盛宴上,出现“汉家杂嬉”也符合逻辑。
那么彼时盛景是如何跨越时代与地域的重重阻隔,重现于今日白玉寺莲师“羌姆”的展演中呢?笔者推演了如下过程,即或许在最初为桑耶寺开光而跳的神舞中,除了驱鬼酬神的宗教舞蹈之外,的确也安排了娱人的歌舞嬉戏,但这一表演并未有明确的汉藏区分,只是在唐蕃长期的交流中,这些乐舞逐渐融入了中原文化的成分。这一场景由当时的佛教徒所记录,并在朗达玛灭佛之际,与佛法一同被四散而去的密咒师保留,并以口传身授的方式在本家师徒之间秘密传授,后弘期当宁玛派在康区扎根之时,他们便将桑耶寺开光仪式上的跳神舞蹈整合到一起,沿用吐蕃时期以神舞供养莲师的形式,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代代承袭。由此,在康藏文化圈中,无论是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在举办莲师法会时,这一具有汉式风格的“甲羌”展演便普遍存在。
另有一说辞为,文成公主入藏之时,经过白玉地区,随同进藏的侍从们带来了汉家舞蹈,并在穿越康区的过程中由当地百姓习得,因而后弘期康边藏传佛教衰而复荣之际,被各教派纳入“羌姆”中以为供养。总之,无论何种缘由,文成公主在“甲羌”这一剧目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直至现在,白玉地区还流传着诸多关于文成公主经过此地时的传说,且尚存一一对应之圣迹,如公主插手杖处、梳洗散发之地等,皆成为天然交互汉藏民族记忆、融合民族情感的共享文化符号。
(二)作为民间之交往印迹 :汉藏通商说
相对于上述从史实层面尚经不起推敲的说法,寺中中青年一代僧人的口述,则展现了一种更为生动的社会记忆:“那个‘甲羌’,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从什么时候来的,就是跟着堪布们一代一代学下来的,他们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学。以前听家里老一辈的人讲过,很早很早以前,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来这边的汉族人很多,有很多开店做生意的,这边住下来之后,过节的时候会跳他们的舞,耍杂技之类的。后来和本地人关系慢慢变近了,经常一起玩儿。这边藏区本来就有很多节日,民间的也好,寺院的也好,汉族的也会来参与,就是表演他们自己的节目,后来就慢慢地保留下来了。”㉒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忘了是什么时候了,反正这边来了很多内地人逃难,他们就是耍那个杂技、舞龙舞狮子谋生,后来慢慢做生意定居下来之后,寺院也会邀请他们表演啊之类的。他们内地的亲戚朋友也会来看他们,一起过节,他们就这样带过来的。”㉓
由上口述可知,他们脑海里有关“甲羌”的知识,显然是经由前辈们身授与口传而来。虽然此二种说辞对于汉族人为何而来的记忆不同,但明显反映了某一年代汉族人大规模主动进入本地藏族社会并与当地人发展亲密关系的过程。另外,在“做生意”这一点上,本地群体也达成了一种记忆共识。这也说明,汉藏之间的商贸互通在此地历史语境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同时也能反映出康巴人对于“做生意”的重视程度。
王明珂曾在其著作《羌在汉藏之间》中将经由口传或文字传递的社会记忆都视为广义上的“文本”,“‘文本’之意义,在于‘文本’与‘情境’的相互诠释,文本产生于情境中(texts in context),情境也在文本中浮现(context in texts)。”㉔由此,对上述口传“文本”再进一步分 析,我们能够发现,与前言“文成公主引入说”相比,此番记忆在时间上似乎距离更近,空间更明晰,因而即便没有明确的史料佐证,我们也能够根据其关于做生意、逃难等的叙述,结合《白玉县志》中所载“汉族人来到白玉,始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㉕,将“甲羌”进入白玉的大致的时间追溯至明末清初,至于何时被纳入寺院“羌姆”体系之中,则必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汉藏磨合期,对此需再三斟酌。
回顾川区史料,有助于我们寻找印证上述记忆的线索。川藏之间的人货流动早在唐宋时期便陆续兴起,然直至明末清初,汉族移民才开始沿川藏道大量涌入康区。其主要原因便是上述所记“战争”事件。即:明崇祯年间,张献忠“屠蜀”而后败亡,此后川区便在大西军残部、南明军、清军以及其他农民军相互混战之间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与此同时,旱灾、水患、瘟疫等皆在此地蔓延,因而为“躲兵避祸”,大批汉族人选择西渡谋生。及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昌侧集烈之乱㉖”之后,于1705 建立横跨大 渡河的泸定桥,《御制泸定桥碑记》中载:“桥成/凡使命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而不致病於跋涉”㉗。“当时清廷进兵打箭炉(今康定),势力达雅砻江以东地区。到雍正年间,清军大败和硕特部,中央王朝的力量深入到整个康区,并将昌都地区及金沙江以东各土司地划归四川管辖。于是,除汉兵之外,经商、采金的汉人也源源而至。”㉘彼时,白玉地区扼守南北进藏路线中间之要道,是“茶马互市”必经之路,战略地位颇为重要,《清实录》中亦称,“三暗巴地方。系通藏大道。”㉙因而,此地成为清政府“王化”之重地,亦间接带动了当地较大规模的产品交换,促进了川康一带汉藏一体化的进程。
在此基础上,当地人借由对“甲羌”的周期性展演来复现彼时情境,使其在现实语境中被反复激活,又以代际传述来储存那段鲜活的集体记忆,而这些记忆又帮助我们重回到历史的脉络中去,为诠释当代康区汉藏“与共”的格局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作为官方之政治礼仪 :皇帝开许说
以上僧人们的口述记忆,多少夹杂了当地历史或野史甚至是虚构的成分,即便能够从庞杂的文史资料当中抽丝剥茧,但细加推敲,我们也难以寻找到这种“汉家杂嬉”是在何种情况下进入“羌姆”的直接依据,很难说在莲师法会上展演“甲羌”究竟自何时开始。而下面的说法,则能够帮助我们大致锁定“甲羌”具体的展演时间,且能够从汉藏史籍中得到双向认证。
“这个主要白玉寺第一世古钦法王被封为国师之后,清政府对于白玉的一个赏赐里面的一个部分,就是特许你寺庙在举行大法会的时候可以有这个杂耍舞蹈,当时说第一批在白玉寺表演的人还是从汉地带过去的,有这种说法。”㉚
该叙事来自一位正在白玉寺学习的小活佛,因自小接受寺院对于活佛的全面培养,所以虽然年少,但藏汉英语言三通,古今史学、佛教义理信手拈来。根据其叙述,我们找到了寺志中对应的第一世古钦法王,也就是白玉寺第四任主持克珠·噶玛扎西(1728-1790)的生平记载,如下。
“尊者四十四岁时,清朝乾隆皇帝与嘉绒小金土司绕登嘉波发生战争,乾隆皇帝迎请尊者前往汉地。……,尊者以观法成功阻遮绕登嘉波降石雨。又为清朝军队制作护身结,……,绕登嘉波最终战败,清朝皇帝的威望直达三有之顶。乾隆皇帝册封尊者担任自己的帝师,赐予封号、诏书、盛于旃檀木与象牙所制宝盒中的金印、银印、象牙印、玉印、与用各种珍宝制成的四印等共计八颗狮柄印以及御桥,每年均广奉田赋以作供养。此外,又奉献了金银、内库哈达、嵌花锦缎等广如虚空的众多财物。”㉛
根据寺志推算,该活佛四十四岁时恰好为1772年,而乾隆二次克复小金川的时间在1771年至1776年之间,与寺志所载时间吻合。且《清实录》中对白玉寺喇嘛赴军营念经一事亦有记载,并询问章嘉呼图克图之建议,是否将其纳入扶绥康藏策略之内。
“又谕、前阿桂奏、欲于噶拉依建庙。令达赖喇嘛、选择有梵行大喇嘛往彼居住一款。……因思前此德尔格忒白玉寺。请赴军营念经之斯第呼图克图大徒弟噶尔玛噶什等三人。曾在两路军营念经。阿桂等称其颇有梵行。或于此内择其最优者。在噶拉依新庙居住。管束众喇嘛。并可令留住之人。来京觐谒。承受恩赉。潜移默化。徐消凶悍咒诅之邪术。似为妥便。”㉜
通过此双向印证,我们能够确认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在克珠·噶玛扎西与乾隆帝之间,也就是白玉寺与中央王朝之间,的确存在着贡赐关系。但以上两则材料中并未明确指出是否赏赐中包括了对展演“甲羌”的开许,反而在噶陀寺活佛的传记中,则直接点明此事。
“根据《斯灯切鸠传》载:‘大师应清朝皇帝之邀到内地,帝特别喜欢,赠送一套乐队及杂耍班子。’而后噶陀寺一年一度的泽鸠节上出现此杂耍队,有摔跤、单杠、双杠等,小喇嘛们特别爱习此杂耍。”㉝
另外,当笔者问起噶陀寺一位活佛是否知晓为何白玉寺也有同样的表演形式时,他是这样回应的:“白玉那边肯定是我们这边传过去的,毕竟他们的法王是我们法王的弟子,而且你没发现,但凡研究宁玛派,无论你研究什么,最后都会追溯到我们噶陀寺这里吗?”㉞诚然,这一回答带有明显的“夸耀”意味,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为我们分析白玉寺中流传的“皇帝开许说”提供了间接佐证。众所周知,白玉寺与噶陀寺在法源上渊源颇深,地理位置相近,几乎经历了相同的历史进程,且两座寺院及其分寺之中都存在“甲羌”这一表演形式,因而,二者对同一事件所述的相同历史记忆,姑且可以成为相互补充的证据。
当前,暂且抛开二寺对“甲羌”来源的争议不谈,我认为这一传说的重点并不在于是哪位活佛所受之赏或是我的传到你那儿去,而在于,一方面,它鲜明地反映了清政府平定康藏 之乱后,以“因俗而治”之策怀柔边地,安抚传统势力,以“赐物”这一政治礼仪建立起与受赐地方文化认同,达到施政于藏边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边缘传统势力对于中央王朝的“攀附”心理,期望借此争取高层护持,赢得继续统辖一方的合法性,赚取促使政教集团快速发展的机会。同时,对比二寺僧人的叙说,也暗含了藏传佛教同一教派内部在宗教地位、权力、声威上的竞争。
四、展演“甲羌”的仪式功能与现实回应
通过对白玉寺“甲羌”渊源多重表述的探讨及其生成意义的分析,使我们意识到,某一文化事项的意涵与其发生之初所处历史语境、不同社群成员各异的认知、利益所指等因素息息相关。由此,我们回归文章开头,尝试解读关于“甲羌”的情节安排、来源口述以及与事实社会发生何种共振等相关问题。
(一)“甲羌”在“羌姆”中的功能发挥
作为一种以彰显藏传佛教神圣崇拜为目的宗教仪式,莲师“羌姆”经历了一个从仅限寺院内部进行隐秘具身训练,到惠及百姓公开展演宣法的发展过程,使晦涩深奥的佛教哲学知识借庄严的舞蹈形式呈现在信众面前,实现了仪式固有的驱邪避祸、救度疗愈、宣泄情感、凝聚族群等功能,此在学界已得到详细且全面地阐释。而“甲羌”作为完整仪式展演中的一环,自然也发挥着这些协同作用,便不再予以赘述。
在此,我们暂且不需汲汲于剖析那些宗教的普世性功能,就其在整个法会结构中的位次及表演的观赏性与技巧性而言,互动与逗趣贯穿始终。戏狮的过程中,雪狮时不时被表演者引向观众席,与老少信众嬉戏玩耍,灵活翻滚,甚至冲撞僧众。当杂嬉开始时,雪狮们便趴在场地一旁,一颠一颠地摇头晃脑甩甩尾巴,此时的观众席中,而杂嬉者们在进行摔跤、擒拿、跳杆等表演时,由于动作有一定的技巧性,难免会有失误,便常常引得观众们爆发哄笑,调侃声、戏谑声此起彼伏。此二场戏,也是整场仪式中狂欢的开始,雪狮的横冲直撞仿佛冲破了先前构建的神圣场域,打破了场内的阶层秩序,此刻僧俗被压抑的情绪被逐步调动起来,那些被请下凡间的神灵也不再令人颤畏,为后续法会的高潮部分——供养莲师,求见解脱的开展,营造了高涨的内场氛围。
由此,从莲师“羌姆”展演的完整程式来看,“甲羌”的演绎凸显出一种奇怪又滑稽的反差感,也正是这种可被注意的反差感,将观众从庄重肃穆的宗教仪式中释放出来,使部分信众开始从文化审美的视角来审视“羌姆”的展演,由参与法会逐步转向公共集会的层面,为宗教的“祛魅”准备了条件。同时,这一形式上的冲突也蕴藏了现存秩序下神圣与世俗、神性与人性、宗教组织与王朝权力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则在我们追溯“甲羌”之渊源,爬梳与这一事项相关的多重记忆与书写的过程中展现出来,使我们能够借此回应当下,进而面向未来。
(二)“甲羌”展演的现实回应
当我们从仪式的框架中跳脱出来,从一种表演或文化戏剧的视角重新审视当年这一地族群借助演绎这一“汉家杂嬉”所希望表达、传递与沿承的社会记忆,我们能够发现,无论这些记忆信息的外显模式或描述类型如何多样复杂,其内蕴的、默示性信息皆指向同一目的,即让一个拥有复杂组织结构,多元文化观念,跨越几代波澜的人群获得共同的身份并长久地稳定下来。
1.从集体记忆到文化认同
历史学家关心历史叙事的真实与否,常常忽略了对那些看似荒诞的民间记忆的诠释,但正是这些被“丢弃”的野史,其背后往往隐含了关于地区文化、民族心理倾向等重要的叙事逻辑。康区作为吐蕃与中原皆鞭长莫及之地,在追寻“甲羌”展演的肇始之时,仍将其记忆指向了文成公主,这显然浅含了民众主观建构的成分,但这也恰恰流露出人们对于这段情谊佳话的重视以及汉 藏民族之间早已互溶的文化认同。
一方面,长期处于西藏与中原王朝边缘话语之下的康藏之地,将原本发生于吐蕃腹地的“文明化”事件拉入自己的社会情境之中,通过“甲羌”的展演并归其因于中原文明,极力将自身纳入整个吐蕃文明进程的一环之中,借以摆脱被本民族 妖魔化、污名化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在汉族移民入康的大背景下,演绎带有汉家风格的杂嬉舞蹈也成为本地藏族接纳汉民的心理前提。同时,也是这些来自汉地的“异乡浮客”寻找文化共性,化陌生为熟悉,孕育共同情感,最终实现和谐与共的重要纽带。正如石硕在论及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时提到:“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各民族及族 群进行认同的重要标志,它代表着这些民族或族群的记忆中的历史及变迁过程,虽然这些历史记忆未必都是真实的,其中不乏主观和虚拟成分,但对于这些民族或族群而言,共同的历史记忆却是其民族性及文化深层内涵的重要体现。”㉟
2. 从商贸互通到族际互动
仪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过去的重演,它承载传统,指向后方,再现过去的社会图景,并由此搜寻构拟当下的历史根源。从顶戴礼帽、对襟短褂等标志服饰,到舞狮、戏雀、角抵、撑竿等肢体展演,“甲羌”中的各项元素无一不是对当年汉藏边地市井街巷热闹场面的复现,也是对当地人历史记忆中由两族间频繁商贸互通而建立的亲密关系最好的撑拒。
马克思认为“交往是一个历史性范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交往的范围、形式与手段将发生巨大的变化。”㊱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需求的多元化,商贸互通早已不再是康藏区域族际间流动的唯一方式,对日益增长的精神治愈的渴求使川西秘境成为人们心中向往的诗与远方。而“羌姆”展演作为康藏文化展示的窗口,除了满足人们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理之外,“甲羌”在其中作为一种熟悉感、娱乐性极强的视觉呈现,能够极大地调动起旅行者的认同情绪,使人们直观地感受到康巴地区主动释放的友好包容的情感信号,淡化排他性倾向,消弭汉藏隔膜,进一步推动族际间的互动往来,为持续性书写共同历史创造条件与动机。
3.从边陲之地到华夷同体
现有的宗教领袖传记、县志以及汉文史料,与寺院中属于精英阶层的活佛口述,皆将展演“甲羌”的渊源追溯至宗教领袖与中央王朝之间的联系,试图通过档案书写或自身对群体的影响力,将这一典范记忆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灌输给社会大众。由活佛被朝廷诏封为帝师,而后开许演绎“甲羌”作为供养或是封赏,其背后所透露的关键信息实则为地方声威与国家权力在利益权衡之下的各自妥协,是地方与中央互认的中介。
在中央对康藏地区的边地战役中,朝廷逐渐觉察到在宗教领域依靠王朝强制性力量难以彻底深入,因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便转而采取一种柔性渗透的方式在地方社会中建立国家秩序,由此,地方宗教领袖便是一个极好的切入点,而法会展演则是宣誓声望地位的最佳形式。将代表国家权威的“甲羌”纳入宗教法舞之中,并借由双方精英之手将其渊源固化于中央与地方的历史知识之内,使统治者与社会记忆结成联盟。通过仪式的操演,一方面地方教团组织传达出归附中央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将中央的政治诉求合法化。从此,这一“匪祸蛮荒之地”逐渐跻身于社会主流话语体系之中,从政治的层面强化了华夷同体的合理性。
当下,白玉寺寺庙乐舞作为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甲羌”在其中的演绎既是汉藏民族间交融共生的活态表达,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生活样态的彰显,更是对当下民族共同体构筑最为有力展示。
五、结语
仪式是人类建构现象事实,表达情感诉求,诠释现实意义的重要载体。“甲羌”在莲师“羌姆”仪式中结合了视听等感官,以多维立体的实践与颇具生命力的活态形式进行演绎,并借助普罗大众或精英阶层之口建构多样的集体记忆,以本土化的文化表达,将这些共同书写的记忆在当代人群中流传、存续,将共同体中的各民族成员编织在一个紧密的“复合文化”体系之内,统摄于中华民族共建的文化系统之下。
康纳顿认为,“社会记忆的存在即是因为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诉求”。㊲由此,剖析有关“甲羌”多层文化记忆形成的底层逻辑,我们能够发现在其繁复、多元的表象之下,蕴含了民族间共历的错综复杂的社会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政权张力、情感黏结与文化认同。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界限,打破了语言与文字的壁垒,回应了当下我们对鲜活的民族交际的需求,对共同政治命运的追求,对和谐社会图景,平等价值共识的渴求。
注释:
① 银措.藏传佛教宁玛派“羌姆”研究[D].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
② 岳岚.藏传佛教羌姆面具的审美探析[D].西宁:青海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4.
③ 红星央宗.万象之舞:新龙苯教羌姆的知识、经验与关系形貌[D].厦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
④ 旦增益西.论“朗达羌姆”的起源及其仪式性[J].西藏艺术研究, 2021(04):58-71.
⑤ 白玛措.康区噶陀寺古鲁羌姆仪式结构[J].中国藏学,2014(01):138-144.
⑥ 邬金林巴.莲花遗教(藏文版)[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461.
⑦ 欧坚朗巴掘自雅隆石窟,多吉杰博整理,五部遗教(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1986:140.
⑧ 欧坚朗巴掘自雅隆石窟,多吉杰博整理,五部遗教(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1986:141.
⑨ 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57.
⑩ 麦波,白玉历史与现状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52.
⑪ 根据白玉寺僧人口述整理.
⑫ 麦波,白玉历史与现状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52.
⑬ 根据白玉寺金刚舞教习堪布访谈整理。
⑭ [明]巴卧·祖拉陈瓦著黄灏,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304.
⑮ [明]巴卧·祖拉陈瓦著黄灏,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7:305.
⑯ [宋]阿底峡发掘,卢亚军译,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110.
⑰ [宋]阿底峡发掘,卢亚军译,柱间史——松赞干布遗训[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115.
⑱ 娘·尼玛韦色著.娘氏宗教源流(藏文)[M],拉萨: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204.
⑲ 陈高华,徐吉军主编;吴玉贵著.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M].2001:761.
⑳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3部[M].1997:214.
㉑ 巴俄·祖拉陈瓦著,智者喜宴(藏文)[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59.
㉒ 根据白玉寺秘书 QMZW 访谈整理.
㉓ 根据白玉寺教师 GSJC 访谈整理.
㉔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85.
㉕ 白玉县志编纂委员会,白玉县志 [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75.
㉖ 昌侧集烈之乱:清康熙三十九年(700年),打箭炉营官昌侧集烈欲凭借固始汗之力独霸一方,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唐希顺率部进驻打箭炉,此次清廷对康区的大规模用兵历时半年之久,对于发展川藏贸易、恢复打箭炉秩序、稳定康区局势起到积极作用。
㉗ 程思源主编 . 中国全史·第十二卷:通史 [M]. 2004:2266.
㉘ 白玉县志编纂委员会,白玉县志 [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75.
㉙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第 2 册 [M]. 1994:1091.
㉚ 根据白玉寺五年级僧人 DG·LSJC 访谈整理 .
㉛ 麦波,白玉历史与现状研究 [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50.
㉜ 西藏民族学院历史系.清实录 藏族历史资料汇编 (共五册)[M]. 1981:1405.
㉝ 白玉县志编纂委员会,白玉县志 [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444.
㉞ 根据噶陀寺僧人 QMZR 访谈整理.
㉟ 石硕.关于藏彝走廊的民族与文化格局——试论藏彝走廊的文化分区[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2):1-6.
㊱ 王瑜卿.民族交往的多维审视 [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15.
㊲ [英]保罗·康纳顿 . 社会如何记忆 [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