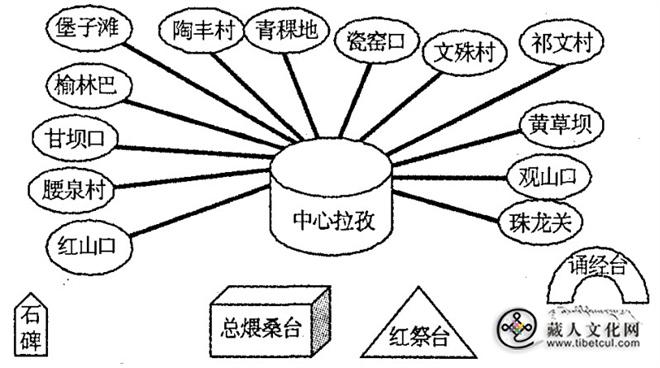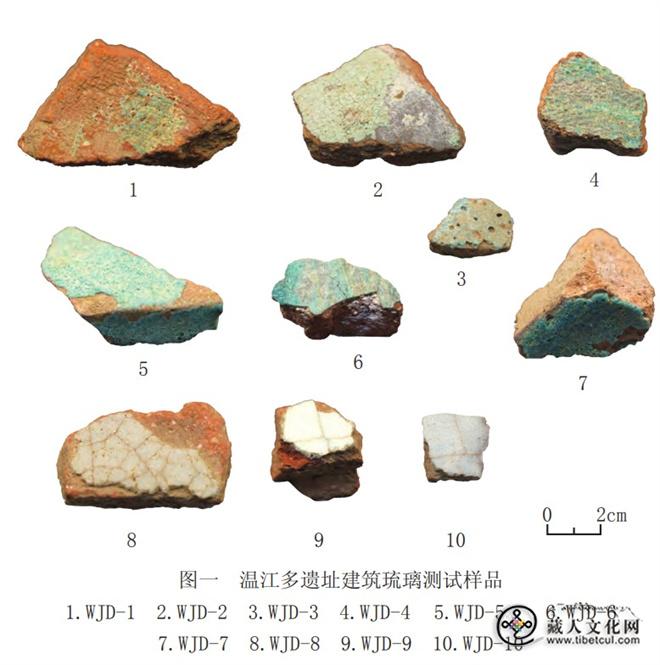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提要:普巴一词在藏语语境中有工具、武器、法器、神灵等不同的含义。普巴由法器演化为神的文化现象,与莫斯《礼物》中的“混融’’概念相似,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藏传佛教哲学与藏族民俗案例也印证了此现象。由此管窥藏传佛教及藏文化对物的认知与实践逻辑,为人类学物研究提供民族志资料。
主题词:普巴藏传;佛教;法器物;混融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藏传佛教普巴的研究,国内很少有人涉足,但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有CathyCantwll、RobertMayer的敦煌吐蕃文献中关于普巴的记载、约翰・C・杭廷顿对西藏橛形法器的介绍、乔治沃•麦里第斯对金刚橛象征意义的探讨。桑木旦•G・噶尔梅在其《概述苯教的历史及教义》一文中提到:“最初,金刚橛被视为在印度使用的一种密宗法器,尔后,逐渐进入密集金刚及金刚鬘这样的佛教密宗教义中。在这些密宗教义中,金刚橛仍旧是主要法器。它用木头、铁甚至人骨等各种材料制成。然而,究竟从何时起这种法器变成了神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噶尔梅提出了金刚橛由法器变神的这一问题,但未做进一步分析。
普巴是藏语音译,也称为多杰普巴,意译为金刚橛。《藏汉大辞典》解释为:小桩,橛;金刚橛。(1)金刚橛,古代印度一种兵器名。(2)密宗本尊手中宝帜名。(3)无上续一本尊名。《东噶佛学大辞典》解释:普巴,藏传佛教密宗宁玛派教义所言,即所谓的具德金刚普巴,上身为怒相,下身为普巴形状的一位尊神,其也有普巴黑神、花神等不同类型,但本人未见相关资料。综合分析以上注释发现,普巴在藏语语境中,有工具、武器、法器、神灵等四种含义。在相关藏传佛教典籍中,也从宗教法器和神灵两个方面进行书写,如《密宗服饰与法器濟《佛教密宗法器简论》等,将普巴解释为法器;如《本尊金刚橛历史资料汇编》《郭扎佛教史》等以神灵进行解释,论述其密法经典和传承,从而呈现出普巴在不同语境中表示迥异的概念,并且有时还有将两者合二为一的特殊含义。由上述普巴概念的解释推断,普巴最初为一种工具(生产劳动或武器等),之后成为宗教法器,后来演变为佛教的神灵。由此也引出了噶尔梅所说的由法器变神的问题。就此问题,笔者借鉴人类学家莫斯《礼物》中的“混融”概念,尝试性地做探讨和分析。
二、作为物的普巴
普巴起初作为一种物,或物的形式存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首先通过语义学了解其含义。《藏汉大辞典》解释为:“小桩,橛”,这是其最基本的概念解释。如藏族日常栓系帐篷绳子所用的橛子,栓系牛、马等牲畜时所用的铁橛或本橛等,皆称为普巴,在藏族日常语言中普遍使用。此时的普巴仅仅作为一种农牧民普遍使用的橛子来看待,没有其他特殊的含义。
约翰•C・杭廷顿对普巴的概念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普巴”这个词的直译是“桩”或“针”,“普巴”习惯上指帐篷的桩子。作者引用了罗凯希・昌德拉博士编订的《藏梵词典》中的同义词,具体如下:1., (1)桩或针;极少见词义,一种武器。(2)金刚普巴。2,(1)桩或针;极少见词义,一种武器。(2)栓或针、楔等。(3)文字符咒主(赞颂)。(4)祈祷和礼拜主,神与人之间的调解者。(5)金刚普巴。(6)一种针、钉、大钉、武器。(7)小箭。似乎在专有名词的文字内涵中强调了此器的主要特性,并传达了一种大钉、桩、钉或某种此类东西的概念,隐约有武器的含义。
乔治沃・麦里第斯认为,(金刚橛)这种横切面呈三角形的形式很可能是从竖立帐篷时的木栓演化而来的。他还认为,金刚橛与箭有关联性,并引用了Roerich的一段话:箭在古代西藏是自然崇拜的一种重要的象征,它与对太阳和以闪电形式出现的天火的崇拜有关,后者是它的象征。现时的游牧民族就佩带古代红铜箭作为护身符。
三、作为法器的普巴
古代中国对器物的崇拜,究其原始,一是源于对器物肇始与创造者的崇敬,二是与器物的使用功能诸如祭祀、丧葬、禳解、求吉等有关,三是历史文化在器物传承与演变中的积淀。那么,普巴作为一种日常生产劳动工具,具有锐利、坚硬的功能,从日常生活逐渐进入宗教领域,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也赋予其神圣性和象征意义,由此变成了法器。
普巴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法器,在相关藏文典籍中对其特征有详细的描述,下面根据《密宗服饰与法器》《佛教密宗法器简论》摘译如下:
普巴的材料,分为一般和个别两种。一般的材料为金、银、玻璃、珊瑚、铜、黄铜、生铁、红白檀香、紫檀、柏木、黑刺、小蘖、人骨、手足长骨、猴骨等多种,都可以使用。个别的材料,四业不同的普巴其材料也各异,作息业普巴为银、玻璃、白檀香等白色的材料;增业之普巴为金、黄铜等黄色的材料;怀业之普巴为珊瑚、铜、红檀香、苏木等红色的材料;伏业之普巴为铁、生铁、黑刺、寡妇所用的纺锤轴等邪恶、危险且不吉祥的材料。
普巴的形状,分为一般和个别两种。一般的是顶部为三面或一面且有小顶尖,双臂在胸前绞合,此下为八角杆,之下是纽结,纽结下面是摩羯头,摩羯嘴里有三角刃,刃底粗尖锋,上面缠绕着蛇束等,有与上述相同的不同类型。个别的因四业不同而各异,作息业普巴色白,头、纽结、刃的形状应为圆形;增业普巴色黄,头、纽结、刃的形状应为正方形;怀业普巴色红,头、纽结、刃的形状应为半月形;伏业普巴色黑,头、纽结、刃的形状应为三角形。
普巴的标准,也分为一般和个别两种。一般是头部的纽结或面为一指,中部的纽结为一指,把柄杆子为三指,刃为三指,共八指。上下的纽结分别为二指,把柄杆子为四指,刃为六指,共十二指等,合理制定标准。个别的是,《业续》道:“四指八指十二指,指宽十八均可行。”
普巴的类型,《慈悲忿怒根续》曰:“普巴分四种,法性义之普巴,智慧之普巴橛,有为法物之普巴,所依身体之普巴。”
普巴的功能,根除、驱逐、分散、压制、逃离魔障,作息业、增业、怀业、伏业圆满完成,守护和藏匿自我与被守护者,摧毁敌人,得如金刚之身。
普巴的象征意义,顶部的纽结象征引入三世界,中部的纽结象征六智,八角象征解脱世间苦难、八识无染的忿怒明王和忿怒佛母,化身头像象征十六细法,中心象征畏怖护门四天神和护门四天母,下面的纽结象征大力怒神,咧嘴摩羯象征畏怖曼荼罗,顶部三角象征忿怒五母本性、驱除三毒所致的身、ロ、语习气,摧毁三界世间之束缚,压制三地,得身、ロ、语清净之果位。另还介绍了普巴加持法、实施法、实施过程中的得失等内容。
总之,普巴作为一种法器,主要用于藏传佛教密宗仪式,其材质、标准、类型等如前文所言,都有明确的要求。其功能除上文所言外,麦里第斯总结道:“这种或那种金刚橛是由喇嘛、和尚、巫师、苯教祭司及天神们所使用的,用于对付魔鬼,特别是天界或地下的魔鬼,或者用于抵制或预防疾病或厄运,或向土地献祭。”普巴的象征意义按其各个部位的不同造型而有所不同。罗伯特・比尔道:“金刚橛较低的橛身代表着方法或方便,上把柄代表智慧。三棱棱刃象征着断灭贪、嗔、痴三毒。”……金刚橛的顶部通常有三个怒相神头饰。这些神灵是应召住在金刚橛上的。在绘制它们的化身时,要分别画成白色、蓝色和红色,代表着嗔、痴、贪。右边的白脸通常被视为怖畏金刚(或降三世明王)的脸,代表身和断灭嗔。中央的蓝色脸是甘露王的脸,代表意和断灭痴。左边的红脸是马头金刚的脸,代表语和断灭贪。……九只眼睛象征着宁玛派的九乘和五佛及四佛母的九大智慧。”
四、作为神灵的普巴
金刚橛,藏语称“多杰普巴”,原为古印度的一种兵器,后来成为佛教密宗本尊手持的一种法器,由此又延伸为该本尊神,是宁玛派无上瑜伽部的一位主要本尊,此本尊法即金刚橛法,音译为“普巴法”,是宁玛派八大法行中属于出世间五法之一的“橛事业”。普巴从法器演变成神灵,其形象也成了一个密宗神像和法器的组合体,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实修普巴的密宗经典。
(一)普巴神的形象
金刚橛神,又称金刚童子,属于宁玛派、萨迦派传承的密法之本尊,极受此二派之推崇。金刚橛神形体奇特,有三头六臂,但其下身是密宗法器金刚橛的前半段,呈锐利的三棱形。可知金刚橛神的身形是密宗神像和法器的组合,较为罕见。《藏传佛教神明大全》是如此描述普巴神的:“肤色深蓝,一面四臂,右面白,左面红,正二手分执九股杵、喷火天仗,上二手举金刚橛、金刚缘铃;由法轮加封且手执天仗和顶骨的明妃搂抱。周围有四子、十忿怒神、护门、护橛、十六护法神。住于梵天座。”
普巴神将密宗怒像与橛形的三角刃结合起来,组成上身为神像、下身为其法器的独特形象。因其为密宗神灵,相比其它藏传佛教神灵并不多见。
“在对神性观念的图像学转化中,印度大不满足于仅仅将神描绘成大的样子,而且还要表现他们的神力。……为了将一切视觉化,大们利用大量的法器来象征神力或神本身。在图像学的语境中,当神被表现为大的样子,他们手持的物体表明了自身的象征含义与所拥有的能力。诸神的许多法器,如牧大的牧杖、祭司的祭勺、湿婆的三叉戟,都具有极强的象征义,明确显示了神的个性。”
“公元前千余年,印度在形成一个兼收并蓄、容纳众神的信仰体系之前,原住民与雅利安移民的斗争非常激烈。相应地,诸神的战争有时也被表现得非常血腥。雅利安大的武器比南亚次大陆原住民的武器更加精良。他们的武器具有神性,有时甚至被拟大化地表现为神灵。……诸神手持的一些武器被奉为神的部分化身,在各种庆典和仪式中起着重要作用,大们向其请求保护、消灾免难。”
比对上述印度的案例发现,普巴也是神灵的武器,也被认为是具有神性、拟大化,在各种仪式起着重要作用,大们崇拜并祈求保护等。因此,其由法器演化为神灵的过程,与印度教诸神法器拟大化的过程有内在的一致性和逻辑性。可以断定普巴受到印度文化,包括印度教的极大影响,但普巴是否起源于印度的问题,目前很难确定。
(二)普巴密法的由来及传承
关于普巴的起源问题,学术界观点不一。公元11世纪以来,起源问题始终是佛教徒争论的问题。金刚橛源于印度的可靠性是争论的焦点。根据宁玛派的传说,是莲花生大师把这种崇拜传入西藏的。天喇嘛译师颇章・喜瓦沃在公元1032年颁布的法令中首先反对这一论断。噶尔梅教授引用了法藏敦煌古藏文PT.44号文献,宁玛派学者索朵巴・洛追坚赞(别名南喀觉巴,1552—1624)的著作《吉祥金刚橛史奇异大海波涛》等部分典籍。其实,藏传佛教领域有诸多有关普巴方面的典籍,尤其集中在宁玛派。其中,上述两种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下面依次论述。
法藏敦煌古藏文PT.44号本尊金刚橛的来历及其成因。昔日,(莲花生大师)从尼泊尔境内洋列雪(岩洞),前往天竺那兰陀寺取《本尊金刚橛十万颂续部》经,雇佣尼泊尔搬运夫夏甲玉、乃伊苏二大驮运。(途中)适遇四魔女神于日暮时吞噬一切过往行大(搬运夫二大即被吞噬)。此刻,莲花生大师大显神通,佯作气息奄奄即将丧命的模样,以手一抹,(四魔女神)“吱”地一声叫,当即就擒,(莲花生大师)将其放入帽中,扬长而去。抵达那兰陀寺,从帽中取出,(四魔女)现出美女的身相,当即(向莲花生大师)发誓祈愿成为本尊金刚橛之护法神,接受其祈求封为护法神,呈现吉祥征兆。以金沙一捧作为布施奉献。随之,迎请《本尊金刚橛十万颂续部》经,返回尼泊尔洋列雪(岩洞)。为了完成总摄的事部以上、阿底瑜伽以下的各乘以及一切密续所属的从《金刚橛续部十万颂》至一切乘的要义,(莲花生大师)命令著作金刚橛之各部经典。(照此意旨完成后)即将《十万颂》送返(天竺)。
《吉祥金刚橛史奇异大海波涛》载:(莲花生大师)莅临尼泊尔,在洋列雪岩洞修真理燃灯九法,遇到当地鲁神江布以及鬼神们的打扰。此地3年未下雨,草本庄稼枯萎,河水断流干涸,出现灾荒。此时大师心想,此无他因,是打扰我修菩提。即向佛献供品,祈祷。空中出现声音道:“除此障别无他法,赴印度那兰陀寺迎请普巴续部经典。”于是,派两位尼泊尔大带着一袋黄金前往,将黄金奉献给五百名班智达,并告知事情原委。班智达们从普巴经典十万部中,给了他俩能承载的两部经典。刚到洋列雪地方,鬼神之障自然消解,雷鸣闪电,骤降大雨,草本庄稼生长起来。此刻大师心想,此普巴经吉祥,且法力迅速,应传布各地。创作了续部注疏、观点、修行、成就金刚童子等四部经典。
在莲花生大师传中,有记载说,他曾到过卡拉卡玛拉北部地区,该地盛行金刚橛崇拜。后来,在加德满都峡谷帕尔平阿修罗洞中静修时,他遭遇恶魔制造的种种障碍。为了应付这些难题,他要求从印度带去《金刚橛密法》。这些经文一、到尼泊尔,人们就开始修持,自此之后,一切都戛然停止。在抵达西藏时,莲花生大师向他的二十五位心传弟子传授了《金刚橛密法》。莲花生大师教授这些经文旨在除障,以在西藏弘传佛法。宁玛派最早把金刚橛神作为能够除障的本尊神进行修持,而这种修持也被吸纳到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之中。
以上三种文本所述内容基本相同,印证了普巴密法由莲花生大师在尼泊尔境内洋列雪地区获取的历史事实,因此藏传佛教界一般将普巴密法的起源归于莲花生大师。
普巴的传承根据《郭扎佛教史》记载,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王传承。公元8世纪,由莲花生在桑耶寺传授给藏王赤松德赞、王妃喀钦氏和三位迎请莲花生大师来藏的藏族译师,后在藏区传布。
(2王妃传承。相传公元8世纪末叶,莲花生从吐蕃返回故乡乌杖那国前タ,将普巴法传给王妃喀钦氏措杰和岸者萨列两位女弟子。据说莲花生传此法时应喀钦氏之请,根据藏族妇女修法的特点,将此法作了一定简化,具有言简意赅、修期短、法力大等优点。喀钦氏将此法主要传于其兄喀钦・贝吉旺秋,后在藏区弘法。
(3)坚木传承。公元8世纪由吐蕃贵族妇女觉若氏贝吉却尼玛传出的普巴法。坚木传承与王妃传承并无大的区别。
(4)绒派传承。公元8世纪由后藏那隆容地方的绒宛•云丹仁钦亲闻莲花生传授此法后传出,形成绒派传承。绒派传承也称为“那南传承”。传至后期称之为“恰派”。
(5)若派传承。吐蕃王朝时期由若宛•南喀益希传出。史载该传承一直在若氏家族中进行,从若宛到若・喜饶喇嘛共24代,家族中有过许多修普巴法获得成就者。
(6)拉那传承。吐蕃时期由阿梨哲•萨列从莲花生及其明妃处受学普巴法后传出,传至雍卓巴・古如央达上师,依照《普巴涅槃续》,将本尊身色改为黑色,始称“拉那”,意为黑色本尊。
(7)萨迦派传承。吐蕃王朝时期,莲花生曾传普巴法于后来萨迦派创始人衮却加布的先祖昆・鲁旺布,后一直在昆氏家族中传承,也称“昆派”。萨迦派形成后,该法未尝断绝,通称“萨迦普巴”。
(8)努派传承。吐蕃王朝时期,由坚木传系的觉若氏贝吉却尼玛传给努钦・桑杰益希,再由努钦传出,所以称“努派”,实同坚木传承,至今有其经续传承。
五、分析与讨论
(一)基于人类学的讨论
物是哲学、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其中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人类学家黄应贵梳理人类学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时言道,“在人类学形成早期,物质文化一直是主要的研究课题,但这个课题也牵涉了不同的理论立场:演化论、象征论、结构论。早期演化论便以物质发展的程度来表征社会文化进步的程度。这样的研究立场,正如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定,视人与物有着主体与客体之别。相对之下,莫斯在《礼物》一书及日后有关研究中,为了批评与改正资本主义经济对于人类社会带来的负面问题,由人与物不可分的文化观点,发展出他的社会之象征起源论。不过,在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论中,他认为不论是演化论将人与物分离的二元论或莫斯将人与物联结的象征论,都是在处理现象的表面。事实上,在有关人与物的现象背后,交换オ是关键而为人类学要探讨的对象。因它才是社会的再现与繁衍的机制,是超越人类意识的存在,是属于潜意识的深层结构。1980年代,米勒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奠定了当代物质文化与消费研究的理论基础。阿帕杜莱编的《物的生命史:文化视点下的商品》,不只是使物与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结合,更使物本身成为研究之主体,而使物有了独立的生命及其独特的价值与重要性”。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的《礼物》是人类学领域物研究的扛鼎之作,以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西北美洲等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志资料为基础,对物及物的交换形式与理由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于莫斯《礼物》的相关理论,以期与研究主题做一些比较。
“归根结底便是混融。人们将灵魂融于事物,亦将事物融于灵魂。人们的生活彼此相融,在此期间本来已经被混同的人和物又走出各自的圈子再相互混融……”
“所有的铜器还分别是不同个体的特殊的信仰对象。氏族首领家中每一件主要的铜器都有名字、有其各自的个体性,也有真正的巫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海达和特林基特部落,公主的铜器是她周围的‘堡垒’有些地方,拥有铜器的首领被认为是不可战胜的。铜器还是房屋中的‘神圣的片状物’。神话也常常把给予铜器的神灵、铜器的拥有者和铜器本身等等都认同为一体。”
“这一切都环环相扣、彼此混同;于是事物都有了人格,而这些人格又成了氏族的某种永久性的事物。首领的名号、护符、铜器和神灵都是一回事,具有相同的本质与功能。”
莫斯又讲到:“毫无疑问,事物本身原本也具有人格和品性。并不像査士丁尼法或我们的法律所论断的那些无生气的存在。”
阿兰•迦耶在《礼物》的中译本导言中写道:“在这些社会中不存在人与物、主体与客体的纯然分离。古式社会是一个完全人格化的世界。”
分析莫斯对物的论述发现,其所表达的观点与普巴所呈现的形式几乎如出一辙。普巴从最初的劳动工具逐渐演化为法器,之后在成为神灵的过程中,经历了由橛(物)』法器(物与精神的交融阶段)』神灵(物与精神的融合)的升华历程,物与神灵合二为一,形成密宗神像和法器的组合体,它既是物,也是神,神物混融,也就是人与物、主体与客体不分,法器具有了人格和品性,赋予人格化意义。由此引申出藏族传统社会中人与物截然不分,物具有人性和精神性的文化传统,也正如莫斯所言的“混融”。莫斯的理论有助于我们从人类学理论层面理解藏传佛教普巴是如何从物演变为法器和神灵的过程,以及神物混融的现象,同时也为人类学提供了中国经验和案例。
其实,莫斯的理论为理解普巴提供了一个视角,可作为西方民族志资料的补充,但要深入探究普巴神物混融这一社会事实,还需追根溯源,从普巴产生的文化背景藏传佛教中挖掘其究竟,了解其文化逻辑。
(二)藏族对物的认知
藏族对物的认知需从藏传佛教与藏族民间文化两个方面了解。在藏传佛教哲学领域,尤其是藏传佛教因明学,将物作为研究对象之一。因明学对物的界定和分类是这样的:“所知是指内心可以认识的外境和所知性相。所知、有、存在、所量、所缘法为同义词。所知分为常和物。物的概念是指有具体的性能作用。物分为色、识、不相应行。可现色者谓之色。色与体同义,分为内色和外色。内色分为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外色分为色、声、香、味、触。识,与思、识、智、明同义。分为心与心所、有分别与无分别、七心识、量与非量、悟心与非悟心、错觉与非错觉。不相应行,指的是一种非物质也非意识活动的存在,如时间、年、月、日、生、死、无常和人等。如‘人’并不是可见色体(人体)的名称,而是肉体和思想意识的总合名称,既不是单一的色体,也不是单一的意识,因此属于‘不相应法’。”由此可知,藏传佛教知识系统将物分为三种,即色、识、不相应行,人和神都属于不相应行。按照藏传佛教因明学的逻辑,可得出如下结论:作为物的普巴是物,作为法器的普巴是色与识的结合体,作为神灵的普巴是不相应行,是既非色体,也非意识的神灵。其中作为法器的普巴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将色与识结合在一起。基于藏传佛教哲学理论为基础形成的普巴,巧妙地表达了藏传佛教文化内在的逻辑,为其存在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和文化依据。这种文化逻辑,与人类学家莫斯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藏传佛教哲学将物归入无常之列,认为一切事物是运动变化的,无论物质和精神,都在即生即灭、生灭交替、新陈代谢,无恒常之物。佛教要求人们完全脱离物质的欲念、占有和物质生活风格。在此观念影响之下,藏族人对物质的追求相对较少,认为物是身外之物,是无常的,物欲相对淡薄,而热衷于追求精神生活和来世的幸福。
除了藏传佛教哲学之外,藏族文化中也有对物的表达及其相关的民俗。首先,我们从语文学角度了解一下藏语对物的解释。物,根据《藏汉大辞典》解释,其有几种含义:一、名词:1.物质,物资,货财,器物用具。2.事物。3.事,性,实有法。4.(辞藻学)实有。甲戌年、本狗年的异名。二、形容词:真实,本身,亲自。
藏族民间认为,物存在“央”。“央”意为“福气、福运、吉利”,这个词在藏文化中普遍使用,且意蕴深厚,很难翻译。所谓的“央”按藏族传统观念,认为是依附于物体上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福气或灵气,与其说这个词适用于抽象的概念,不如说更适用于实际的事物。它有象征财富、运道、福气、权势和生命等多重含义,汉语中很难找到一个与此概念相对等的词语,暂可译为“福”或者“福运”,可以和其他的词合起来使用。例如,用在家畜上,就有“达央”(马之福运)、“搂央”(羊之福运)、“闹日央”(牛之福运)等等;泛用于各种生活财产和人生命时,就有“吉央”(财富之福)、“色央”(食物之福)、“オ央”(生命之福)等等。3下面举两个案例,以了解藏文化中的“央”观念。
案例1:藏族民间,如果某人出售牛、羊、马等家畜,在交易过程中,将揪下牛、羊、马身上的一撮毛,放置牛圈里,或系在“央达”(神箭)上,嘴里念诵“留下福祉,带走厄运”之后,オ把牲畜交给对方。
案例2:在藏族传统农区,人们互相送粮食或面粉时,主人将会从一升粮食里抓一把粮食放回粮仓,嘴里念诵“留下福祉,带走厄运”,然后端出去送给对方。
上述案例表明,藏族对物的认知与莫斯所谓的礼物之灵极具共性。藏族认为物具灵气或灵魂,礼物交换或流动时,保留“央”,也就是物之灵カ,招致财富,带走厄运。这一习俗也说明了藏族传统社会中物具有精神,人与物混融的文化传统。
结语
普巴由最初的一种劳动工具,逐渐演变成藏传佛教的一种法器,后来又成为藏传佛教各派及苯教的本尊神,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普巴的密宗典籍。普巴既是工具,又是法器;既是神灵,又是密法,包含着多重含义,其形象也是法器和神灵的组合体,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藏传佛教文化圈内也比较少见。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礼物》中的“混融”概念,对理解此文化现象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典型案例告诉我们,普巴也是“混融”的产物,与莫斯所讲的“混融”概念相似,由此能管窥藏传佛教以及藏文化对物的认知与实践。这一个案也为人类学提供了中国经验和案例,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
本文为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资助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中国西藏与南亚文化交流史研究”(31920210149)、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藏文南亚文献整理与研究”、"青藏高原区域历史文化研究创新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看本加,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刊于《宗教学研究》 2022年第2期 (责编:心愚) 注释及引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