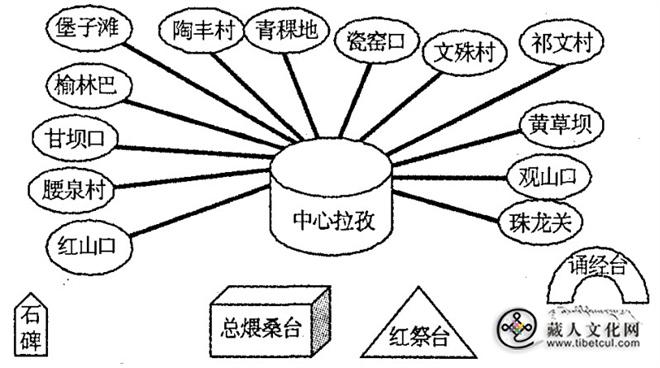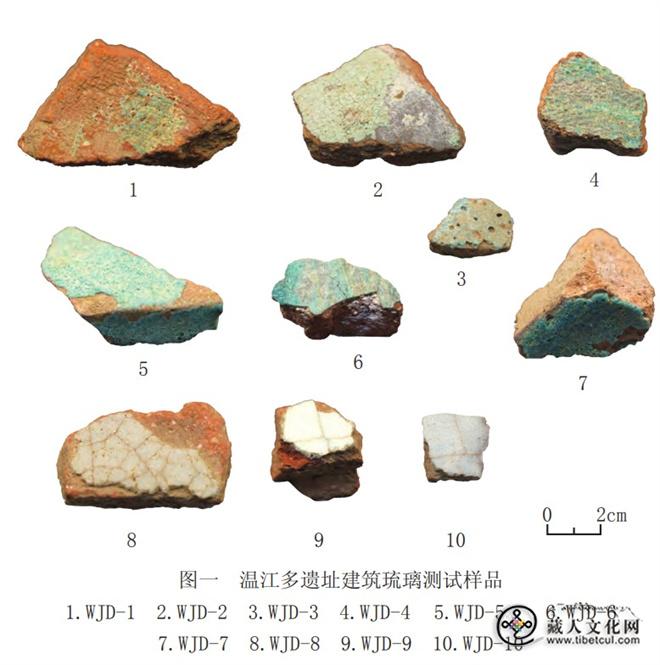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藏族的创世神话是藏族神话中的一种,其内容较为广泛,大到宇宙的形成,日月星辰的创造,人类的起源,小到草木昆虫缘何而生,都作了自己独特的阐述。她不仅在藏族神话中,而且在藏族古典文学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藏族的创世神话主要有《什巴卓浦》、《什巴问答歌》、《什巴塔义》、《猕猴变人》、《大鹏与乌龟》、《大地和人类》、《马和野马》、《七兄弟星》等。这些口碑流传和书面记载的创世神话,充满浓郁的高原风情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她与其他民族的神话一样,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藏族先民对大自然的探求和认识。而且,与宗教一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都在客观物质世界中找到它们反映内容的最终根源。就藏族创世神话与原始宗教而言,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具有相同的一面,而且在起源上也几乎是同时的,正因为创世神话和原始宗教有着这样一些共性,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
藏族创世神话,大多与自然崇拜、图腾崇拜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随着氏族和语言的出现,人类具有思维能力,客观世界的种种变化,便映入藏族先民的脑海,他们试图解释并加以控制,由此,一个个被想象的神,伴随着对宇宙万物的解释而诞生了。他们想象,宇宙尚未形成时,天地混沌一团,是大鹏和乌龟把天地分开。藏族先民用一种原始的思维方式,通过幻想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来构想它的形象及其活动,从而产生对自然或某种动物的崇拜和模仿,也即萌芽状态的原始宗教。虽然这些原始宗教活动都有各自特定的方式和内容,但是它们又具有共同的神秘仪式和礼仪形式,是以幻想和情感体验来表现、模仿或塑造各自所需的形象的。正是这些共同的特点,构成了藏族创世神话产生的动因。
丰富的想象力和感性思维,使原始社会生活在藏族创世神话中形象化了。例如在《什巴问答歌》中写道:
什巴宰杀小牛时,砍下牛头放山上,所以山峰高耸耸。什巴宰杀小牛时,割下尾巴放路下,所以道路弯曲曲。什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铺大地,所以大地平坦坦。
在神话时代,自然与社会以及人自身,对藏族先民来说,主要是感知与体验的对象,不可能是理性把握的对象。因此,他们将高耸的山峰、弯曲的道路、平坦的大地与自己生活中所熟悉的牦牛的形象联系起来,作出巧妙的解释,这无疑是一个较大的进步。它说明了藏族祖先丰富的形象思维能力。藏族创世神话之所以能获得长久的魅力,也正是由于它们这种类比联想对自然和社会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
关于藏族远古时期的象雄六大氏族之一“琼”的肇始,藏文史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报身化身慧明王,化作三鹏空中游,
栖落象雄花园内,象雄人们大惊喜,
从未见过此飞禽,老人称其有角鹏。
三鹏飞返天空时,爪地相触暖流闽,
黑白黄花四蛋生,每孵幼童叫琼布。”[1]
对世代生活在“天然动物园”中的藏族来说,他们从远古就和各种动物结下了天缘。藏族先民关于卵生世界的这一信仰,也正是源于他们对鸟类和其他卵生动物的一种直观联想。因为,许多动物的生命都从蛋中肇始的,从而,他们以为蛋既能生人、也能生天地,并把自己祖先的形成也与传说中最大的鸟——大鹏联系起来,加以崇拜。动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和意义。正如费尔巴哈所说:“动物是人不可缺少的、必要的东西,……而人的生命和存在所依靠的东西,对于人来说就是神。”藏族先民以神秘的色彩渲染动物,把它们供奉到最高的神座上,并以自己的亲族祖源关系相待,以予神圣化。因此,藏族创世神话作为藏族早期生活中一种隐秘的、特殊的理性活动形式,折射着不发达阶段的社会实践内容。它既表现着神的世界,又充满着世俗生活的内容。它对万物起源的追寻,虽然是一种主观的联想和神秘的猜测,但是,它也是藏族先民探索宇宙发展的一次尝试。
在《大鹏与乌龟》中,藏族先民认为大鹏从上白、下黑、中红三种颜色的蛋中孵出,是拉、年、鲁三神合为一体的化身。而这三种神灵都是藏族的原始神灵,分别居住在天上、地上和地下。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主宰着人类以及自然界的一切。天上为神界,是“拉”高居的地方,“拉”可以佑助人类,给人类带来幸福。“地”为人界,是“年”神生活的地方。“年”是一种祇神,相传倘若触犯它,人畜便会遭受灾难;如果虔诚地供祭它,福泽便会降临。“地下”是“鲁”神栖息的地方。“鲁”是一种水神,一般生活在水中。祭奉它会给你幸福,反之则招来疾病和灾害。这些神灵对人类或善或恶,取决于人类对它们敬仰、崇拜与否。所谓“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2]。于是,藏族先民虔诚地跪拜在具有巨大威力的各种神灵的脚下,祈祷和崇拜它们。同样,正是在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的意识形态里,诞生了各种解释性的创世神话。“大鹏”也是在这种万物有灵的观念中孕育的一种图腾崇拜物。也就是说,原始宗教的幻想,激发了藏族创世神话的诞生。
二
藏族创世神话作为藏族先民的文化精神遗产,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是各种意识的综合体。其中,宗教意识的影响占有相当的地位。
在苯教的经典中,记载着这样一则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
在很早以前,有位名叫南喀东丹却松的国王,拥有“五种本原物质”,法师赤杰曲巴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入他的体内,轻轻地“哈”一声,吹起了风,当风以光轮的形式旋转起来的时候,就出现了火。火越吹越旺,火的热气和带有凉意的风产生了露珠(水)。在露珠上出现了微粒,这些微粒反过来又被风吹落,堆积起来形成了山。法师又从五种本原物质中产生出一个发亮的牦牛状的卵和一个黑色的呈锥形的卵。然后,用一个光轮来敲发亮的卵,产生了火光。雨和雾又从五种本原物质中产生出来形成了海。于是,天地形成,世界就这样被创造出来。”[3]
这是一则纳入宗教典籍中反映向宗教过渡的创世神话。在远古时代,藏族曾以神话治国。神话的说唱形式,是苯教的重要仪轨之一。苯教将神话纳入其经典或仪礼中,用它来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这则创世神话反映的是宇宙的本原观,认为万物起源于“五种本原物质”,体现了藏族先民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值得称道。然而,同时,它又表现了神的超人力量。创造“五种本原物质”的是苯教的报身(受用身)的化身,万能的法师即神。因此,创世神话既是艺术的表现形式,又是宗教意识的具体体现,具有双重特征。
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吐蕃时,受到了土著宗教的顽强抵抗。佛教为了在吐蕃站稳脚跟,迎合藏族的传统信仰,把苯教的神灵以及神话中的神灵都纳入自己的神灵体系中,作为佛教的护法神,进行佛教化的解释,创世神话从此也被佛教所渲染。如关于藏族族源的著名神话《猕猴岩魔女》中说:
“圣观世音菩萨,对一神变示现的猕猴,授给近事戒律,派遣到西藏雪域的地方修行。当他修习菩提慈悲之心、对于甚深之佛法性空生起胜解的时候,有一个被业力所驱使的岩妖魔女来到那里,穿上妇人的服装,苦求与他媾和成婚。在观世音菩萨的祝福、愤怒母和救度母的称善中,他们配成夫妻,并生下由六道轮回中的生灵投胎的六个猴崽。对边地雪国具有三种功德:未来之时能使佛教常弘常存,善知识不断出世,宝藏开发,利乐善业遍及十方,吉祥如意。”[4]
在这则神话中,不仅加进了圣观世音点化,而且以人和动物的形象为蓝本,创造了猕猴神的形象。既直接描绘猕猴和岩魔女,也通过圣观世音、愤怒母和救度母以及近事戒律、性空、六道轮回等佛教教义间接虚构出另一个境界,使神话不仅表现社会现实,而且表现幻想的彼岸世界,既有现实的人或动物,又有虚幻的神,色彩奇幻。
随着佛教的深入发展,藏族的创世神话发生了更大的变异。藏族的原始神灵与佛教的神灵相互影响,互相杂糅,又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创世神话。如在《大鹏与乌龟》中,关于乌龟的形成是这样描写的:
“这只金色的乌龟,父母三世为生处,
是一切佛的化身。在上与天神同处,
在中与年神同处,在下与鲁神同处。
居在海心之玉宫,乌龟栖身在中央。
周围四方有四门,各门有一护持神。
东有护持国之神,南有护持地之神。
西有广目之地神,北有多闻之神守。”
上述神话中,把藏族原始神灵“天”、“年”、“鲁”神与佛教中的天王混合在一起,对自然力进行神化,并借助于神的观念,对乌龟进行解释,也是藏族先民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感情,置于神的世界中,调动自己非凡的想象力组合而成的艺术形象。因此,这个乌龟并非凡龟,而是藏族先民所崇拜的、非凡的、神秘莫测的图腾神。尽管它是一个以表现宗教教义为宗旨的艺术产物,但是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美,意在激发人们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乌龟的生处“三世”,即“过去”、“现在”、“未来”,是佛教中因果轮回个体一生的存在时间。东西南北的护持神,也是佛教中镇守四方、摧邪辅正、护法安僧的神将。显然,神话中的神,同时又是宗教中的神,只不过是用艺术的想象力将宗教和创世神话联结起来,扩大了创世神话的接受层次,并通过它来表现虚构的神灵世界和神灵的生活方式。
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的分野。人世间于是有了君王、部落首领之类的等级划分。这种等级观念很自然地被摄入到宗教、神话与其他意识形态中。譬如,藏族创世神话《大鹏与乌龟》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问:“倘若祖父来到天,居天父亲是哪个?
倘若祖母来到地,住地母亲是哪个?
倘若儿子来中间,中间儿子是哪个?”
答:“要叙居天之父亲,父亲是天上的释帝。
母亲是大地的众生,儿子是陆上的乌龟。”
神话作为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精神意识,是受历史制约的社会现象。法国社会学学者杜尔克姆(Durkheim)认为:“不是自然,而是社会才是神话的原型。神话的所有基本主旨都是人的社会生活的投影。靠着这种投影,自然成了社会化世界的映象:自然反映了社会的全部基本特征,反映了社会的组织和结构,区域的划分和再划分。”[5]因而,藏族创世神话中的这种天父神王、地母众生的观念,也是社会生活中人类行为的一种折射。随着君权专制的出现,社会结构、人与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人与神的关系便自然地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天地有了相对应的地位,也就出现了天父地母、天父神王、大地众生等等级的系列划分。原始苯教有了三界天,佛教有了三十三天、三界九地、六道轮回等层次分明的大千世界。古老的藏族祖祖辈辈默然听认着这样的解释,并接受了这个存在。创世神话中的“天父帝释”是佛教中三十三天之王,居须弥山顶之善见城,是佛教的最高神;“乌龟”是“天子”、“君主”即神的儿子,是神在人间的化身;“地母”即“众生”,是万物之灵,要服从神的旨意、神的安排。故此,左右人们的依然是“神”、“天子”、“君主”,而受苦受难的依然是贫民百姓。但是,他们在虚幻天国的种种说教中,得到了精神上的慰藉,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后,就会安于物质上的贫困和现实生活的痛苦,把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于“天国”、“来世”,从而顺应“天命”,成为宗教的奴役。于是创世神话也不可避免地依附于宗教。
四
藏族的创世神话,是藏族原始社会集体幻想的产物,也是藏族先民原始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从现象上看,它始终与宗教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密不可分。首先,由于创世神话与宗教都试图以主观想象解释世界,反映了先民的理想和希望。其次,因为宗教要利用神话得以发展,神话也往往依附宗教得以保存、弘扬。再者,富有宗教意识的古老藏族,总是把幻想中的各种神灵、图腾、天国、来世等宗教感知和体验,渗透到神话与其它社会意识当中,按照自己的需求和愿望或审美规律来造型。这样,在形式上就表现为藏族创世神话与宗教的联结。
二者关系尽管密切,但仍存在本质差别。创世神话虽然是一种心灵创作,可它依赖于外在的世界,是心灵对客观自然世界与人类自身的一种观照;宗教虽然也是一种世界观,但它是一种绝对的心性依赖。它的一切功利,只能在空幻而神秘的想象中实现,终究不能与世俗生活要求的真实性协调起来。所以,藏族创世神话,作为宗教的生命力几乎消亡,而作为艺术的生命力却永世不朽,并以自身特有的神奇的想象力增加了奇幻多姿的魅力,获得了其他艺术所不曾有的审美情趣,从而显示出其真正的审美价值。
注释:
[1]《本教源流》,白崔著,西藏人民出版社,页375。
[2]《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3]噶尔美《苯教历史及教义概论》,《藏族研究译文集》,中央民院藏学所编,页59-60。
[4]《西藏王统记》,萨迦·索南坚赞著,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页49-51。
[5]《人论》(德)思斯特·卡西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页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