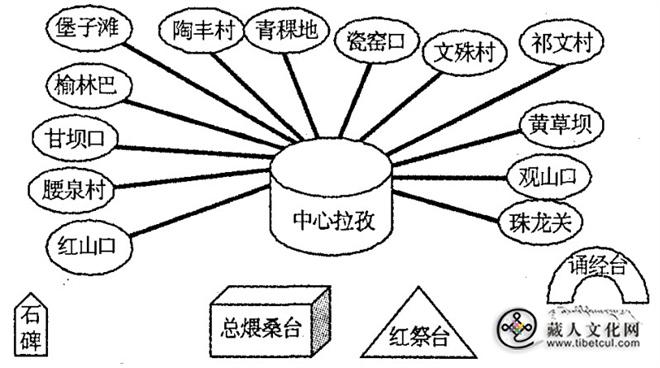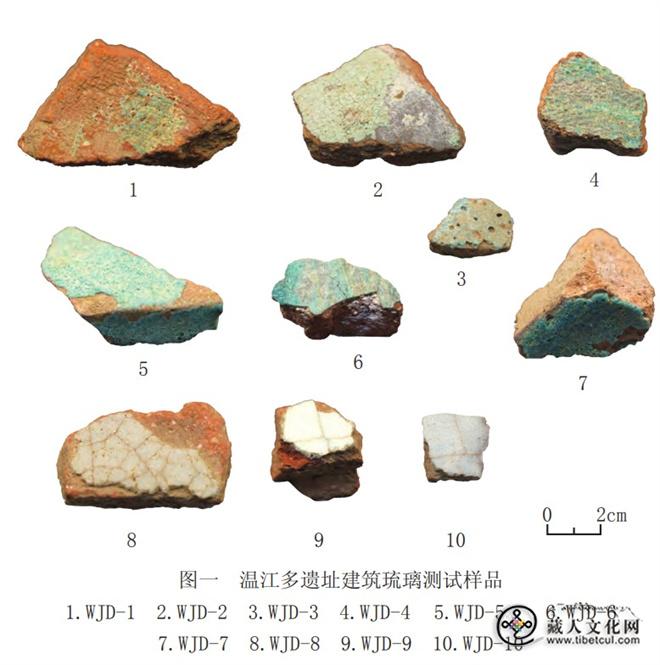摄影:觉果
摄影:觉果
内容提要:万玛オ旦小说的突出特征之一在于奇幻叙事。他以独有的方式将转世轮回、生死界限的打破等奇幻元素融入到对藏地日常生活的书写中。探索小说中奇幻叙事的来源、藏地奇幻叙事的特征以及小说如何通过奇幻抵达当下的现实等问题,为理解万玛オ旦的作品提供了新路径。奇幻的背后是作者对前现代文化的回望,展现了非理性之下对现实的触碰。
关键词:万玛オ旦 小说 奇幻叙事 藏地书写 现代性
万玛オ旦的艺术成就主要分为电影与小说创作。电影创作中,万玛オ旦的作品有《寻找智美更登》《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塔洛》《五彩神箭》《气球》《撞死了一只羊》等,其电影多次获得国内外高水平电影奖项。同时,1991年以来他完成了多部小说,其中藏文小说集有《城市生活》《诱惑》,汉文小说集有《嘛呢石,静静地敲》《流浪歌手的梦》《塔洛》《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等,还有翻译作品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与《人生歌谣》。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万玛オ旦就开始了小说创作。文学与电影是万玛オ旦选择的两种不同但具有关联的表达方式。关注他的文学创作对完善其整体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藏族作家群的写作各有特色,如扎西达娃深受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在小说中融合了传说与神话,其书写呈现出不同的样貌;阿来的小说中既有宏大的历史书写又有藏区独特的民族文化,在藏族作家群中独树一帜。万玛オ旦的小说受雪域高原的神秘性与佛教文化的浸染,往往将藏地作为奇幻发生的重要地理背景。他的小说中虽没有强烈夸张的魔幻成分和宏大的历史书写,但作者以独有的方式将奇幻元素与藏地文化融入到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中。他将奇幻作为重要元素参与小说情节的发展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并进一步关联到小说深层思想的表达。
一、万玛オ旦小说奇幻叙事的来源
文学作品中存在大量奇幻叙事。如人们熟知的《一千零一夜》中的飞毯、飞马、阿拉丁的神灯和戒指构成了奇幻叙事的重要推动カ,19世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仙境》讲述主人公掉入兔子洞开启奇幻漫游的故事。根据法国当代结构主义文论家茨维坦•托多罗夫对奇幻的定义,奇幻通常是指神秘、无法解释、怪异的现象出现在日常生活中,是自然与超自然的融合。中国当代文学中,扎西达娃、莫言等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作家创作通常有一定的奇幻色彩。读万玛オ旦的小说,也很容易关注到他小说中出现的大量奇幻叙事,如《诱惑》中嘉洋丹增被黄绫紧裹的经书谜一般地吸引,《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死后还在嘛呢石上刻字的刻石老人,《气球》中过世的爷爷奶奶会转世回到自己家中等。奇幻叙事作为万玛オ旦小说中独特的部分,融合在他对藏地日常生活的书写中,此种奇幻书写有其独特的来源。
其一,来源于藏族神话与民间故事。万玛オ旦曾翻译出版了藏地故事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在藏语中的原意是《如意宝尸所讲述的神通故事》,也有人简单地翻译为《尸语故事》。这是一本类似于西方《一千零一夜》的框架式结构的故事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从内容看都是训诫与魔法故事,具有很强的想象性,原本来自印度,“是在原民间故事基础上,经过佛教意义的加工后集结而成的……但在流传过程中,特别是那些脍炙人口、ロ头流传的故事,却受到了藏族民间化的修饰加工。也就是说,《说不完的故事》在藏地的流传,是在藏传佛教和藏族民间文化两个体系的选择和改写之下”。这有助于读者了解《西藏:说不完的故事》的佛教与民间渊源,这一故事集对万玛オ旦小说奇幻叙事的影响较深。
从具体的小说来看,《尸说新语:枪》属于万玛オ旦小说中典型的奇幻叙事类型,讲述的是德觉桑布带如意宝尸回去的故事。故事中的德觉桑布原名叫顿珠,他的哥哥赛协跟着术士七兄弟学法术不成,反倒让聪明细心的顿珠掌握了全部秘诀。顿珠偷学法术的事被术士七兄弟发现后,他分别变成白马、鱼、鸽子以逃脱术士七兄弟的追捕,逃到潜心修炼的龙树大师处求救,后变成大公鸡咬死化作蜈蚣的术士七兄弟。因伤了七条人命,顿珠被龙树大师取名德觉桑布,他要找到如意宝尸并将其带回才能补过。如意宝尸专讲引人入胜的故事来迷惑德觉桑布,德觉桑布一旦着迷于故事开口说话,宝尸就会飞回寒林坟地。德觉桑布的故事本身带有奇幻色彩,其中包含了“法术”“变形”等重要而显在的奇幻元素。如意宝尸讲述的故事中包含了香獐子这一子故事。勒安沉迷赌博,对病重的母亲尼玛拉姆不管不顾。智者说,要等他额头上长出黑痣オ会醒悟过来孝顺母亲。当黑痣长成后,智者的话果然成真。此前父亲明美因射杀香獐子而死,儿子勒安为尽孝找药引,再次主动开枪射杀香獐子。故事中智者的话语带有极强的预言性,这种预言性可被视作带有超自然性的奇幻。从《尸说新语:枪》来看,万玛オ旦部分作品中不论是故事本身还是其中嵌套的子故事,叙事上都带有奇幻色彩。
《西藏:说不完的故事》这一藏地故事集中也讲述了魔法师七兄弟和赛协、顿珠的故事。弟弟顿珠偷学了魔法师七兄弟的法术,七兄弟牵走由顿珠所变的白马。顿珠为了逃脱七兄弟的追捕,变成金鱼、白鸽和龙树大师念珠上的珠子,最后变成大公鸡咬死了变成蜈蚣的七兄弟。顿珠需要取回如意宝尸来消除杀人的罪孽。顿珠取法名德觉桑布。为了不被德觉桑布带走,如意宝尸开始讲述故事,故事内容包含诸多奇幻元素,“变形”是其中重要的一个。除了主故事中顿珠偷学法术后的变形,子故事中也有类似的青蛙和公主的故事,讲的是娶到公主的青蛙的真实身份是龙王儿子,披上蛙皮变身青蛙是为了和妖魔决斗。如意宝尸讲述了另一则关于牧羊少年的故事:牧羊少年听到鹦鹉和小猫对话,说主人家孩子的头痛病是因为蜘蛛钻到了耳朵里,“治疗的办法是在一个蓝围帐里生上火,洒些水,让病人坐在里面擂鼓,蜘蛛以为是夏天的雷声,就会带着小蜘蛛出来,那时趁机捉住它们,这样不用治疗也会自动好起来的”。这则故事中,叙事的奇幻之处在于动物有了人的意识并能与人进行交谈。万玛オ旦在写作中化用了类似的赋予动物以人的意识的情节,实现了人与动物的交流。小说《八只羊》中,牧羊少年甲洛的妈妈曾给他讲过虫子会钻进耳朵里吃脑髓的故事。某天,牧羊少年的耳朵疼痛难忍,半夜听见家里的牧羊狗和猫正在聊天,谈到治疗的方法:"只要在屋里洒一些水,生一盆火,在耳朵边上敲鼓,那些虫子以为是春天的雷声就会钻出来,把它们一个一个掐死就没事了。”按照动物说的做,甲洛果然治好了耳朵。不论是动物间的交谈还是敲打治疗的民间方法,《ハ只羊》的叙事明显化用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中的民间故事资源。
小说《气球》中,江洋带回来的连环画上画着藏族经典的民间故事《和睦四兄弟》。江洋安排爷爷、两个弟弟和自己分别扮演大象、猴子、兔子和鹦鹉四种动物,爷爷在其中演了最小的兄弟大象。小说最后卓嘎意外怀孕,得知去世的爷爷会投胎成最小的孩子降生。这一情节暗示了“将来如果母亲卓嘎能够把孩子生下来的话,和睦四兄弟的故事就圆满了,否则就是缺失的”。从中可以看到万玛オ旦将藏族民间故事《和睦四兄弟》化用到小说中,以轮回转世构成了奇幻叙事的一部分。《陌生人》中,陌生人来到有二十一个卓玛的故乡,故事最后小卓玛出生,刚好凑够二十一个卓玛。二十一个卓玛对应了二十一度母赞,奇幻的发生与藏地的佛教风俗相关联。从具体作品中可见,万玛オ旦小说中的奇幻叙事来源于藏族神话与民间故事。他曾在访谈中透露此种影响缘何而来:小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是动画片《三打白骨精》《大闹天宫》等影片,里面的一些神话元素和我曾经接触过的藏族本身的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比较接近”。
其二,小说中的奇幻叙事来源于西方现代作家的影响。万玛オ旦阅读广泛,大学学的是藏语言文学专业,他坦言自己接触外国文学的轨迹由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始,之后通过中国作家了解了现代主义文学,然后才深入了解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后,也启发了万玛オ旦。
万玛オ旦曾透露受到过许多外国作家的影响:“也有那么几个人,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自己所受的影响。像马尔克斯、卡夫卡、福克纳、契诃夫、莫泊桑、卡佛……我更喜欢读一些短篇小说,受短篇小说作家的影响比较大吧。”对寸万玛オ旦短篇小说创作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西方现代作家。西方现代文学中不乏对魔幻与奇幻元素运用到极致的作品,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包含床单升天、家族人物轮回转世等奇幻情节,卡夫卡的《变形记》以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开启了一场现代性的奇幻之旅。坦言自己深受现代文学影响的万玛オ旦,在小说创作中同样留下了奇幻的痕迹。自西北民族大学毕业后,万玛オ旦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他被评价“是带着东西进来的。这里的东西,指丰富的社会历练、特殊的藏地经验、具备自我观点,也包括他的作家身份”。藏地的民间故事、万玛オ旦本人独特的藏地成长经历与丰富的现代文学阅读经验一同成就了他的小说,构成其创作中奇幻叙事的重要来源。
二、万玛オ旦藏地奇幻叙事的特征
万玛オ旦的藏地叙事在藏族作家群中具有独特性。他依托藏地这一文化背景,运用多种叙事手法,使读者产生犹疑以达到奇幻书写的效果。同时他将转世轮回、生死界限的打破等非常规现象融入到小说的日常书写中,构成了作品中的奇幻叙事特征。这使他的藏地书写具有基于日常却超越日常的超验性。
首先从人称与叙述者来看,万玛オ旦多篇奇幻文本中的叙述者是“我”,“我”既是人物又是叙述者。第一人称最大的作用是混淆读者的判断,使之陷入犹疑。茨维坦•托多罗夫指出:“奇幻就是一个只了解自然法则的人在面对明显的超自然事件时所经历的犹疑。”万玛オ旦小说通过第一人称叙事使读者产生犹疑来达到奇幻效果。《乌金的牙齿》即以第一人称叙事。“我”与活佛曾经是小学同学,这让拥有活佛这一特殊身份、与常人秉性相异的乌金参与到世俗世界中。在藏地活佛意味着什么?村里人不如意就会去求活佛乌金保佑,有了他的加持,很多人变得顺利了。乌金成为活佛后,“我”回忆起过去乌金救鱼的故事,那条像是死了的鱼被乌金坚持放回水里之后又活了。《乌金的故事》中关于乌金的一切始终存在疑虑,大多只是“我”的不可靠回忆,加上叙述者“我”一直对乌金活佛身份的怀疑,因此关于活佛乌金的一切都蒙上了奇幻色彩。
《水果硬糖》也是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小说。主人公“我”有两个年龄相差十八岁的儿子。第二个孩子多杰太刚生下时懵懵懂懂的,开口说话晚,看上去像个傻子。主大公“我”在年轻时遇到过卓洛仓活佛,当时卓洛仓活佛给过“我”一把水果硬糖。被误认为是傻子的小儿子多杰太后来被僧侣们认证为卓洛仓活佛的转世,为了使这一说法更可靠,小说中写被认证为活佛的多杰大的微笑“就是许多年前卓洛仓活佛盯着我看时脸上的笑容”。《水果硬糖》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使读者在将信将疑中完成阅读,达成了产生奇幻的效果。小说《乌金的牙齿》和《水果硬糖》中的活佛作为一种比普通大更有力量的存在,也是奇幻文学中常见的要素。
万玛オ旦的藏地奇幻书写中还出现了“酒鬼”等不可靠叙述者。不可靠叙述者指的是叙述者在讲述和评判事实时出现偏差,所报告的内容不准确,因而使读者在作出判断时缺乏相应的依据。“酒鬼”因处于非理性状态,其评判的内容缺乏可靠性,因此被视为不可靠叙述者。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刻画了死后在嘛呢石上刻字的刻石老人。酒鬼洛桑的阿妈托梦让刻石老人为她刻一块六字真言的嘛呢石,死去的老人只有在刻完嘛呢石后才能自然往生。为此酒鬼洛桑在铁匠处买了锋利的凿子供过世的刻石老人使用,人们拿吃的喝的来供养刻石老人,现实的事物在小说中能被死去的人使用和享用。酒鬼洛桑与刻石老人交流想法的方式是托梦,生与死的界限以梦的方式被打破。老人吃多喝多就动不了,死去的人依然如活着的人一般有人的秉性和生活习惯。故事设定为只有佛缘很深的人才能第一个听到敲嘛呢石的声音,这个人的身份恰好是酒鬼。托多罗夫指出:“人物的语言令人生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想象这些人物都是疯子;但尽管如此,由于叙述者没有直接说他们是疯子,我们就会对他们半信半疑。”酒鬼洛桑的话令故事中的人物和故事外的读者半信半疑,这种使人生疑的感觉符合奇幻产生的条件。万玛オ旦曾对此作出解释:“因为人物是个酒鬼,他说的话就不被人们所相信,他所描述的事情在别人看来是荒诞的、不可理喻的,这也为叙事的展开提供了契机、动カ与空间。”小说中酒鬼这一打破理性法则的身份,对构建突破生死界限的世界具有关键作用,推动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不可靠的叙事效果,这使故事中的人物与读者产生犹疑。万玛オ旦小说中的不可靠叙述者还有《死亡的颜色》中会预言转世的上师、《牧羊少年之死》中知道前世身份的牧羊少年等,人物身上的非理性色彩作用之一是使读者在犹疑中被推动着前进。
其次从小说对非常规现象的叙事来看,万玛オ旦关注到以欲望为中心的非常规现象,并将其化作小说中的奇幻元素。依据托多罗夫对奇幻的定义,社会中的非常规现象虽然不属于超自然,但作为欲望的变体也属于奇幻文学。《诱惑》中嘉洋丹增被黄绫紧裹的经书吸引,看到经书就会忘却一切,变得无比痴迷。“嘉洋丹增的视线立即被那卷经书上散发出来的金灿灿的光紧紧地吸引住了……刹那间,他觉得那光束直直地射向了自己,使他眩晕,使他难以站稳。”嘉洋丹增的真实身份是佛爷,他出生那天干梨树在冬季开了花,东方的天空出现了祥光,停留了几分钟。《诱惑》中还有对人死后世界的书写。嘉洋丹增死后被老头子和他的女儿仁增旺姆带走,后又被送回现实世界,被人们称为“活佛还生”。老头子变成了现实中矮小的老喇嘛,仁增旺姆也没有死。嘉洋丹增在得到经书前再次去世,一个小喇嘛“看见嘉洋丹增活佛捧着那卷用黄绫紧裹着的经书,随着一道祥光缓缓地飘摇而去了”。小说中与嘉洋丹增相关的叙事通常带有奇幻色彩。小说书写嘉洋丹增谜一般地渴望经书,实际映射的是人的欲望。当欲望被不断放大,就会显现为非常规现象,产生奇幻性。小说《第九个男人》中也存在欲望的变体。主人公雍措是村里的美人,一共和九个男人好过。雍措将自己和其他八个男人的故事毫无隐瞒地讲给第九个男人听,小说通过描述第九个男人听故事后的反应,构成隐含的多角恋关系,小说中非常规的性欲作为欲望的变体出现,构成了万玛オ旦的奇幻叙事。
最后从转世轮回、生死界限的打破等与佛教相关的奇幻元素来看,万玛オ旦小说中存在大量与转世母题相关的奇幻叙事。《牧羊少年之死》中,牧羊少年清楚知道自己前世的身份是屠夫,老母羊是去世奶奶的转世,因奶奶前世骂了修行者,今世オ变成了畜生。他记得自己与牧羊少女前世是一对自由飞翔的小鸟,后来转世为一对猛虎。此后牧羊少年投胎成人,因家道中落流落街头成为杀生的屠夫,为了赎罪替所杀的一千五百个生灵点了一千五百盏酥油灯。转世是推动小说发展的主要线索,它还出现在万玛オ旦其他的作品中。《气球》中过世的爷爷奶奶会转世回自己家中;《死亡的颜色》中上师算出尼玛的弟弟达娃会在四十九天内转世回到自己家里;《特邀演员》中老人的第一任妻子得病后,世间的医生都治不好她。只有子女出家当僧人才能慢慢消除孽障,即让子女代替父母清除前世的孽障。“转世轮回的反复讨论,在万玛オ旦多篇小说中不时出现,它联结了父子爷孙。”转世轮回作为与佛教紧密相关的元素,联结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不仅是沟通死者与生者的方式,还是将不同时空融合打通的超验形式。
生死界限的模糊营造了一种混沌的时空感。徐晓东曾指出万玛オ旦小说中的时间有很强的主观性:“比如《诱惑》中,他明明睡了七天,却感觉自己刚刚睡着,而有的时候,又是比较客观的时间,比如他只剩下五年时间,五年一到,他就真的死去了。而有的时候,时间又是错乱的,比如将白天当成了晚上。”再如《尸说新语・枪》中的时间与原本民间故事中的时间不同,原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万玛オ旦的小说则“发生在’遥远的将来’,像一个科幻片一样”。于空间也是一样,“生与死这两个空间被打通,梦境与现实、客观与想象也被打通”③。托多罗夫指出,奇幻文本中“超自然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不再是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奇幻让时间和空间具有某种新的延展性与可能性。
万玛オ旦认为藏区的人读他的故事会相信它的真实性,“不会觉得它是虚构的。生者与死者之间可以沟通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托梦’”。万玛オ旦奇幻书写的特征在于,藏区的人们深信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与藏区的文化背景相关。他们“相信那些略带魔幻的现实就是真实的现实;别人看来是魔幻的,他看来是真实的”愚。对藏地的人们而言,奇幻的存在有现实依据,正如藏族史书本身就带有奇幻因素。奇幻只是意味着无法用理性世界的法则进行解释,但这些事件被藏区的人们视作现实的组成部分。
无法用理性世界的法则进行解释的非常规现象,被现代理性归于奇幻。为了呈现这种奇幻,万玛オ旦的藏地叙事采用第一人称叙事及“酒鬼”等不可靠叙述者使读者产生犹疑。小说关注到社会中的非常规现象如欲望的变体、转世轮回、生死界限的打破等,将其作为叙事的重要推动カ。此外,小说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中通过奇幻营造出混沌的时空感,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万玛オ旦的藏地书写。
三、万玛オ旦奇幻叙事下的现实表达
万玛オ旦的小说以藏地为文化背景,依托多种奇幻元素,创造了不太合乎理性的世界和不遵从理性行事的人。对奇幻元素的关注源于万玛オ旦对世界的认知,他认为“'混沌'是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也是对这个世界的准确呈现。世界对我们在场,它的面貌不可能完全清晰……对于一些未知的东西,或者信仰层面的东西,都是混沌的”。这是万玛オ旦选择奇幻叙事进行藏地书写的原因。因藏语文学往往能通过简单的故事形式传达深刻而丰富的教义,受藏语文学叙事传统的影响,万玛オ旦没有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而是在奇幻或超自然的故事中传递他的思想。混沌可以作为万玛オ旦对世界形态的认知之一,现实主义的方式无法呈现混沌的真实状态。正如酒作为重要元素参与着万玛オ旦的小说世界,只有奇幻元素才能使原本的秩序松动,展现更为真实而丰富的藏地现实。
当代藏族作家借用传统民间神话、传说进行创作的例子不在少数,作家出于不同的审美趣味和创作旨趣,对文化资源的利用方式也不同。万玛オ旦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民间传说与神话中的情节在现代性视野中拥有了新的涵义,作家“在现代性视野里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重新审视这些故事及其内涵,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赋予它们新的内涵”。民间传说与神话资源作为奇幻元素被运用在小说中,作者试图借助此种方式提供看待现代社会的不同路径。奇幻书写的作用之一就是还原对世界的整体认知,万玛オ旦说:"我对这个世界的整体认识,可能就是一种荒诞和无常的感觉。”这种认识与西方的现代主义对接,使得他对藏地日常的书写具有西方现代主义的色彩。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转向对人内在精神的关注,万玛オ旦的小说即是在对藏民日常生活的书写中,运用奇幻叙事这一形式去深入藏族人们的精神世界。
由于奇幻叙事的参与,小说中出现了大量非理性场面。小说《岗》中,牧人在梦中所见的雪地上的婴儿出现在现实中,“在月光的照射下,他发现这个婴儿的身体是透明的。婴儿体内小小的五脏六腑的轮廓显得清晰可辨,而且随着呼吸在轻轻地颤动着”。男孩岗看不到自己的模样,但和女孩岗长得极像,两人相貌酷似、肌肤雪白。矛盾的是身为雪山精灵的岗只能通过现代社会的宣传手段来解决酷暑的困境。《流浪歌手的梦》中,流浪歌手次仁梦中的女孩会一点点长大。小说中超自然叙事的出现往往带有非理性意味。万玛オ旦在采访中被问及如何看待现实中不可能的事奇迹般出现时,他回答:“很早以前,就像当地的藏人一样,我也全心全意地相信着这一切,现在,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内心会有质疑的声音,由于现代理性的渗透,我对于藏区的人、事的感受,已经不是那么纯粹了。”由于现代理性的渗透,面对超自然现象时人们产生了犹疑与不确定,原本被认为是真实的事件以现代理性为标准被认定为奇幻。万玛オ旦借助奇幻叙事尝试去还原被现代理性渗透的世界,他深知全然抵抗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对此只能身处理性与情感的矛盾之中。但奇幻叙事至少营造了一种新的现实——“较之过于理性与坚硬的现实,它呈现出某种混沌、松软与诗意”。
万玛オ旦在访谈中说:“我并不拒绝现代化,我的作品呈现的也并不是现代和传统之间的二元对立,而只是一种现实的状态。”与通常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的观念不同,万玛オ旦的小说要呈现的是现实与人最真实的状态,这也是奇幻叙事背后更为本质的追求。在被现代理性冲击的世界中,万玛オ旦意识到人无法避免被卷入到由技术、理性主导的世界中,但从情感上他倾向传统藏地文化背景下人的本真状态。出于这种矛盾的态度,小说要呈现人真实的状态需以一种去魅的方式进行还原。也就是说,即便是神的存在,也是与人和人的日常紧密相关的。“你更关心人间日常和行进变化的藏地,即便是’神’,也是和人相关的,比如《静静的嘛呢石》里的寺庙和小活佛。”当活佛有求于洛桑时,“洛桑从来没见活佛对什么人这样客气过”,当活佛如愿拿到了刻有六字真言的嘛呢石,小说这样描写活佛的状态:“活佛很高兴,高兴得合不拢嘴巴。他左看右看了好一阵之后说’’我们得好好超度超度这个老头子了。’”这オ请了七个喇嘛大张旗鼓地念了七天七夜的经。此时活佛的喜怒、行为和平常人无异,小说通过具体人物行为的描写实现了对神的去魅。
万玛オ旦的作品中包含了许多奇幻叙事,但每一处奇幻都与真实的人与事紧密联系,奇幻不仅仅是一种手法和形式,也是对现实的表达,更是对人生存状态的展现。《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洛桑和死去的刻石老人之间的对话无比轻松俏皮,洛桑说:“我就算是你儿子,我也不会跟你学这个手艺的,我不喜欢这个,我只喜欢喝酒。”从中能看到藏区的现实、藏区人们真实的生活和情感方式,就如同万玛オ旦说的:“其实他们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的,只是你不了解罢了。”
万玛オ旦的奇幻叙事既融合了藏地民间故事的写法,又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现代人生存境况的探索,他在短小的篇幅中完成了一系列与藏地文化相关的想象,在藏地与现代性背景下探索着更为本真的人的存在状态。“我想写作的终极目的不是为某个问题找到一个答案,或者为某种困境找到一条出路,也许把人在某个阶段的困惑和困境表现出来就够了。”这正是万玛オ旦小说奇幻叙事下的现实表达,他意识到藏地的人们无法抵御现代理性的入侵,同时试图通过不断重返前现代社会中的超自然文化,来实现情感上的抵抗与回望。
结语
万玛オ旦的奇幻叙事没有宏大的历史书写,有的只是发生在藏地的日常生活、偶然出现的超自然现象,以及偶尔闯进村庄的现代文化与外来人,它们基于藏族人们的日常生活,吸收了藏地民间故事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精神,在藏族作家文学创作中显现出独有的面貌。小说通过轮回转世、超越生死界限等奇幻元素的加入完成了独特的藏地书写。万玛オ旦奇幻叙事的背后是对前现代文化的回望,展现了非理性之下对现实的触碰。在作者对藏地日常生活的奇幻书写中,能看到藏地的现实是某种疏离现代理性的混沌与诗意,是生活于其中的人最真实自然的精神与生存状态。(作者:金露,苏州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2021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当代文学中的甘肃’形象’与想象”(项目编号:2021YB061)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第42卷2024年第5期,原文版权归作者本人及原单位所有,篇幅所限,注释略。(责编:周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