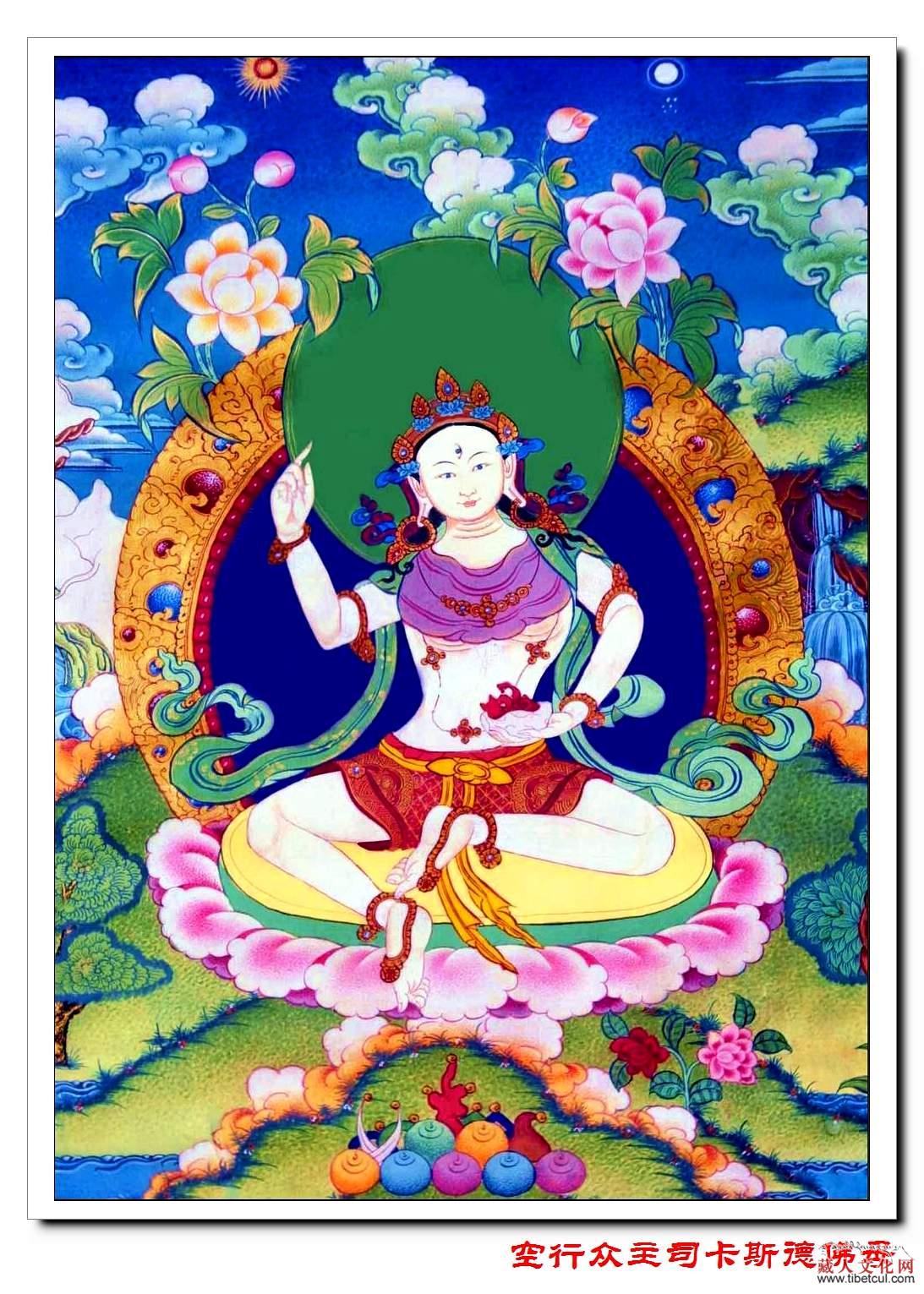巴·赛囊自幼受到良好的培育,才识过人,早年即侍奉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身边,颇受青睐。他崇信佛教理论,认为在吐蕃地方只有依靠佛教,才能利益众生,维护赞普的统治。因此,他和一些信佛大臣尽力说服赞普,要在吐蕃大兴佛教。赤松德赞派巴·赛囊等人前往当时盛行佛教的中原地区取经。巴·赛囊重任在肩,千里迢迢赶到长安,受到唐朝君臣的欢迎。唐肃宗满足了吐蕃赞普的要求,除送给大量蓝纸金字的佛教经典外,还特别送给赤松德赞1顶颇罗弥帽子,1万匹锦缎以及直径为1庹的彩纹木盘。巴·赛囊也得到100两乌雀图案的金纸、500匹绸缎、1庹长的珍珠链10根,以及颇罗弥宝瓶、100两重颇罗弥盘各一。巴·赛旋等人的长安之行,对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吐蕃与内地的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等到巴·赛囊等人回到吐蕃时,情况已有大的变化。吐蕃王朝内部崇佛与佞佛的大臣争斗激烈,强大的反佛势力使赞普亦无能为力。巴·赛囊不久便被排挤出逻些,贬到芒域(今济咙一带)担任地方官。但是,他仍不忘兴佛,利用任职的便利,在当地主持修建了两座寺庙,以表虔诚的崇佛之心。巴·赛囊的举动使反佛势力更为不满,于是不断施加压力,逼迫赞普撤掉他的官职。巴·赛囊丢官后,对佛教的敬信有增无减,仍前往天竺大菩提寺和那烂陀寺朝拜圣迹。在尼婆罗,他遇到了著名佛学大师寂护。在他的一再请求下,寂护大师答应,如果得到赤松德赞的邀请,他可以前往吐蕃弘扬佛教。巴·赛囊旋即返回逻些,向赞普面陈与寂护大师的会面。赤松德赞听后,经过深思熟虑并征求亲信大臣的意见,设计将代表苯教势力、极力反对佛教的大臣马尚仲巴结活埋,显赫一时的达札路恭亦被流放北方。
巴·赛囊在除掉崇佛障碍后,即奉命前往尼婆罗迎接寂护大师。寂护抵藏后,向赞普讲解佛教的道德规范和基础理论,如“十善”、“十二因缘”等。赞普对此感兴趣。不巧的是,寂护在吐蕃期间,正遇灾荒瘟疫,苯教徒遂嫁祸于他,赤松德赞不得不把他送回尼婆罗。临别时,他举荐了另一高僧莲花生。巴·赛囊再一次奉命前往邀请。莲花生以咒术见长,来吐蕃路上,一路与苯教徒斗法,连获胜利,直至桑耶附近。赞普遂率臣民亲往迎接。不久,寂护也再次应邀赴吐蕃,至此佛教势力大长。
巴·赛囊随后即从天竺高僧寂护大师出家,成为首批被剃度的藏僧之一,取法名巴·意希旺波,开始了他的佛学生涯。他脑子灵活。学习刻苦,深为赞普赏识。后来,寂护大师圆寂,赤松德赞即任命他为堪布,并赐其大金字告身,特许他参加吐蕃王朝的小御前会议,地位高于其他大臣,足见赞普对他的恩宠。
当时,僧人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赞普府库供给,但数量不定。赤松德赞每每虑及此事,即感不安,尤恐自己故去,僧人无法生活。他召见巴·赛囊,谈及想给寺庙300民户、每个僧人7户百姓的供养,但巴·赛囊自有见地,他婉转地对赞普说,此事与赞普奖子功臣900户百姓相比较,一点也不多。可是今后要遇到天灾人祸,恐不能保证这样的供给数量。所以,从长计议,还是实际些,给寺庙属民200户,每一僧人属民3户较为合适。赞普遂依其意而行,总计赐给桑耶寺和305名僧人寺属奴户1065户(按每户4口计算,总计4260人)。赤松德赞和巴·赛囊此举对藏传佛教的发展颇有影响。
佛教在吐蕃传播后,这里聚集了中原地区乃至天竺的大批僧人,佛教内部的纷争也随之而起。当时,汉地佛教的顿门派和天竺大乘佛教的渐门派之间矛盾日趋明朗,争辩尤为激烈。赤松德赞对佛理知之甚少,不好轻易表态。巴·赛囊是热心于天竺渐门派的,一气之下,跑到吐蕃南部去坐静。两派互不相让,斗争达到白热化程度,赞普再难等闲视之,不得不下决心请出他在佛教事务上的谋臣,先后三次派人劝巴·赛囊回逻些,但都被婉言谢绝。赞普无奈,下死命令让朗伦康巴务必请回巴·赛囊,完成任务可子大铜字告身,否则问斩。巴·赛囊再难拒绝,被迫返回逻些,他回来后,便向赤松德赞灌输寂护大师所传之渐门巴才是佛教正宗的思想,极力劝他派人到天竺迎请寂护大师的亲传弟子噶玛拉锡拉。巴·赛囊还就“顿渐之争”的实质等向赤松德赞作了详细的解释。赞普听后非常兴奋,即向巴·赛囊顶礼,并一再说:“巴·赛囊是我的轨范师。”噶玛拉锡拉被赤松德赞请到吐蕃后,赞普亲自主持召集天竺佛教(以噶玛拉锡拉为首)和汉地佛教(以摩诃衍为首)的僧人们在桑耶寺举行辩论。赞普事先说定,辩论中的败者必须离开吐蕃,否则严惩不贷。
巴·赛囊等人完全支持噶玛拉锡拉的观点。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经过紧张激烈的辩论,摩诃衍等汉僧失败,被迫返回内地。
佛教虽然在吐蕃站住了脚,但它与苯教的斗争仍在进行。不久,噶玛拉锡拉被人刺死。巴·赛囊闻讯,恸心不已,几近昏绝,顿感心灰意懒,绝食而死。
巴·赛囊对前弘期佛教做出了较大贡献,在历史文学上也成绩卓著。有人考证,藏族古代历史名著《巴协》就是他所著。这本书自赞普赤德祖赞(704~755在位)兴佛说起,直到其子赤松德赞建成桑耶寺为止。增广本则写到阿底峡大师入吐蕃(1038年)时为止。是书对唐朝金城公主入吐蕃、桑耶寺修建等记载颇详。其记叙史实较翔实,成为后世藏族史学家写史的依据。